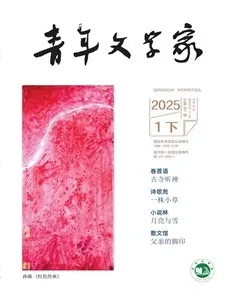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視角下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悲劇形象研究
女性主義是一個復雜而多元的思想體系,旨在推動全球范圍內的女性團結起來,維護自身權益,進而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解放。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是女權運動第一次高潮中的重要流派。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他者”“超越性”“內在性”等重要概念。她提出的“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的觀點,體現出男性將自己定義為標準,而女性則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和被壓迫的對象,被剝奪屬于自己的權利和地位。鑒于此,本文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視角對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悲劇形象進行分析,探討其成為“他者”的過程及原因。
一、理論概述
西蒙娜·德·波伏瓦從存在主義理論出發,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戀愛、結婚、生育到衰老各個階段,以及在農婦、女工、知識分子、明星等各個階層中的真實處境,探討女性獨立可能的出路。她發現女性生存在一個男人強迫她成為“他者”角色的男權世界里,女性被迫處于性別邊緣。這構成了《第二性》的主要論點:女性被男權強迫進入一種被壓迫的地位,同時她們中的大部分人思想固化并逐漸服從壓迫,從而與男性建立起不平等的性別關系。
關于女性“第二性”和“他者”地位形成的原因,西蒙娜·德·波伏瓦進一步闡釋說“女性長期以來處于壓迫和被動的‘他者’地位,這種壓迫和被動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結構所造成的”。“第二性”通常指的是女性在社會、家庭中所處的次要、附屬以及邊緣化的地位。男權地位的上升是女人權利和生存地位下降的重要因素,這主要體現在男女生理差異、社會分工以及歷史演變等方面。首先,隨著男性體魄優勢的顯現,他們逐漸在生存攻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次,女性自身的“內在性”。女性一開始就被冠以生育和教養孩子的義務,因此女性如果不能生育或者不能生育兒子,就可能面臨家庭的壓力甚至指責。女性被“母親”的身份所束縛,從而不得不回歸家庭。因此,這種所謂的“內在性”限制了女性“超越性”的發展。社會通過灌輸男權主義思想,迫使女性順從被壓迫的事實,剝奪女性應有的權利,如教育權、生育權等。在這種精神灌輸下,女性被迫放棄了自身的“超越性”和獨立性并逐漸接受“他者”的身份,以滿足父權社會的需求。因此,“他者”和“內在性”成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思想的關鍵詞。
縱觀歷史,我國文學作品中存在眾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三國演義》中的貂蟬等。而英美文學作品當中,也不乏此類悲慘的女性角色,比如《面紗》中的凱蒂、《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薩拉等。這一系列的文學作品都以不同的視角闡述了不同背景下中西方女性角色的生活和命運。上文敘述的中西方文學作品呈現出存在主義哲思:女性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男性的附屬品嗎?只是成為社會中的“他者”和“他性”嗎?鑒于此,通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存在主義哲思,本文將深刻探討中西方不同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地位,結合時代背景和文化因素分析其不能擺脫“他者”身份的原因,以及對于當代女性樹立女性主體意識、實現自身價值的激勵作用。
二、我國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悲劇形象分析
(一)《祝福》中的祥林嫂悲劇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身處一個具有濃厚封建禮教色彩的時代,她所經歷的兩段婚姻都不是自主選擇的。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意味著祥林嫂成了一個寡婦,在20世紀20年代的貧苦農村,成為寡婦的下場無疑就是被夫家賣到別處。無奈之下,她選擇逃離,來到了魯鎮魯四老爺家中做起了女工。然而,踏踏實實生活的祥林嫂再一次被賣到山里的一戶人家做老婆。祥林嫂做過抗爭,下了花轎后不肯拜堂,卻被眾人摁住后撞暈過去完成了儀式。此時的祥林嫂只能接受被賣掉的命運。婚后祥林嫂為第二任丈夫生育了一個兒子,可好景不長,丈夫病死,而唯一的兒子也被狼叼走,祥林嫂徹底心如死灰,無處可去的她只能重新回到魯四老爺家做工,最后承受不住現實生活的打擊變得麻木。祥林嫂的形象被塑造為服務男性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展現了封建禮教下女性作為“他者”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存在主義哲思同時也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祝福》中的祥林嫂生活的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新舊思想并存,廣大貧苦人民看到了希望,但以地主階級、資產家為代表的守舊派拒絕這先進的、損害他們利益的思想。祥林嫂骨子里想要擺脫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可她個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無法與整個守舊派抗衡,導致了她的悲慘結局,成為一個被封建社會吞噬的存在物。
(二)《三國演義》中的貂蟬悲劇形象
在男權主導的社會背景下,《三國演義》中的貂蟬是一個自我意識缺失、生存困境重重的悲慘女性形象。基于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女性個體意識和自由選擇的覺醒,貂蟬缺乏獨立的存在意識和價值,充當了王允等男性角色實現政治目的的棋子。在這一場精心設計的謀劃中,貂蟬在王允的授意下讓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去離間董卓和呂布之間的關系。貂蟬的主觀意愿和個體意識被極大的忽視,被迫成了男性權力斗爭的一顆棋子,她的存在在很大意義上成了權力斗爭的犧牲品,被定義為“他者”,無法選擇和掌握自己的命運。同樣,在連環計中,貂蟬一直周旋于董卓和呂布之間,她的愛情觀與婚姻觀被權力斗爭所扭曲,導致了她的人生更加悲慘。
在這場政治斗爭中,貂蟬對于身份認同的迷茫以及不自覺地淪為“他者”地位的悲慘遭遇是基于父權封建主義下的思想固化,最終以悲慘的結局收場。
三、英美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悲劇形象分析
(一)《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薩拉悲劇形象
約翰·羅伯特·福爾斯,英國當代作家。1947至1949年底,他就讀于英國牛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其間,他主要學習法語和法國文學,深受法國存在主義作家的影響。畢業后,他在法國、希臘和英格蘭都任教過一段時間,因此他認為,他的精神氣質和文化背景主要扎根于法、希、英三國,相比較而言,他認為受歐洲文化的影響更甚于本土。1969年,《法國中尉的女人》出版,榮獲史密斯文學獎和國際筆會銀獎;1981年,《法國中尉的女人》被改編成電影。《法國中尉的女人》是反擊20世紀60年代“文學衰竭論”和“小說困境論”的一部力作,它揭示了“自由”與“顛覆”主題,啟用了三個身份、目的和職能不同的敘述者講故事。這部作品蘊含著約翰·羅伯特·福爾斯所倡導的存在主義自由觀,展示了人類在困境中的自我實現以及自由選擇。
薩拉出身于社會底層,她的父親出于名門情結堅持讓她接受教育并爭取脫離底層,躋身上流社會。但薩拉所接受的不過是一所三流女子學院的教育,她得到了所謂“淑女”的虛名,卻被迫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受害者。并不幸福的家庭氛圍使得薩拉對于愛情的理解是模糊的,她曾經照看過一位因輪船失事而受傷的法國軍官,她誤以為兩人之間產生了感情,結果卻被法國軍官始亂終棄,也讓她背負上了“法國中尉的女人”的罵名。丟失工作、受人冷眼的薩拉被人介紹成為波爾坦尼太太的秘書。波爾坦尼太太是維多利亞時代上層人物的代表者,她遵從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標準,嚴格監控薩拉的言行舉止,但薩拉并沒有放棄她對自由的追求。薩拉與業余科學家查爾斯在安德克立夫相遇后,查爾斯被她“恐怖”的孤獨所震驚,也對她這個不同于其他女人的女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基于維多利亞時代對于女性自由的束縛,薩拉對待愛情的態度是主動出擊,不論是她假裝腳踝受傷以博取查爾斯的同情和關心,還是在谷倉中親吻查爾斯的手背,她都居于主動的地位,顛覆了查爾斯對于女性在愛情關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查爾斯同樣深受浪漫主義思想的熏陶,在薩拉直爽灑脫的態度的對比下,他逐漸厭煩了未婚妻循規蹈矩、裝腔作勢的派頭,對她的維多利亞淑女氣質感到失望,被自然、向往自由和純真愛情的薩拉所吸引。作為維多利亞等級社會的一員,薩拉也是受害者,面對世人對她的嘲諷和詬病,她不畏懼周圍的異樣眼光,不僅接受“法國中尉的女人”這一罵名,承認自己的“他者”身份,同時還編造了自己與法國軍官的虛假關系。這是處于等級社會中女性缺乏自主性從而產生的逆反心理,她認為在這種身份下自己能夠獲得更大的自由,從而達到對社會的嘲諷。
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崇尚等級觀念的男權社會。在此背景下,英國女性通常被期盼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她們的生活往往圍繞著家庭和社交圈子展開。這些女性雖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修養、家政技能和社交禮儀等,但她們的教育卻很少涉及科學、文學或者藝術等領域,使得女性缺乏自主性和培養個人興趣的機會。此種社會背景下,同樣接受過這些教育的薩拉呈現出后現代女性的特征,她勇于挑戰階級權威和傳統觀念,展現了存在主義視角下女性不甘淪為“他者”的反抗精神,清醒的追求自己的理想。當薩拉發現自己與查爾斯的愛情動機不純時及時抽身,毅然決然地終止了他們之間的關系,轉而追求獨立自由的生活。薩拉沒有選擇附屬于男性,在與查爾斯的關系中,薩拉也不屑于扮演需要人同情和幫助的弱者形象,掌握了十足的話語權和主動權。薩拉的形象體現了一位處于維多利亞時代的新女性對于自由的追求以及對傳統的顛覆。
(二)《面紗》中的凱蒂悲劇形象
《面紗》的作者毛姆是著名的英國小說家,一個自狄更斯以來擁有最多讀者的小說家。由于幼時口吃、父母離婚等不幸的生活經歷,毛姆的作品大多探討人性的陰暗面,特別是對于女性的諷刺描寫。
故事的開端介紹凱蒂長得非常美麗,雖然有著好看的外表,實質上卻是一個“愚蠢、輕浮、無知”的女人。她認為女人只需要依附于男人,而她的終極目標就是釣上金龜婿,一躍而上躋身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正所謂有其子必有其母,凱蒂扭曲的價值觀的形成就是拜她的母親賈斯汀太太所賜,她同樣將婚姻當成利益,最終卻沒有實現她的理想。因此,賈斯汀太太將她所有的心血和希望都寄托于她的兩個女兒,希望通過兩個女兒的婚姻為自己帶來實質性的利益,至于愛情則是無關緊要的。在與妹妹婚姻的攀比下,凱蒂草率地嫁給了細菌學家沃特,毫無疑問她憑此獲得了不錯的社會地位。但由于兩人之間并不存在愛情,也缺少共同語言,他們的婚后生活是不幸福的,這也為后文凱蒂另尋佳婿來滿足自己的貪婪埋下伏筆。凱蒂隨丈夫來到香港,她遇到了比她丈夫社會地位更高的外交官查理。盡管兩人都是已婚狀態,但這并不妨礙兩人走到一起。奸情敗露后,沃特徹底看清了凱蒂的真實面目,也明白了兩人的婚姻就是一場經濟游戲,根本不存在什么愛情。但沃特并沒有當面揭發兩人的奸情,而是使用了一種更為殘酷的手段:他給了凱蒂兩種選擇,要么讓查理與他的妻子離婚,并和凱蒂結婚,要么讓凱蒂和自己一起前往正在遭受霍亂的湄潭府。既然事情已經敗露,凱蒂深知去了湄潭府就等同于送死,因此她選擇和查理結婚。可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查理的事業需要他現任妻子的支持,與妻子離婚就相當于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因此,權衡利弊之下,查理無情地拒絕了凱蒂的結婚請求并拋棄了她。
《面紗》的命名典出雪萊的十四行詩《別揭開這畫帷》:“別揭開這畫帷,呵,人們就管這叫作生活。”凱蒂受利欲熏心的母親的影響,也成了一個非常現實、驕傲和有野心的人。她奮力想完成階級的跨越、實現自己的價值,然而她采取的方法卻是錯誤的。凱蒂似乎在無意中陷入了自我貶低的境地,她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商品化”與“他者化”的位置,視自己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男權主義的盛行一方面源于男性自我設定為“標準”,并對女性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女性不自覺地接受了“他者”的角色,甚至對此感到滿足,將自己視為可以交換、以價值衡量的物品。這種行為在無形中削弱了那些勇敢反抗男權主義的女性的努力,極大地影響了當代女性的婚姻觀、兩性觀和價值觀,阻礙了世界女性意識的覺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她們又何嘗不是男權主義背景下悲劇的產物呢?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凱蒂的家庭環境和母親的教育都預示著凱蒂在未來將會成為一個與她母親相似的、利欲熏心的女人,她扭曲的婚姻觀和兩性觀也導致了她悲劇人生的結局。
本文通過分析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悲劇形象,深入探討了不同背景下女性淪為“他者”的社會、文化等因素以及女性反抗傳統觀念的動機。上述作品通過介紹女性的生活背景,描述女性不同時期的生活愿景,以及創造一系列矛盾來凸顯獨屬于女性形象的堅毅、細膩和勇氣。然而,現實生活的殘忍對女性造成了嚴重的沖擊,面對不公的命運她們奮起直追,卻最終以悲慘的結局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