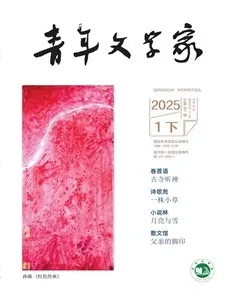禪宗“空”“相”思想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研究


禪宗是佛學與中國儒、道思想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化的佛教,它雖然延續了佛教“空”的理念,但禪宗的“空”卻與“相”有著密切的關系。禪宗的“空”“相”思想也對中國傳統繪畫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本文以禪宗“空”“相”思想為研究視角,進一步剖析其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為進一步豐富中國繪畫理論增磚添瓦。
一、問題的提出:“空”“相”與中國傳統繪畫關系的再審視
“空”是禪宗的核心,體現為“無念”“無相”“無住”。其中,“無相”與視覺的關系最為密切,它也是對中國傳統繪畫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人們要做到“無相”,必須首先了解“相”。那么,“空”和“相”具體是什么呢?“空”,禪宗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沒有獨立的實體。“空”并不是一般意義的“無”,而是涵容萬有。“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慧能著,丁福保箋注,哈磊整理《壇經》)“空”也是修行者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禪修的終極目標,它是人對自身存在的超越。“相”是禪宗思想的理論范疇,“相是什么?粗略地說,就是事物的相狀,即我們常言的現象,是時空中的具體存在”(張節末《禪宗美學》)。“相”在數量上是無窮無盡的,它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連,人們往往把這些“相”看得無比重要,生起計較、執著之心。“空”與“相”的關系是緊密相連的。“空”就是強調不住于相的“離相”。“離相”只是把“相”看“空”,并不是與“相”絕緣,也不是要求人們離開現象界。因此,本文立足于視覺藝術,從禪宗“空”與“相”的思想出發,深入剖析其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不失為豐富中國繪畫理論的一個關鍵視角。
二、以“空”為本:“空”“相”對審美心理的影響
(一)由“虛靜”到“空靈”:“空”“相”對“虛靜”審美心理的影響
中國美學的“虛靜”偏重的是一種藝術主體的審美心理活動,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形象。“虛靜”與中國道家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道家哲學的核心是“道”,但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這說明“道”不可說,無法用言語表述。老子又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也就是說,雖然“道”不可說,但可以在致虛守靜的境界中去“體道”。道家認為“虛”和“靜”是“道”的兩個根本屬性。《莊子》有言:“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在老子的基礎上,又把“虛”與“無”聯系了起來,得出“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的結論。莊子的虛靜是擺脫物欲和各種情感,然后才能無為而無不為。莊子顯然把“虛靜”從外在于主體的“道”向理想人格過渡,遁向內心,達到精神上的超然獨立。但老子和莊子的“虛靜”還都只是哲學層面的“虛靜”,而最早將“虛靜”引入文藝美學范疇的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意思是說:在進行藝術創作前,藝術家要先對心靈世界進行淘練與潤澤,徹底清除功名利祿的欲望,讓躁動的心緒趨于平和,進入空明澄清的心境。從上可知,盡管劉勰在藝術上引用了“虛靜”,但他只是把“虛靜”作為藝術創作的前提和心理準備,其本身并非結果。
再看禪宗盛行后,“空”“相”思想對中國傳統審美心理的影響。禪宗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慧能著,丁福保箋注,哈磊整理《壇經》)。禪宗通過“無”與道家哲學進行了聯系,它要求人們由“無”去領悟“空”。但禪宗又把“空”落實在了“自心”上,要求外于相離相、內于念不念,更強調了個體的主觀能動性。“離相”既不舍相也不著相,主張對所有的相都不即不離。禪宗的這種心理和思維方式也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的“虛靜”審美心理,藝術家不再執著于有限的“相”,而是要在與“相”相統一的“空”中追求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感受。也就是說,意境的實現必然落實為“象外”的空靈感。禪宗的這種“空”“相”思想促進了中國藝術“虛靜”審美心理的發展,它不僅使審美創造心理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而且使繪畫作品有了空靈的神韻,使繪畫創作和審美走向了禪的“空靈”境界。
(二)由“丹青”到“水墨”:“空”“相”對色彩審美心理的影響
在禪宗看來,外在事物的諸“相”,都是人的六根所對應的六塵。繪畫是視覺藝術,它與我們六根中的“眼”關系最為密切,“眼”對應“色”相,如顏色,形貌等。我們知道,從顏色上看,在物質色彩的條件下,三原色合一即呈現黑色。在色光的情況下,三原色合一即呈現白色的光。長期以來,人們對色彩的認識,只是客觀的“有色界”的認識,反映在繪畫作品上,只有絢麗的色彩,而不見“空靈”的意境。因此,在禪宗看來,外在的東西并不是其本質所在,要探索事物的本質,就要去除表象的限制。禪宗“空”“相”思想對眼“色”的觀點與老子《道德經》中“五色令人目盲”的觀點是一致的。只有去除顏色對人的干擾和障礙,才有可能達到最終的“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階段。因此,在“空”“相”的影響下,以王維為代表的藝術家們的審美心理發生了變化,從崇尚青綠山水向水墨山水轉變。
三、引禪入畫:“空”“相”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創作的影響
(一)“反常”禪趣:基于“空”的禪宗時空觀對繪畫內容的影響
我們一般認為時間是客觀的,它是單方向流逝的。但禪宗講“萬法皆空”,認為作為現象之一的時間也是世間萬法的表象形式,也是“空”的。而“心”是萬法的根源,時間也是“因心而生”。人在頓悟時,可以有對時間的特殊體驗,“即所謂‘永恒在瞬刻’或‘瞬刻即可永恒’”(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因此,在禪宗那里,線性的時間可以被顛覆,時間序列可以任意轉換和交融互攝,如青剉如觀禪師的“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普濟《五燈會元》)。同樣,禪宗的空間觀對于常人來講也是不可思議的。禪宗認為:“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靜、筠禪僧編,張華點校《祖堂集》)空間和時間一樣都是“空”的,是人心所現之象,無大小之分。禪宗的這種對于現實時空觀的超越,對唐代王維的繪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畫物時,多不受實際時空的限制。他的《袁安臥雪圖》中的“雪中芭蕉”就是一個反日常現象的繪畫,他將生長在南方熱帶的芭蕉置于北方寒冬的大雪中。這是中國繪畫史上爭論極大的一幅畫,歷來人們對此毀譽參半。他之所以把芭蕉畫在大雪中,則是深諳禪宗的時空觀,將心性體驗的時空代替了自然法則的時空,營造了富有禪宗哲思的境界。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說:“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二)以“淡”為美:“空”“相”對水墨畫產生的影響
在禪宗盛行的中晚唐時期,藝術家受“空”“相”思想的影響,“淡”成為當時流行的筆墨趣味。藝術家不再以艷麗的丹青為美,而崇尚水墨。“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維《山水訣》)。張彥遠也在《歷代名畫記》中說:“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因此,王維在畫法上進行了創新,他開創了濕筆水墨渲染法。“余曾見(王維)破墨山水,筆跡勁爽。”(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破墨”就是濃墨中加水,破成濃淡不同的層次,然后去渲染出山石的陰陽向背、高下凹凸。所謂“破墨”,即意味著渲染法的出現,初步奠定了中國水墨山水畫的基礎。董其昌奉王維為文人畫的始祖,并把畫分為南北二宗,推王維為南宗之祖。董其昌對文人畫的南北分宗對中國繪畫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國自六朝時就興起的青綠山水,刻畫精致,設色艷麗的風格,在唐代由于受“空”“相”的影響,轉變為墨色淋漓的水墨畫風格,用樸素的墨色營造了不一樣的別致風貌。
(三)“不求形似”:“于相而離相”對繪畫“求真”問題的影響
禪宗的“無相”既不舍“相”也不執著于“相”,而是“于相而離相”,這在形式上啟發了水墨畫的意象構建。水墨畫既非有形,又非無形,既是有形,又是無形。“無相”并不排斥“相”,畫家只有忘“相”,才能不為“相”所束縛,才能實現對“相”的超越。其實,有關繪畫“不求形似”和“求真”的問題,早在五代時期就被提出來了。“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茍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荊浩《筆法記》),這里的“似”即形似,“真”就是繪畫對象的精神特質或生命的真實。從《筆法記》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說明繪畫最重要的是“求真”,而不是“形似”。八大山人的“畫者東西影”的觀點更好地詮釋了繪畫“真”的問題。他認為畫要畫出“東西”的影子,要超越具體“相”的本身,去表達深沉的生命感覺。
(四)空靈意境:色空觀對繪畫留白的影響
禪宗的色空觀,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經》)。色由因緣和合而生,所以色即是空,而空能生萬有(色),所以空即是色。色空本為一體,沒有二樣,故稱之為不二法門。因此,禪宗的色空觀體現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秦祖永《繪事津梁》)的理念,它影響了中國畫的構圖。中國畫在構圖上留下一些空白(即留白),既可增加畫面的空間感,又可虛實相生,相得益彰。例如,宋代法常的《六柿圖》(圖1),紙本水墨,35.15cm×29.1cm,日本京都龍光院藏。畫面中只有六個柿子,無桌子,無題字,亦無落款,元素簡約單純。六個柿子近乎一行但也錯落有致地排列于畫面的下部,造型簡單但也有方圓變化。背景空白,不著一色,大面積的“空”反襯出了柿子的“有”。六個柿子墨色濃淡不一,顏色從空白到深,又由深到空白,象征著事物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過程,揭示了事物都是在無常變化著的,而最后都會歸于空。這幅畫雖然極其樸素,極其空靈,卻像清凈的本體一樣,鉛華褪盡,純凈無塵,更體現出禪宗境界。
(五)“喜空尚簡”:“頓悟”對“減筆”畫的影響
禪宗提倡“頓悟”。六祖慧能的“頓悟”思想,貫穿于整個《壇經》文本。“頓悟”一詞在《壇經》中共出現了5次,并不算多。但在《壇經》中,描述頓悟發生時,多用“言下”一詞。“言下”在《壇經》中出現頻率高達14次。這說明“頓悟”的“頓”具有此時性和此地性。“此地”就是人在現實世界中當下所立足的地方,它就在日常生活中。因此,禪宗強調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只需“向內心探求”。這種具有鮮明個人色彩的“頓悟”說,可謂是簡便、省力,對傳統文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它表現在繪畫風格上,則形成了一種打破固有常規,不拘于常形的“減筆畫”風格。“減筆畫”整體上以“空”的形式呈現出“簡”的面貌,用筆簡潔、惜墨如金。在我國繪畫史上,最早的形象簡略的畫法以宋代梁楷的“減筆”人物畫為代表。例如,梁楷的《太白行吟圖》(圖2),紙本水墨,81.2cm×30.4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這幅畫只有頭部相對較為細致,但也只寥寥數筆,就把李白灑脫、豪放、飄逸的神態刻畫得惟妙惟肖;對衣袍的描繪,也好似不經意間幾筆帶過,顯得簡淡疏落,但用筆粗細濃淡恰到好處;從衣領至肩背,以及衣擺處,用粗筆稍重的墨色來支撐畫面,其他部位的線條則采用淡墨,很好地表現了衣袍的質感。整幅畫簡到不能再簡,但李白一面走、一面吟詩的形象卻活靈活現地展現在了觀者面前。
禪宗作為中國化的佛教,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博大精深的禪宗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藝術的審美心理和藝術創作,尤其是禪宗的“空”“相”思想在中國傳統繪畫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認真探究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反常”禪趣、以“淡”為美、“不求形似”而“求真”、空靈意境、“喜空尚簡”的藝術創作風格背后的真實原因,會感到別有一番風趣,這對進一步豐富中國繪畫理論將起到一定的作用。研究禪宗“空”“相”思想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還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對其他視覺藝術的“跨媒介轉化”起到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