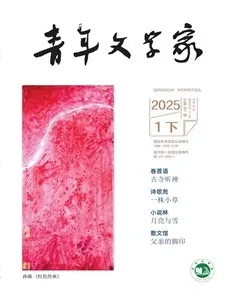博爾赫斯小說的互文性新探
邊緣性是現代詩學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而對間際的跨越無疑是博爾赫斯“奇幻敘事”小說詩學顯著的屬性之一。在談及其首部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里,他曾害怕這本書會變成一種“葡萄干布丁”(《博爾赫斯文集·文論自述卷》)—因其過于繁雜的內容。的確,“葡萄干布丁”式的雜糅寫作在博爾赫斯后來的小說創作中屢見不鮮,既包括主題和形式的雜糅,也包括文化背景和美學風格的雜糅。無論是跨越邊緣還是雜糅,這兩個特征都指向了博爾赫斯小說中所運用到的重要手法—互文性。
一、“互文性”概念綜述
受到俄國文論學者巴赫金關于對話主義理論的啟發,法國批評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亦稱作“文本間性”)這一概念。她在1966年至1968年期間對該理論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1967年發表于《批評》雜志上的文章《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在這篇文章里,克里斯蒂娃闡明了所有文本實際上都是由引用其他作品片段拼接而成的觀點;換句話說,每個文本都包含了對其他文本材料的吸收和轉換過程。到了1968年,“原樣”學派出版了一部名為《整體理論》的研究論文集,在這部著作中進一步強調了每篇作品均是由多個文本相互交織而成的思想,正是由于這種融合與解構功能賦予了文本獨特的價值。由此,“互文性”的理念逐漸成為文學批評領域內備受關注的話題。
這一理論之所以能夠在批評界得到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克里斯蒂娃的導師羅蘭·巴特。1973年,在編寫《通用大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羅蘭·巴特在討論文本理論時引入了“互文性”的概念,并提出每個文本都是通過重新組合和引用已有的語言構建而成的觀點,從而幫助“互文性”確立了作為一個文學理論的正式地位。然而,由于克里斯蒂娃沒有對該理論給出一個明確且嚴謹的定義,“互文性”作為一個模糊而開放的概念,為后來的研究者們留下了廣闊的解釋空間。許多文學評論家根據各自的理解與需求對這一理念進行了調整、修正及再詮釋,最終導致互文性理論分化出兩個主要的發展路徑。
第一個研究路徑是解構批評,也被稱為廣義或解構意義上的互文性。這一領域的杰出貢獻者包括羅蘭·巴特、雅克·德里達、J·希利斯·米勒及哈羅德·布魯姆等人。羅蘭·巴特在其著作《作者之死》中提出,作者實際上扮演了“抄寫員”的角色,他們所做的不過是重復另一部模仿作品的過程,因此所有寫作都不具備絕對的原創價值;雅克·德里達對于“互文性”概念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他提出的“延異”理論指出,每個新出現的作品都是基于對先前存在的文本經過選擇與創新之后的結果,認為作者對文本所進行的所有評價、鑒賞或是解釋工作,本質上都是試圖對原作作出補充;而美國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誤讀圖示》一書中強調,所謂的影響力實質上指的是不存在孤立的個體文本,只有文本間的相互作用,這種觀點揭示了由于互文現象普遍存在,使得創作者們面臨著難以擺脫的影響焦慮。
另一個研究路徑是詩學與修辭學,有時也被稱作狹義或結構主義的互文性。這一領域將“互文性”視為一種分析文本的方法論工具,用于具體文學現象的研究,并具有較強的實用性。米切爾·里法泰爾提出,文本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內在的互文性質,而這種靜止不變的意義來源于它能夠把單個詞語、圖像以及主題等元素相互關聯起來。此外,他還強調了互文性對于讀者及接受層面的重要性,指出互文性即為讀者對某作品與其相關聯的作品之間聯系的認識。安托萬·孔帕尼翁,作為克里斯蒂娃的學生,在其作品《二手資料,引文的工作》中深入探討了引用在寫作中的作用,他認為所有的寫作都可被視為拼貼加上解釋,引用附加評論。熱拉爾·熱奈特則對互文性的理論進行了更加詳盡和深刻的闡述,這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廣義文本之導論》《隱跡稿本:第二度的文學》和《副文本:闡釋的門檻》中得到了體現。有人評價說,正是通過熱拉爾·熱奈特的努力,使得“互文性”這個概念變得更為清晰明確,并且從一個原本局限于語言學討論的術語轉變為了指導文學創作實踐的重要理念之一,標志著從廣義到狹義互文性理解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文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
互文性理論被劃分為兩大類:“定義性的”與“可操作性的”。前者主要用于探討文學的本質或文學性,而后者則側重于分析具體的文學現象。然而,由于廣義的互文性帶有強烈的解構主義色彩,它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倡導開放式的文本解讀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性,同時忽視了作者的角色以及對原創性的否定,因此,在具體文本的研究過程中缺乏明確的界限。正因如此,中國文論中采納的“互文性”概念主要作為一種工具和解釋手段存在,或者說,這種互文性實際上更接近于傳統的源流及影響研究范疇。鑒于此,為了增強互文性在特定文本分析中的實用性,本文將基于“狹義的互文性”來進行討論。
二、共存關系—改寫、并置
實際上,自熱拉爾·熱奈特的《隱跡稿本》問世以來,評論家們便逐漸形成了對兩種互文策略的區分:一種表現為共存形式,即一文本直接嵌入另一文本之中;另一種則表現為派生方式,指的是原作中的元素在新作品中被再現并加以改造。這兩種手法,在《小徑分岔的花園》這部作品里均得到了鮮明的展現。
從共存關系的角度出發,《小徑分岔的花園》這部作品在形式上表現為一名囚犯的獄中自述,全文以第一人稱和有限視角展開敘述。然而,在小說開篇處卻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文字講述了一段根據利德爾·哈特所著《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記載的故事,即原計劃于1916年7月24日由十三個英國師(配備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發起的攻勢被推遲至29日上午進行。利德爾·哈特上尉將此次延期歸因于連綿大雨,這看似并無特別之處。但青島大學前任英語教師余準博士所提供的證詞,經過記錄、復述并經本人簽字確認后,卻為這一事件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解釋。利德爾·哈特確有其人,《歐洲戰爭史》確有其書,歷史與現實交匯,虛構與考據相接,這天然地形成了多文本并置的局面。
“當敘述中的人物變成敘述者時,敘述就分為層次,一個敘述層次向另一個敘述層次提供一個或數個人物作為該層次的敘述者。從理論上說,敘述層次可以無限多……如果我們把占了主要篇幅的層次稱為主敘述層次,那么,為它提供敘述者的層次可稱超敘述層次……”趙毅衡在《中國小說中的回旋分層》中將占據主導地位的那一層定義為主敘述層次,而為其提供敘述者的那一層則被命名為超敘述層次。前者是供詞體裁的小說本身講述的一起謀殺案,與其說是對正史上英國軍隊延遲進攻一事的補充,不如說是對歷史真實的顛覆和改寫;后者則是對歷史真實作為小說敘事母本的一種確認,在這里,余準不再是最高層次的敘述者,他被更高一級的敘述者(也就是博爾赫斯本人)降為單純的敘事文本中的人物,又兼“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所以,他的證詞也隨之失去信度。
博爾赫斯通過開篇簡短的引述,引用了《歐洲戰爭史》對于延遲行動的闡述,構建了一個敘述者與被敘述對象間錯綜復雜的互文關系。他以小說角色的“陳述”挑戰了傳統敘事中的“歷史”概念,相對于其母文本《歐洲戰爭史》,展現了強烈的反歷史性特征。在持續與母本對話的過程中,讀者開始反思敘事的本質:究竟何為真實?是余準戳穿了正史的謊言,還是他的證詞本身就是一種謊言?這無疑又指向了博爾赫斯的迷宮敘事。利德爾·哈特的書寫與余準供詞的并置,最直觀的功能就是使歷史在1916年7月24日到29日之間走過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而這種時間的分岔與匯合正是整部小說著力闡發的內容,每個分岔都孕育著一個新的可能,表現出對無限可能的追求,就像小說中彭?的迷宮一樣,博爾赫斯也在文本敘事結構上為我們建立了迷宮,使文本內容與文本本身形成了同構。
三、派生關系—戲擬、仿作
除共存之外,熱拉爾·熱奈特還提出了另一種互文手法—派生。這種手法涉及對原作的一種轉化或模仿,但不會直接引用原文……仿作即為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在仿作中,雖然沒有直接引用原文,但其風格受到原作的顯著影響。派生主要分為戲擬和仿作。戲擬通過轉換原作內容,或是以漫畫化的方式再現原作,或是對其進行重新演繹。無論采取何種方式處理原作,它都保持了與原文學作品之間的緊密聯系。總的來說,戲仿實際上是作家對其他經典作品風格的模仿、情節的戲擬甚至故事的抄襲,當然,一方面是為了致敬,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求變求新。這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也有體現。
(一)與外來文本的互文關系
根據詞源學的視角,熱拉爾·熱奈特特別指出了在派生作品中,原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被辨識出來。戲仿的目的可能在于通過諷刺超文本來表達一種游戲性的反叛態度,也可能純粹是出于對原作的喜愛。通常情況下,戲仿的對象往往是經典文學作品或教科書中的材料。而博爾赫斯作為對中國報以無限想象的作家,他將自己對中國的偏愛也輻射到了文本中,對中國的經典名篇進行戲仿。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無疑是《紅樓夢》留下了最明顯的痕跡。
除了余準步入花園時內心獨白中提及他的曾祖父夢想創作一部人物數量超越《紅樓夢》的小說,從而直接構建了迷宮小說與《紅樓夢》之間的聯系之外,從小說中出現的兩個中國人名就可見一斑。主人公余準,在其他譯本中有另一個較為主流的譯法“雨村”,與紅樓夢中賈雨村同名,幾乎直接告知讀者二者都是串聯全文的線索型人物,同時“假語村言”的伏筆也陰差陽錯地暗指了故事的虛構性,盡管博爾赫斯本人也許并未考慮到這一層漢語意思。余準的祖父彭?與彭祖在西方的音譯PengTsu又無限類似,讓人聯想到莊子《逍遙游》中壽命與自由的關系,道破時間永恒的秘密。文中描述道,彭?放棄了顯赫的地位、美麗的妻妾以及奢華的生活,甚至舍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隱居達十三年之久。他去世后,繼承者只發現了幾堆雜亂無章的手稿。據說,家族成員曾打算銷毀這些手稿,但遺囑執行人—一位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將其出版。這里既包含了賈寶玉的結局—拋棄一切凡俗,也包括了曹雪芹的經歷—“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還包含了《紅樓夢》小說本身的命運。剩下的“雜亂無章的手稿”正是對《紅樓夢》未完的模仿,與彭?至死未完成的迷宮謎題相呼應,同時刊行人是“一個道士或和尚”,不由得讓人想起那位空空道人將一整部《石頭記》刻在補天頑石上傳之后世。
此外,姚寧指出書中的漢學家史蒂芬·艾伯特的居所是一座充滿中國特色元素的園林,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紅樓夢》中描繪的大觀園。也許從中國式花園直接推導至大觀園有些牽強,下文對室內書房的描寫就可以確證他的猜測:“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佚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只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只紅瓷花瓶,還有一只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這與賈寶玉游歷太虛幻境前,對秦可卿臥房各類華麗古董陳設的書寫幾乎如出一轍。余準與史蒂芬·艾伯特試圖解開的時間謎語,與薄命司金陵十二釵的判詞隱喻無限逼近,相似的幻想氣氛頓時在兩個書寫時間相距甚遠的文本中一道彌漫開來。
(二)自涉互文性分析
隨著后結構主義批評理論的興起,一種特殊的互文現象—自我指涉的互文性文本逐漸在文學領域中浮現。這類文本存在于同一作者構建的故事宇宙內或是在一個特定的文化語境之中,通過后期創作讓讀者能夠“重遇”早期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及情節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簡單的復制粘貼過程;相反,它體現了作者如何基于過往經驗以及對未來世界的構想,不斷地重塑角色及其經歷的故事線。利用精湛的藝術手法對先前的作品進行再創造,不僅豐富了故事內容,也提升了整體的藝術價值。
在《我這樣寫我的短篇小說》中,博爾赫斯指出:“《特隆,烏克巴爾,奧爾維斯·忒蒂烏斯》《EI Zahir》和《沙之書》這三篇作品看上去很不同,但本質上它們是一樣的:一種插入所謂現實世界的神奇的東西。”(喬·艾略特等著,張玲等譯《小說的藝術》)既然作者已明確表示這種自我指涉的互文性特征存在于他的創作之中,那么我們是否也能在《小徑分岔的花園》這部作品里找到類似早期著作中的痕跡?對此問題的回答幾乎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博爾赫斯在《阿萊夫》中將“宇宙空間的總和”濃縮于一個直徑僅約一英寸的發光小圓面內一樣,在《小徑分岔的花園》里,他再次以一部充滿迷宮般復雜性的小說形式,展現了對“宇宙時間總和”的獨特理解;就像他在《接近阿爾莫塔辛》中通過虛構一位來自東方孟買的律師來傳達深奧哲理那樣,《小徑分岔的花園》則借用了古代中國云南總督彭?的形象作為敘事載體;同樣,在《秘密奇跡》的故事里,拉迪克臨刑前的時間被神恩賜延長至一年之久,而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余準借著列車班次為自己延長了一小時的作案時間。其中,《沙之書》對于無限與有限概念之間矛盾關系的探討尤為引人注目—它既占據著有限的空間范圍,又如同恒河之沙般無窮無盡,與“迷宮”的意象趨于同構,都打破了線性的時序,指向了永恒的輪回。總而言之,博爾赫斯的作品中頻繁出現自我參照及互文現象,并未削弱其藝術價值,反而構成了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特色之一。這些表面上看似雷同或重復的情節設計,并非毫無意義的簡單復制,而是為了達到作品間相互詮釋、彼此照亮的效果,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在寫作技藝上不懈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