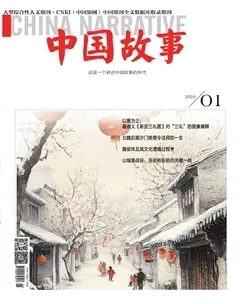刑名的懸解
【導讀】王夫之援儒入道,重解莊子,將儒家思想注入《莊子·養生主》之中,對其做出符合儒家傳統君民關系思想的重大改造。這一改造就形而上來講,必然要牽涉到天人關系,但文本中并未直接描述天人關系,而是透過刑名關系與形神關系顯示出來的,刑名關系牽引出了天人關系,形神關系才直接彰顯了天人關系,王夫之極力凸顯神的重要性和不滅性,就是要突出與神等價的天的主宰性和永恒性,進而引申出君的絕對性和至高無上。由此可見,君民關系是天人關系的現實表達,而君又是重中之重,倒懸與懸解皆依賴于君主一人,因此,君民關系中關于存在與意義的三重倒懸是中國古代政治結構建立的根本,也是王朝更迭、循環往復的癥結所在,倒懸是帝制時代的常態,懸解則是封建時代的變態。
《莊子·養生主》中的“養生主”有兩種解釋:一是養“生主”,存養生命之主,即形體;二是“養生”主,主要探討養生之道,養生的要旨在于存養精神,而“養神的方法莫過于順乎自然”。這兩種解釋被認為是《養生主》一文中要探討的兩個面向。
《養生主》篇幅不長,但哲學意蘊豐富。人生有涯而知無涯、“緣督以為經”、 庖丁解牛、右師之介、澤雉樊中、“秦失吊老聘”、薪盡火傳……這一系列寓言和故事構成了《養生主》的整個文本,歷代名家也對其多有注釋。郭象總括其為“夫生以存養,則養生者理之極也”,主張養生之道;朱子認為“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對其多有批評之意;王陽明則表示“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要求將養德與養生統一起來。
王夫之認為“養生”就要防止危害身心的三重刑罰,既有身體發膚的形體之刑,也有功名利祿的人世刑罰,亦有使右師獨足的天刑。刑名關系直接涉及天人關系,天人關系則是刑名關系的哲學表達,而天人關系又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和社會基礎上產生的。在古代,所有關系中最要緊的就是君民關系,君民關系就是天人關系的現實投射,君民關系在現實中又有著存在與意義的三重倒懸。王夫之與同時代的思想家力圖解除這三重倒懸,恢復三代圣王的君民關系,實質上就是要重構天人關系,拉近天人之間的距離,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王夫之的一系列觀點要求改變君民之間絕對懸殊的現實境況,改善君主治下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狀態,使得“民重君輕”的民本思想不至于淪為空談,帶有一定的啟蒙色彩。
一、生命的三重刑
王夫之按照自己的哲學脈絡和思維邏輯對《養生主》進行了重新解讀,認為有三種刑罰對生命造成了戕害。
(一)形體之刑
他首先指明了幾個重要概念,并點明主旨:“形,寓也,賓也;心知寓神以馳,役也;皆吾生之有而非生之主也。”這表明形體或身體是寓所,是賓位,居于次要地位,心知則是寓于神中的,這也就意味著心知與神是緊密相連的,而形體與心知都是生命自有的,并非是生命的主宰與核心,這里其實已經暗示了神的重要地位。首段最后一句說:“養生之主者,賓其賓,役其役,薪盡而火不喪其明;善以其輕微之用,游于善惡之間而已矣。”“養生之主者”能使身體、心知與精神各安其分,各得其位,那么“生之主”就應該是“性”,只有依靠人從天那里所稟受的本性,才能有如此清楚明白而又自然妥帖的安排。“性”又是運動變化的,能夠“游于善惡之間”,這就是說,王夫之并未單純地繼承單一同質的性善論、性惡論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層次分明的性三品論等人性論觀點,而是認為人性會有所變化,不能僅進行先驗預設,而是要更多地考慮后天因素,與習、情等要素結合在一起加以探討。
身體之性不只是個體之性,更是與社會聯系在一起,人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而存在,身體也是處在社會空間之中,社會的層級結構和穩定形態都要求名利與刑罰的雙邊制約,以確保社會的運轉與發展。因此,身體之性就具備了社會屬性,從這一角度來講,社會之刑就是形體之刑。而身體之性又是與天關聯在一起的,緣督為經,“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天是無善無惡、超脫善惡的,由天貫徹到人,由天刑落實到個人,自然順遂,行止自如,天刑勝過人刑。
(二)名之刑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嬰,大善大惡之爭,大險大阻存焉,皆大軱也。” 這是在講刑名關系,大名與大刑纏繞之處就是善惡交鋒爭斗的地方,也是艱難險阻所在的地方,但刑名又是人世間不可避免的網羅,“避刑則必尸其名,求名則必蹈乎刑”。逃避刑罰必然趨向于功名利祿,求取功名利祿又必然會陷入刑罰的泥潭而難以自拔。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像庖丁解牛一樣,“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既“依乎天理”又“因其固然”,使得“名者自名,刑者自刑,瓜分瓦裂,如土委地,而天下無全天下矣”。天下雖然不全,但我之情乃全,我的身體沒有受到傷害,神完氣足,足以養天年而終余年。
(三)天刑
刑名雖有內在的現實關聯和事實邏輯,但也需要與外在超越領域——天相關聯,從而為人世間的刑名提供形而上學的基礎。右師之介乃是天之刑,而“名者,天之所刑也”,天之刑涉及天的維度,天之所刑的名與人間刑罰的刑就是人的維度,如此一來,刑名關系本質上就是天人關系,而天人關系隱喻的是君民關系。先秦諸子對于天人關系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天人之間的關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實際上先秦諸子并沒有進行明確清晰的論證,無論是孔子罕言“性與天道”,還是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亦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具有模糊性與含混性,都在實質上以一種微妙而靈活迂回的態度避開了這一問題。他們將天人關系這一需要論證的結論當成先驗前提予以論證,這無疑陷入了循環論證的怪圈。真正對這一關系予以證明與確立的人是董仲舒,他對傳統的天人關系進行了改造,提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的觀點,建立起了一套“天—天子—父—子(人)”的天人關系學說,其看似在建構天人關系,實際上在確認君臣父子的尊卑關系。王夫之承接了董仲舒的這一思想,“蓋天顯于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為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天人所不能違”,民眾依賴天或天的具象化——天子來生存與生活,而天子的地位是由天來授予的,那么皇權至上與皇位世襲也具有了正當性與合法性,天人關系或者君民關系也由此固定下來。
二、三刑的懸解
右師之介代表的是人的非常狀態,即一種殘疾缺陷的狀態,但這也是最壞情況下最好的狀態,“寧近右師之刑,勿近樊雉之名”,這種非常狀態亦是懸的狀態,對常人是一種困縛,“天懸刑以懸小人,懸名以懸君子”,這又將天與人結合起來,進一步分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又與善惡掛鉤,這就是從人的角度判定善惡,但王夫之又講,“然懸于刑者,人知畏之;懸于名者,人不知解”,就天的角度來看,刑名善惡的區別沒有意義,就人而言,則有知與不知的分別,這就要求懸解,解開約束,恢復常態,破除生死。
“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盡”是指個體生命的消亡,包括個人肉體和個體精神的終結;“火傳”則指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而非個體精神的存留。換言之,“薪盡火傳”是在講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的動態關系。個體小我融入整個宇宙大我之中,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思想境界,這樣才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這是一個宇宙論的講法,王夫之則從形神關系上立論,把天直接等同于神,那么人就只能對應于形了,“蓋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則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于形而謂之神,不寓于形,天而已矣”,人首先有形體,再有神的附著,形與神有先后次序的差別。形體是人存在的基礎,神則是獨立自主、可以脫離形體而存在的,但又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與核心。如果說形體構成了人的生存場域,確保了人類的存活與存在,那么神就建立起了人的生活場域,是主體間性產生的關鍵所在,使我與他人有了真正的區分,保證了我之為我的生存意義和生活意義。人的世界由物的世界轉化為事的世界,即不再是單純無意義的自然界,而是完全意義上的屬人世界。人來賦予這個世界意義,同時,人也賦予自身意義,力圖完成個體的人格化和社會化的建構。人不只是一個自然人,更是一個社會人。
天落實到人之上謂之性,此性“至常不易、萬歲成純、相傳不熄”,具有天的特性,而又“來去適然,任薪之多寡,數盡而止。其不可知者,或游于虛,或寓于他,鼠肝蟲臂,無所不可,而何可聽帝之懸以役役于善惡哉?”如此一來,各物自有其性,無所不可,不一定會拘泥于善惡。“傳者主也,盡者賓也,役也”,生生不息、傳之不盡的是性,燃燒殆盡的是形體和心知,換言之,形體與心知共同構建了性,性也能使“賓其賓,役其役,死而不亡”,“哀樂不能入”。
確立這樣的形神關系,對應于身心關系的重構,由非常狀態的身心關系轉向了常態的身心關系,也是由懸到懸解的轉變。那么,既然身心都是變動不居、有生有滅的,那么人性也是運動變化、日生日成的,因此,王夫之的社會歷史觀也是運動變化、不斷發展的,這就傾向于唯物史觀,具備了一定的唯物主義特質。
形神關系背后是天人關系,天人關系是君民關系的虛擬化、神圣化,君民關系則是天人關系的真實化、世俗化。王夫之在篇章中多次強調神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位置,“其神凝”“神雖王,不善也”,這實質上是在強調君的絕對地位和主宰含義。神為天,即君為天,君權天授的觀念依然籠罩在王夫之的頭腦中。以王夫之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階層所建構的話語體系,其話語對象是君主。他們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們要維護等級森嚴的封建秩序,自由、民主、平等這些理念根本無處容身。因此,所謂的“萬物一體”境界,更多地是針對人與自然事物的和諧共處,當然,也不排除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友善關系,但這不是平等,而是人際交往準則和社會交往規范在境界論上的升華與展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社會結構由平面化轉向立體化,就意味著階層分化,這已經蘊含著不平等了,但這種不平等也代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與進化。伴隨著封建社會一系列制度律例的制定,這種不平等就會被固化下來,所謂的平等只會體現為封建制度下的細節平等和技術平等,而不會顯現為完全的平等,平等就成為民眾所向往和追求的一個理念。
君民關系具備存在與意義的三重倒懸:
第一重是存在的倒懸。中國古代王朝常常扭曲了這樣一個道理:明明是百姓敬獻萬物以養君,卻被說成是君賜予萬物以育民,君民的供養關系被顛倒了過來。
第二重是意義的倒懸。孟子講民重君輕,從百姓之中誕生的君主應當為百姓做事。這種對上古圣王的政治幻想其實是一種經驗主義的邏輯倒推。寄希望于遙遠的古代社會,認定古代比現代更好,相當于要由已知達到未知,這就喪失了對未來的判斷能力。未來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自在之物,這樣的斷裂就使得我們走進了經驗論的死胡同。過去推論不出未來,因果鏈條就被解構了,這樣的幻想只能像泡沫一樣煙消云散。君主擁有絕對權威,予取予奪,掌握生殺大權,持賞罰之柄,戕害百姓,百姓居于弱勢地位,只能逆來順受,直到忍無可忍,改朝換代,如此,君民的意義就倒懸了。
第三重是存在與意義的倒懸。孟子言,“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面對殘暴不仁的君主,是可以誅殺他的,這不是弒君而是誅殺獨夫民賊。君的存在被意義遮蔽了,君不再是君,而是桀紂一類的獨夫,也就是說,政治意義上的君主存在就被取消了,君主德不配位,取而代之的是“一夫”。語言名詞上的轉換,表示意義代替了存在,但存在不是完全消解了,而只是暫時退場了,仍隱匿于事的場域之中,意義暴露在了人的眼前,占據了原來存在的位置。存在只能在意義的籠罩之下,成為意義的影子與鏡像。存在與意義是事物的一體之兩面,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意義遭到了抹殺,那么存在也就崩解了。看似是誅殺獨夫,其實就是在弒君,意義優先不能瓦解存在優先,誅殺獨夫和弒君本就是一事,但通過意義的改變和前置就賦予了弒君合理性,也就是實質上肯定了以下犯上、以臣弒君的合理性,這暗含了孟子對于社會現實“禮崩樂壞”的無奈接受。當然,孟子將這一合理性的程度與范圍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之內,但在實際的運用上,卻可以將之擴大化,為自身的不臣之舉(如清君側)辯護,存在與意義的置換在這一層面就有了充分展現。這三重倒懸是否也存在懸解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懸解的可能性取決于君而不決定于民。“民重君輕”“君舟民水”都是在以君為主的前提下展開的,在這種畸形的社會結構下,只能依賴于圣君賢相來達到懸解的暫時功效,而不可能真正地實現懸解,這是“王夫之們”難以掙脫的藩籬。
三、王夫之對《莊子·養生主》疏解的意義
從時代背景來看,天人關系源自君民關系的逐漸崩解與重新確立。天人關系形成與確立,需要社會土壤與現實基礎。先秦對天人關系的初步思考,是分封制度土崩瓦解和君主集權制逐步建立的反映。周代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宗法分封制,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步消解。這意味著個體不再被束縛在嚴苛的血緣宗法制和等級制下,而是直接敞開,面對世間萬物和天地。這種轉變是“禮崩樂壞”的精神開端。人一旦在現實中不再直接面對等級制度所要求的規范和約束,就會自然地將目光轉向天地。從這一角度講,先秦諸子將人的目光從自身轉移到了外在的客觀世界,這才需要考慮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即人與自然之天的關系。但先秦諸子所論述的“天”又絕不止自然之天一種,更有意志之天、主宰之天,等等,這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一般而言,我們最開始認識的天應當是自然之天,就像泰勒斯所認識的水一樣。這個水可能是河水、江水、溪水,但不太可能是抽象的水的概念。因為這種抽象的邏輯思維方式,直到巴門尼德建立起形而上學本體論時才具有。泰勒斯說“大地浮在水面上”,這明顯是對城邦情形的現實刻畫。但水是萬物的本源,即萬物都在水中循環、往復、生成、變化,這是一個通過觀察而歸納總結出的理性結論。同理,天的多重含義是由自然之天引申出來的,經過長期的發展與演化,天最終被固定為中國哲學的最高范疇。宋明理學中的理學與心學都將天作為自身理論的終極依據,這其實是一種思想的慣性,代表著中國的文化早熟。文化早熟的根源在于政治早熟,政治早熟是由于帝制時代興起。帝制延續了兩千多年,文化包括文化的核心——哲學,其基本架構和思維方式也就沒有發生根本轉向。
誠然,朱子開辟了儒學的新方向,陸王(陸九淵﹑王守仁)拓展了為學的新路徑,但最后的落腳點都是在道德上。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這種基于道德理想主義的哲學與文化,注定了中國哲學是境界論,即強調個人品質修養和道德境界提升,披上了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但這只是表象,實質上,這種境界只能凝結為個人的境界,絕對不能上升為群體的清醒意識判斷。根據“德必配位”的傳統,孟子說人人皆有堯舜之性,人一旦實現了先天具有的堯舜之性,那么也應當擁有堯舜之位,即天子之位。如果人人都實現了堯舜之性,那么人人就應該具有堯舜之位,但這又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暗含的是一種政治結構的扁平化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這是集權君主無法忍受的,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無法容忍的。
因此,后世哲學家對人的本性加以收縮和限制,不再從政治上立足,而從個人的道德人格入手,提倡道德圣人,鼓勵個人存心養性以臻至品德圓善完滿,以期維持社會秩序穩定和社會結構穩固。因此,我們所說的天人合一不是絕對的、永恒的宗教式合一,而是相互對待、相互成立的對象化統一。
四、總結
王夫之對于《養生主》的闡釋既立足于莊子的文本,又糅合了自己的思想與觀點,引儒入道,“以儒解莊”,以儒家思想來解釋道家學說,通過刑名關系與形神關系展現天人關系,將“天之刑”和“神”對應于“天”,將“天之所刑”“人之刑”與“形”對應于“人”,揭示了天人關系的至高境界——天人合一。這種合一并非絕對同一,而是對象化的合一。因此,天人關系實質上是君民關系的哲學表達式,使君民關系具有了形而上的基礎,解釋了君民關系何以可能。而就形而下的角度而言,君民關系是天人關系的現實刻畫和直接依據。君民關系的三重倒懸(存在與存在的倒懸、意義與意義的倒懸、存在與意義的倒懸)是天人關系在封建帝制時代倒懸的有力證明。
王夫之希望解除這種倒懸的狀態,給予百姓更多的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但囿于時代而又無可奈何。因為懸解的完全實現必須要消解掉君民關系,徹底摧毀封建制度,讓所有人在法律地位上平等,這是君主與士大夫絕對無法接受的方案。故而只能維持倒懸—懸解的動態平衡,而不能收到撥亂反正之效。到了近代,外部力量的刺激打破了這一僵局,為傳統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 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2] 郭象,成玄英. 莊子注疏[M]. 曹礎基,黃蘭發,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1.
[3] 朱熹. 朱子全書:第23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第一冊[M]. 北京:線裝書局,2012.
[5] 王夫之. 王夫之全書[M]. 長沙:岳麓書社,2011.
[6]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7] 聶敏里.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臘哲學史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