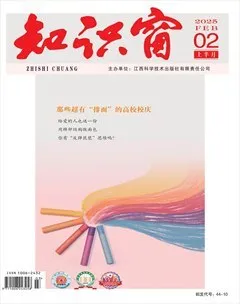穿越山海,見字如面
“這是我在朋友手里搶到的最后一張明信片,它是在卡姆登市場買到的,那里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等你來了,我帶你去玩。”2024年收到的第一張明信片來自我的姐姐。當知道姐姐寄了一張明信片過來時,我計算著明信片的到達時間——從英國倫敦到中國重慶,明信片應該會在路上航行兩個月,于是,在一個傍晚,我走進了學院的收發室。沒有人通知我,就是在冥冥之中,我感覺它靠岸了。
孤零零的一張明信片,混跡在眾多信件中,但我站在收發室的門口,便遠遠地瞧見了繪制著玫瑰色的畫的它。當我拿起它,看見正面寫著姐姐在英國的寄件地址和我的收件地址時,心中還翻涌著些許不可置信,和我手掌一般大小的明信片,真的漂洋過海來到了我眼前。我也曾與南京的筆友互通過書信,可惜在我寄出第二封信后,筆友就不再給我回信。我對給陌生人寫信的熱情就此消散,只每年給自己寫一封電子郵件,寫給一年后的自己。
我很久沒有見過姐姐的字了,在日常生活里,我倆和絕大部分人一樣,已經不太會用手寫的書信來表達自己了。由鍵盤敲擊而成的方塊字和語音實時輸入的語句,覆蓋了我們交流的絕大部分時間。現代通信技術已經足夠發達,無論我們相隔多遠,有著多少個小時的時差,都能通過網絡,隔著屏幕見面。而手寫的書信,需要時間,也需要空間。
人們都說字如其人,我手上的明信片,筆跡娟秀,沒有一絲涂改的痕跡,看得出是姐姐鄭重地思考后,才提筆寫下的。我熱切地看著明信片上的字,似乎看到了姐姐寫字時的模樣——認真、柔情又帶著一絲狡黠。
我想起關于明信片的故事。據說,世界上第一張明信片是一位叫胡克的人寄給自己的,反面是他繪制的一幅帶有諷刺意味的漫畫,正面則貼著一張黑便士郵票。黑便士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郵票,郵票上印著維多利亞女王的頭像,且不像現在的郵票擁有便于裁開的齒孔。
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篇語文課文講了齒孔郵票的發明——發明家阿切爾在小酒館看見有人用領帶上的別針給郵票的連接處刺上小孔,郵票便很容易地被撕開了,而且撕得很整齊。學了這篇課文后,我用媽媽針線盒里的針刺過白紙,試圖自己制造一些“郵票”。
現在想來,明信片的誕生頗具波瀾。顧名思義,明信片是不用信封封裝的,明信片正面除了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個人信息外,所寫的簡短通信內容也暴露在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并不習慣公開自己所書寫的內容。直到1869年,世界上第一張官方發行的明信片從?奧地利寄往奧匈帝國。從此,那些可以公開傳遞的信息開啟了另一種表達模式。潔白的信箋上,短短幾句話便可以將情誼說滿,且寄信人能自得地將這份情誼展示給所有能接觸它的人,將兩人之間原本私密的對話,敞亮地、自如地向世人宣告。
人們總抱怨紙短情長,但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本就不需要長篇大論,“今晚的月色真美”足矣;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也不需要殫精極思,“我想你了”足矣;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更不需要華麗辭藻,“等你來河邊一起散步”足矣……
我輕輕摩挲著明信片上的字跡,一段文字,航行了兩個月,帶著寄信人的溫度和心意,來到我的身邊,最終停靠在了我的手心。在這兩個月里,我也曾認真地期待它的靠近。
無論現代的信息傳遞技術發展得多么快,將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遞變得多么便捷,明信片帶來的浪漫永不凋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