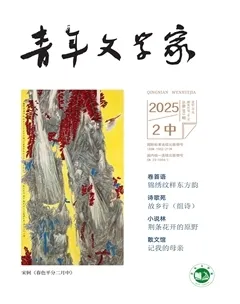命運波折與詩路探索


香菱是《紅樓夢》中命運極其悲慘的一位女子,曹雪芹刻畫出來的香菱形象有著立體鮮活的性格,由此投射出其復雜且具有多層次性的心理。香菱心理想法與行為標準主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眾多外部因素強烈向內擠壓著香菱,讓這位本就脆弱的女子更為謹慎,最終以逆來順受建立起自身防御機制。分析香菱的人物形象可以使用弗洛伊德著名的“冰山理論”,本文將從其“冰山理論”所包含的“本我-自我-超我”三層心理結構以及“意識-前意識-無意識”三層意識結構來分析香菱的行為沖動與內心傾向,在“冰山理論”精神分析的視域下對香菱人物形象作出更為全面立體的分析,對于用現代理論研究《紅樓夢》的多元人物特色很有價值。
一、命途多舛—“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層折射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指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構成。“本我”是生理的理性的自我,是無視道德標準與社會價值的無意識自我;“自我”是理性的自我,要根據實際生活中外界種種因素而滿足自己的渴求;“超我”負責監督本我,要通過壓抑本能來讓自己生活于現實生活中,注重“我應該要做什么”,用社會道德倫理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三者共同來實現人格的構成,并且相互調節來維持個體的正常生活。
香菱原名甄英蓮,是甄士隱唯一的女兒。在英蓮四歲時的元宵節當天,她同家奴霍啟看社火花燈時,因霍啟中途小解,將她獨自置于一戶人家的門檻上,以致她在看花燈時被拐走,她的悲慘命運也由此拉開序幕。英蓮被拐子養大后原本被計劃賣給馮淵,卻被惡霸薛蟠看中,薛蟠的奴仆將馮淵活活打死,然后強迫英蓮做了自己的妾室。嫁進薛家后,英蓮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改名:寶釵叫她“香菱”。之后,薛蟠離家之時帶香菱去大觀園,在此她經歷了人生中最為快樂的一段時光,即著名的“香菱學詩”情節。后薛蟠娶了彪悍的夏金桂為妻,夏金桂將香菱視為眼中釘,將其改名“秋菱”,并慫恿薛蟠毆打香菱。在冤屈難伸的境況下,香菱選擇默默忍受。薛蟠入獄后,夏金桂妄圖毒害香菱反被害。在這個過程中,香菱屈辱地忍受了薛家的凌辱,幸而真相大白。薛蟠出獄后香菱被扶正,后難產身亡,回到了太虛幻境。
香菱的一生命途多舛、悲劇色彩濃重。從香菱命運的悲歌中透視出生活外部壓力對她內心的強烈壓迫,致使她在不斷的挫折經歷中形成了逆來順受的保護機制。“《自我與伊底》中弗洛伊德認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部分構成動態連續的整體。彼此互相獨立又互相制衡,基于不同的情境對個體的行為進行影響。”(黃強、王璐穎《從人格發展理論的視角探索道德創傷的作用機理》)
香菱在外部壓力的作用下同樣彰顯出鮮明的“三我”人格架構:“本我”是一種生理性的本能,是不具有任何邏輯與社會價值的最原始的自我形象。香菱作為那個時代無能為力改變環境弱女子的代表,“本我”之中自然飽含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是人類共同的本能渴望。例如,在“香菱學詩”這一情節中,香菱對于詩歌的追求可謂達到如癡如狂的地步,寶釵曾對其打趣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除了周圍人對香菱行為的評價外,作者在描寫中還多次使用“怔怔”“癡癡”等詞,將其“為詩而狂”的形象通過神態描寫展現在讀者面前。探春請她入詩社時,她說:“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里羨慕,才學著頑罷了。”“心里羨慕”體現出香菱對以詩詞為代表的美好事物的向往,這種對藝術強烈與不懈的追求正是香菱內心深處純真無邪形象的外化體現。這種對美好事物本能的追求拋棄了一切社會價值與外界壓力,真實再現了其心底深切的情感渴望,這是香菱“本我”投射下的真實形象。
“自我”與激情的“本我”相對應,是具有決策行為功能的理性形象。香菱被薛蟠霸占為妾后,外部種種壓力因素讓其獨自尋找到了夾縫中生存的唯一道路,即用逆來順受的形象應對一切不公與冤屈。例如,在第八十回描寫道:“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叫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夏金桂如此刁難香菱,卻對自己的霸王丈夫不管不顧,甚至助紂為虐。本身地位低微,作為正妻的夏金桂又具有和其性格匹配的權威,再加之蠻橫無理的丈夫薛蟠,這些因素都讓香菱徹底失去與挫折抗爭的籌碼,因此隱忍溫順的妾室形象是香菱賴以生存的“自我”理性形象,這與學詩中主動忘我的她截然不同。
“超我”形象具有自我規劃的功能,“超我”的存在有助于監督管理自己的行為,這些行為由于“超我”的存在而受道德標準的規范,直指內心的精神追求。香菱所處的環境對她施加種種壓迫,為了生存她不得不委曲求全、逆來順受。但是她那份純真善良與頑強自尊從未改變,這種內心的“超我”品質與她經受的外部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是在“香菱學詩”這一情節中,香菱主動拜黛玉為師,她說:“我這一進來了,也得了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在學習過程中香菱謙虛恭敬,這是她內心純真友善的外化體現。同時,在對詩歌藝術真摯追求的過程中,無論自己的詩歌怎樣受到批評,或者周圍人怎樣對自己癡迷學詩的行為打趣,香菱依然無視外界干擾,一心追求更加完美的作品,這是她強烈自尊心的體現,是她渴望通過寫詩技藝的精進來追求自我進步的表現。這種純真善良與頑強自尊的品質是香菱精神上的超越,是追求自我超越的結果。
二、壓抑之詩—詩路探索中三層意識的交織體現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心智可以分為三種:意識、前意識以及無意識(又叫潛意識)。意識水平包含個體的思想與直覺,位于人類意識的表層;前意識包含記憶和知識的儲存,位于大腦的中層;無意識位于最深層,就像一座冰山潛藏于海底的部分,在暗處影響著個體的行為。“弗洛伊德認為,解決心理問題和理解人的行為需要深入探索潛意識(無意識)的層面,以便揭示隱藏在冰山深處的沖突和欲望。”(寧亞菲《愛的時候不必撒謊—弗洛伊德“冰山理論”視域下〈我們八月見〉解讀》)對香菱來說,她在學習詩歌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出這種觀點,為讀者呈現出前意識與無意識下的香菱。
首先,意識層面,香菱對于詩詞藝術強烈的追求與精益求精的態度是她渴望提升自我的思維體現,這種熱情主動的行為是表現在外界的最直接的行為,投射了香菱認真好學、渴望進步的年輕女子形象。香菱向黛玉學習的過程中明確體現出她對知識和藝術的鉆研,即使身處困境、生活苦難、歷經多重挫折,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泯滅她求知好學的心。她希望通過藝術層面的追求來豐富自己、提高精神境界。這是當時香菱的行為與思考,是明顯的且具有表層性的理性行為。
其次,前意識層面,前意識的存在是介于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個體不可能時刻體會到前意識的存在,但在特定事物的影響下會瞬間篩選并想起曾經的記憶。例如,香菱的生活十分悲慘,在家中受盡屈辱而無力反抗,來到大觀園后將詩歌作為自己發泄情緒的載體。這是她在精益求精、不懈修改詩歌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她渴望獲得尊重、渴望實現自我突破的體現,她希望自己能夠把握詩歌的命運,因為詩歌的好壞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發生變化的。這種精神層面的渴望是她在寫詩過程中受到過往傷痛記憶影響而彰顯出來的內在動機,雖然并未直接進入意識,但在學詩過程的引導下仍然浮現出來。同時,香菱拜黛玉為師,在黛玉的指導下苦思冥想精進詩歌,也是在內心渴望獲得黛玉和大觀園眾人的尊重與認可,希望通過詩歌記憶的提升來實現自己地位低微的突破,用藝術作為自己與其他“上層人物”平等交流的橋梁。前意識下香菱的行為既承接了意識層面對詩歌的追求,又體現出過往傷痛對自己行為的影響。
最后,無意識層面,“弗洛伊德認為夢是通往潛意識(無意識)的唯一途徑,人唯有在睡夢中方能將理性防備卸下,那些被抑制的、潛伏在潛意識(無意識)中的大量記憶和欲望才得以浮現”(寧亞菲《愛的時候不必撒謊—弗洛伊德“冰山理論”視域下〈我們八月見〉解讀》)。香菱在學詩過程中也受到了夢境的極大影響,如第四十八回寫道:“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做不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香菱在白日所作的詩歌均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她精心鉆研到癡狂的程度,但所得詩句仍有欠缺。這天香菱仍然滿心想著作詩,直到凌晨才完全睡下,甚至說夢話都在反復斟酌詩句。正如弗洛伊德所說,香菱通過夢境進入了無意識狀態,在這個階段下所有的理性都被拋棄,于是香菱夢到了這樣的詩句:“博得嫦娥應借問,緣何不使永團圓!”香菱詩句中描寫的仍然是前面斟酌的“月”意象,但這次的詩句被放置于“團圓”這一升華后的背景下,圓月當空,誰看了不會思念家鄉與親人呢?香菱在四歲被拐走的時候即是正月十五賞花燈的日子,當天的月亮也是如此皎潔圓滿。所以,這句被黛玉評價為最完美的詩句是在喚醒香菱無意識中曾經恐懼與悲傷的回憶后寫下的,反映了她在圓月之時被拐走,離家遠去思念親人渴望團圓的深刻情感。這種情感就像烙印一樣深深刻在香菱的腦中,以至于提到圓月就會在無意識中浮現出對過往傷痛的回憶與對家人團圓的極度渴望。香菱前段時日一直以來的癡迷斟酌、茶飯不思、日思夜想,這些為無意識的激發做了良好的鋪墊,進而通過夢境喚醒了她的無意識。她無意識中體現出的對于團圓的渴望體現在詩句中,形成了她對命運不公的有力吶喊與對生活苦難的強烈抗爭。
弗洛伊德還指出,無意識包括性本能與毀滅本能,而性本能即是內在驅動下生存下去的本能。香菱的三首詩體現了她不斷向內挖掘,最終以無意識狀態呈現出完美詩句的過程。例如,在她所作的第一首詩中,開篇就寫道:“月掛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詩歌首句第一字便點出所描寫的意象,這是最為表層的描寫方法,也說明此時香菱的意識還停留于最為表層外在的階段,即是“看月寫月”階段。香菱的第二首詩進步明顯,這次她寫了隔簾望月:“夢醒西樓人跡絕,馀容猶可隔簾看。”全篇無一“月”字,卻處處是月,可謂“看月不寫月”,這表明香菱已經從表層形式逐漸深入,探究月的本質,因此想出這一首反映月色的詩歌,這也是她意識不斷深入的過程:夢醒時分的西樓上已經沒有了人,香菱在大量閱讀前人詩歌的過程中形成了知識貯存,意識到寫詩要聯系一些記憶,于是她想到了圓月所象征的團圓,知識貯存和記憶兩者共同作用,這就是香菱深入到前意識階段的表現。而香菱的第三首詩直接是從夢境中獲得的,這種進入無意識領域的方式與弗洛伊德的理論恰好吻合。香菱在第三首詩中同樣沒有直接寫月,更沒有直接寫抒情主人公在看月,在這種“不看月不寫月卻處處表現出月”的藝術形式下營造出優美有深度的意境。“與第一首和第二首詩不同的是,它不是用 ‘外’在的事物比喻月亮,而是用月亮本身意象特點在象征‘內’的情感。”(張麗紅、何娣《源自潛意識深處的月亮詩—香菱“學詩”夢的精神分析式解析》)香菱在夢境中喚起的無意識,體現了她對于幼年的自己在月圓之時被拐走的恐懼以及渴望闔家團圓、家庭美滿的欲求,這種愿望是無法再實現的,在凝結了自身的生活經驗、喚醒了意識深層的記憶后,集中體現出她最為內在的生存的需求,這種需求與現實生活形成強烈的沖突與反差,也正因此被壓抑到大腦最為深層的無意識領域。
香菱的一生命運悲慘,幼年被拐、身份低微、家庭不幸、難產而死。她的一生經歷了身心雙重拷打,這些磨難為她的意識留下深刻的烙印。“香菱學詩”的情節也并非一個普通女子學寫詩歌的簡單故事,而是香菱不斷深入大腦、實現意識的三重交織后發出的心底里的吶喊,深深飽含了她對文學藝術等美好事物的追求,對提升自身價值、獲得尊重平等的渴望,以及思念親人、希望家庭團圓的強烈情感。在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論”下,我們看到了“本我-自我-超我”狀態下形象更為立體的香菱,也通過其學詩過程中展現的三重意識交織狀態感受到其無力改變環境但仍頑強生活的復雜形象。這種過人的才情、頑強的毅力以及內心深處對美的追求和對幸福的渴望,在一個個沖突矛盾中深刻地形成藝術上的巨大張力,鮮明呈現出這樣一位可憐女子的形象,讓古今讀者無不為之動容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