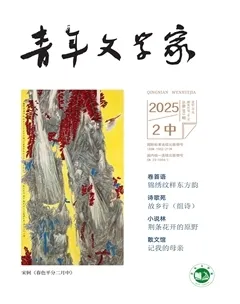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中的仆人形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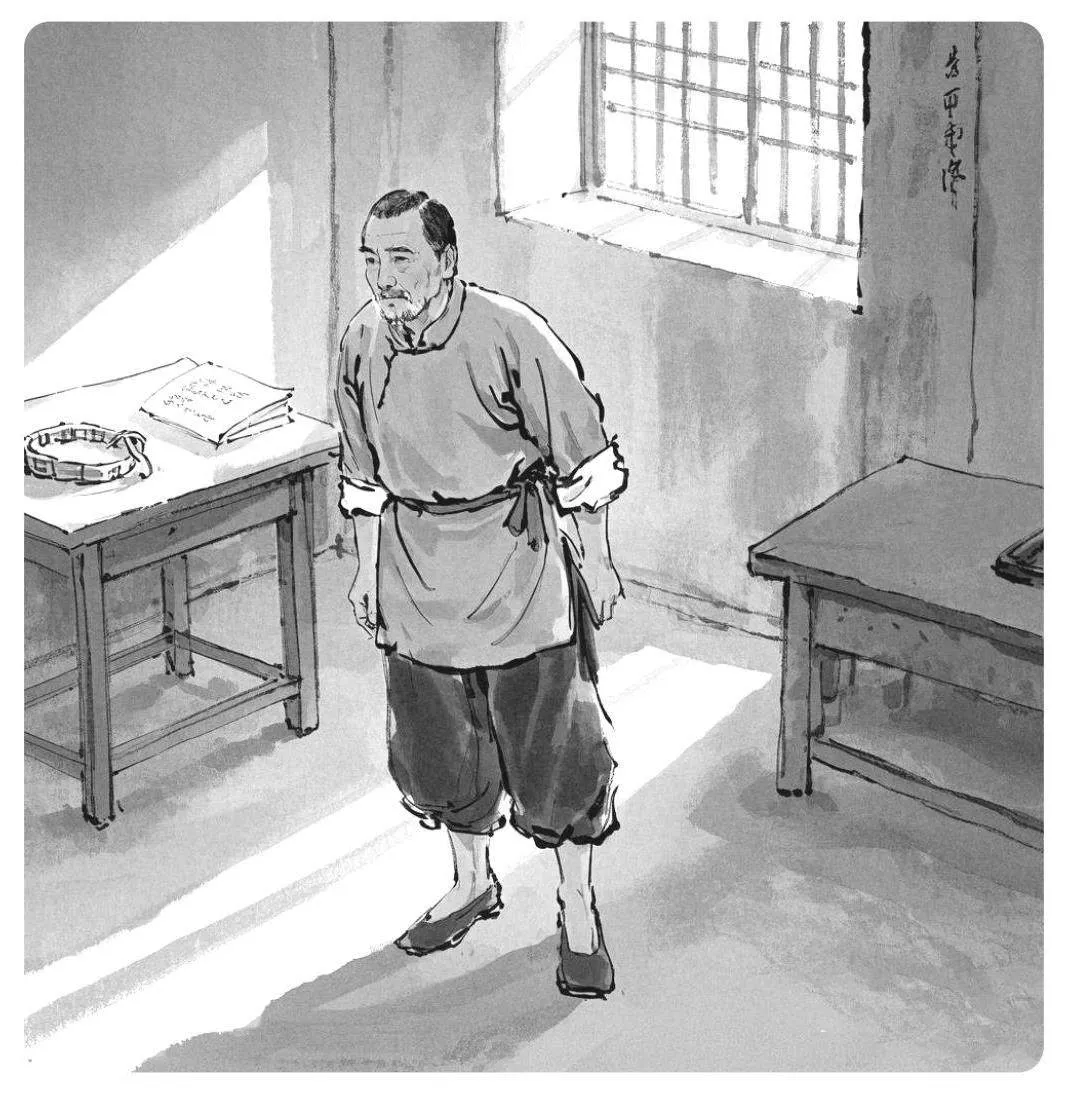
《說文解字》中“奴”釋義“持事者”,“仆”釋義“給事者”。《新華字典》中對“仆人”的解釋是“被雇到家里做雜事、供役使的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中的仆人形象眾多,形色各異,而仆人書寫也構(gòu)成了一種“群體觀察”。對比現(xiàn)代文學(xué)與當代文學(xué),由現(xiàn)代文學(xué)開啟的“奴性”闡釋與“奴性”批判也同樣在發(fā)生著變化。
一、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仆人群體及其悲劇底色
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仆人書寫常與苦難敘事相伴而生,呈現(xiàn)歷史、社會與人性多維壓力作用下的底層群體的命運悲劇、積弊深久的社會悲劇。仆人按照類型可以分為“貴仆”“惡仆”與“忠仆”三類。
“貴仆”表面上按照一套“為己”的生存邏輯行事,無意識地充當其所供養(yǎng)階級的捍衛(wèi)者,以上層階級賦予的微薄的權(quán)力壓榨比他們更低等級的人,如《北京人》中的陳奶媽,“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話就說,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駱賓基《老女仆》中的曹媽是俞家女主人最信任的老仆,一面討好主人一面又在主人缺位時以上位者自居。貴仆處于主人與更下層的仆人之間,極易耽溺于表面的風光,并無顛覆階級的能力或意愿。
“惡仆”遵循一套純?nèi)弧盀榧骸钡纳孢壿嫞柗铌庍`且為私利不惜以惡的手段貶害弱者,如《雷雨》中算計主家妄想賣女求榮的魯貴,《日出》中欺壓弱者、為虎作倀的王福升。惡仆品行卑劣,行事猥瑣,其惡在于展現(xiàn)了底層人民之間的相互碾壓,同時也展現(xiàn)了結(jié)構(gòu)性問題下的非道德生存法則的無奈。
“忠仆”常為馴順不自知的“愚仆”、軟弱無能的“苦命人”,是現(xiàn)代文學(xué)中數(shù)量最多、最典型的一類仆人。他們通常淳樸本分,對主家忠誠恭順,如魯迅筆下的閏土、長媽媽和祥林嫂,柔石《為奴隸的母親》中的春寶娘,老舍《牛天賜傳》中的四虎子,巴金《憩園》中的李老漢。他們的悲劇性在于對一套已然是歪曲了的社會秩序表現(xiàn)出絕對的、無意識的馴順,承受肉體與精神雙重規(guī)訓(xùn)的過程中既感受到強烈的悲哀,又無可奈何,而這種本意為求自保的乖順在一個良俗錯位的時代反倒使他們遭受最不公正的迫害,弱者的善在恃強凌弱的時代表現(xiàn)出如“稚子抱金過市”般的殘酷與悲哀。
現(xiàn)代文學(xué)中仆人書寫的悲劇歸根到底是弱者、平民與庸碌者的共同悲劇:普通人尚且難以憑個人力量顛覆積弊已久的階級秩序,更何況非自由身的仆人。平民悲劇根源是專制社會的結(jié)構(gòu)性困境。其一,經(jīng)濟制度導(dǎo)致了層級壓迫與“奴性”的依賴。例如,《日出》中黃省三為了微薄的薪水苦苦哀求李石清,李石清又同樣有自己的金錢危機,終日奉承巴結(jié)貴婦大亨,妄圖飛黃騰達。其二,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存在上位者對下位者的碾壓與旁觀。例如,《祝福》中魯四老爺一家對祥林嫂的苦難置若罔聞,《家》中高老太爺隨意指配丫鬟鳴鳳的婚姻。其三,階級觀念固化造成主仆心理結(jié)構(gòu)的雙向扭曲,前者習慣于凌駕與威懾,后者習慣于屈從與馴順。按照葛蘭西的“臣屬”概念,“專制的情況下必然從結(jié)構(gòu)上發(fā)展的智力卑下和順從遵守的習慣和品質(zhì)”(羅崗《“主奴結(jié)構(gòu)”與“底層”發(fā)聲—從保羅·弗萊雷到魯迅》)。現(xiàn)代文學(xué)揭露了最本質(zhì)、最無解、最徹底的一種“奴性”,即是自我意識的奴性。以《故鄉(xiāng)》為例,重逢后閏土已無法平視迅哥,他恭敬地喊“老爺”并非刻意恭維,“可悲的厚障壁”已重塑了他的氣質(zhì)人格。這也不禁使人質(zhì)疑童年回憶情節(jié)的真實性,迅哥視角作為帶有主觀色彩的兒童視角,又是否有意無意地避開了“總角之宴”中隱藏的“厚壁障”呢?
二、當代文學(xué)中的仆人群像及其文化象征意義
文學(xué)“怎樣說話”即作家“如何敘事”。當代中國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仆人,作家在塑造和把握仆人形象時常借助“作為既定前提的文學(xué)史資源”對仆人形象進行合理的想象—這即是作家需要抉擇“怎樣說話”(陳曉明《表意的焦慮》),當代作家挪移了仆人書寫的敘事空間,并重新解釋了主奴關(guān)系。
(一)民間性符號與歸鄉(xiāng)隱喻:仆人形象的文化象征意義
仆人書寫的敘事空間相較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生轉(zhuǎn)變:從《雷雨》中的資本家客廳、《日出》中的摩登都市交際花的酒局、《家》中的封建大宅,變成了《人面桃花》中的鄉(xiāng)紳閣樓,《文城》《活著》中的小地主家宅,《紅高粱家族》中的高密東北鄉(xiāng),以及《白鹿原》中的西北村落田壟。從文化表征的意義上來看,以鄉(xiāng)野空間為敘事背景體現(xiàn)了作家對民間文化的思考,仆人形象契合虛構(gòu)的鄉(xiāng)野時空輔助表現(xiàn)敘事的真實性。從立意的角度來看,鄉(xiāng)野空間寄寓了創(chuàng)作者的“歸鄉(xiāng)”情感沖動。敘事空間轉(zhuǎn)變同樣隱喻了社會結(jié)構(gòu)變動:隨著傳統(tǒng)社會框架的解體,主仆關(guān)系中顯性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轉(zhuǎn)為隱性。仆人不再是絕對的“被壓迫者”,而更近似小市民和農(nóng)民,與工作職責的綁定比與主人的綁定更牢靠:寶琛、喜鵲既是陸家的家仆,也是普濟村民;鹿三是“白鹿原上最好的一個長工”;羅漢大爺是單家酒廠的管事兼長工;田氏兄弟是林祥福家的管家,也同佃戶一樣在田間勞作。仆人在階級敘事與鄉(xiāng)村敘事之中扮演了一個恰到好處的中介形象。
仆人書寫中的歸鄉(xiāng)主題構(gòu)成了對知識分子歸鄉(xiāng)敘事的補充。知識分子的“歸鄉(xiāng)”基本遵循“在鄉(xiāng)-離鄉(xiāng)-歸鄉(xiāng)”的動態(tài)敘事邏輯,呈現(xiàn)視野變動下的文化反思。仆人與鄉(xiāng)野空間一體,在歸鄉(xiāng)敘事中扮演靜態(tài)的鄉(xiāng)村守望者:或如《紅高粱家族》中羅漢大爺“像忠實的看家狗一樣看守著我家的產(chǎn)業(yè)”駐守;或作為故鄉(xiāng)的象征承接游子歸鄉(xiāng),如《文城》中田氏兄弟帶林祥福“葉落歸根”。林祥福復(fù)雜曲折的“離鄉(xiāng)-尋找-返鄉(xiāng)”與田氏兄弟的“尋主-歸鄉(xiāng)”之途呈現(xiàn)出復(fù)調(diào)式的互文,并且在結(jié)尾處可以發(fā)現(xiàn)屬于林祥福的歸鄉(xiāng)敘事最終是在田氏兄弟的行動序列中實現(xiàn)的。
鄉(xiāng)野空間是承載與呈現(xiàn)作為底層民眾的仆人群體典型性格與生存智慧的最佳場域。現(xiàn)代仆人群體表現(xiàn)出的忠善沉穩(wěn)與象征傳統(tǒng)的大地的溫敦質(zhì)樸氣質(zhì)相契合,以鹿三和羅漢大爺為例:鹿三穩(wěn)成持重,沉默寡言,對白嘉軒來說意味著“鎮(zhèn)靜和抗御的力量”(林語堂著,郝志東、沈益洪譯《中國人》),他數(shù)次找鹿三傾訴蘊含著“回返至傳統(tǒng)道德文化根基處”的象征意義;羅漢大爺更是被塑造成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忠君奉主的民族英雄,日常“品行端方,忠心耿耿”,在被殘殺的時刻卻展現(xiàn)出了紅高粱家族式的堅毅血性,沉靜的忠與激情的勇在他身上得到了均質(zhì)呈現(xiàn)。
敘事空間轉(zhuǎn)換對應(yīng)著當代小說對現(xiàn)代性與民族精神的反思,“返鄉(xiāng)”情節(jié)的演繹則表征當代作家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普遍轉(zhuǎn)變:在現(xiàn)代意識的重新發(fā)掘下回到民間尋求民族性自我,利用本民族古久精神、深袤文化資源重鑄民族自我。
(二)錯位與救贖:當代文學(xué)對主仆關(guān)系的新解
古典文學(xué)中常有丫鬟為小姐、書童為公子代言的情節(jié),仆人替主人說不適合說的話,做不適合做的事情,他們的行動可被視為主人意志的延伸,主仆間存在著一種“雙簧關(guān)系”。當代文學(xué)在此基礎(chǔ)上對主仆關(guān)系進行了新的闡釋。
首先,當代文學(xué)拆解了主仆關(guān)系的內(nèi)部邏輯:階級壓迫的表象下也存在依附與黏合的屬性:“在現(xiàn)實處境中,被壓迫者一直是‘依附’于壓迫者的。也許他們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踐踏,甚至也意識到自己是壓迫者的對立面,但被壓迫者卻未必渴望‘解放’,他們可能更向往和認同壓迫者的一方,在那里找到‘做人(manhood)’的榜樣。”(李云雷《“底層文學(xué)”研究讀本》)主奴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同時產(chǎn)生壓迫與依賴的雙重效應(yīng),呈現(xiàn)為下位者自愿馴順心理結(jié)構(gòu)。鹿三對白嘉軒無條件的支持,田氏兄弟對林祥福的忠誠,反映了佃農(nóng)長工對地主的依附心理。《我的帝王生涯》展示了“依賴的悲劇”:被遣散的前代大燮朝宦官在等待召回中死于饑寒,王朝權(quán)力豢養(yǎng)出他們馴順的性格也令其深陷“無能的安全感”。
其次,當代文學(xué)在主奴關(guān)系中賦予仆人更大的自主意識,從“為他的存在”轉(zhuǎn)為“為己的存在”。鹿三殺害田小娥符合封建禮教的捍衛(wèi)者白嘉軒的立場,但又導(dǎo)致黑娃誤會與白嘉軒代鹿三受過的連環(huán)情節(jié),造成“主尊仆卑”倒反。《妻妾成群》中死去的雁兒梳著太太的圓髻出現(xiàn)在頌蓮的夢境中,暗示頌蓮對“雌競”的渴望而又畏懼的隱秘心理。
當代作家展示了主仆關(guān)系中“生命庇佑與心靈救贖”的二級性,主對仆的衣食庇佑彌補了仆人在經(jīng)濟上的貧瘠,仆對主的救贖和慰藉超越階級學(xué)識而散發(fā)出純凈的人性良善。
三、當代文學(xué)仆人形象及書寫意義的轉(zhuǎn)變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中寫道:“每一個時代的作家都有權(quán)利選擇他們認為最合適的表達方式,這里沒有對錯或高低之分……關(guān)鍵在于新的敘事模式是否更準確更生動地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的生活與感情。”當代作家以不同觀看視角、寫作立意賦予仆人不同的命運結(jié)局與精神內(nèi)核,有意避免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中臉譜化程式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將仆人書寫的視點凝聚在被宏大敘事掩蓋的日常瑣隙,將其從象征底層人民的類型符號還原為真實生活圖景中的人。
(一)底層敘事與平民文學(xué):啟蒙主題的延續(xù)
劉志權(quán)在《從“寫平民”到“平民寫”—試論20世紀末“平民文學(xué)”的研究思路》中詮釋了當代文學(xué)中反饋出的“平民精神”:“即一個人可能就社會地位及生活條件而言是平民,但就其精神上的強健來說,其實是精英的甚至貴族式的。”羅漢大爺、鹿三、喜鵲、燕郎等仆人的經(jīng)驗與視角全然是底層的,但他們的敘事卻能反映出“求生者的求勝”的意味。
當代文學(xué)揭示了仆人身份的曖昧的居中性。仆人介于自由平民與真正底層之間,處于顯性“侍奉-庇佑”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之中不困于口腹的需求。主人的破產(chǎn)可能會讓他們變?yōu)閾碛凶杂缮淼霓r(nóng)民,而也容易滑向真正無產(chǎn)無業(yè)的底層,如翠喜、田小娥,仆人身份仍然是懸置在他們“求生”命途中的悲劇隱喻。當代文學(xué)寫出了“仆者的求勝”,如羅漢大爺臨刑時超人的無畏英勇;鹿三在交農(nóng)事件中領(lǐng)悟到“自己說話”的自由;喜鵲擺脫了文盲的懵懂與蒙昧,在詩的世界獲得了精神性的救贖。無論是道德覺醒、知識覺醒還是自我覺醒,他們是在精神上跨越了仆者身份自行卸下奴性的一批人,走出“不成熟狀態(tài)”的一批人,與啟蒙者同為人生勝者。
仆人群體意識覺醒與啟蒙覺悟提升了普羅文藝中形而上層面的價值,“平民的辛勞、貧困、實際的生活方式產(chǎn)生了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和平凡性……正是這種平民精神生發(fā)出現(xiàn)代性,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催化力量”(楊春時《魯迅的貴族精神與胡適的平民精神—從現(xiàn)代性審視的文學(xué)思潮》)。
(二)從觀看到平視:視角與創(chuàng)作心態(tài)轉(zhuǎn)變
現(xiàn)代仆人書寫常以苦難敘事、社會問題敘事為底色,多采用知識分子與啟蒙革命者視角,難以避免“看客視角”與底層苦難保持著距離感。當代仆人書寫青睞平民視角。《人面桃花》中大半篇幅都是喜鵲、寶琛、老虎的視角中的革命,《白鹿原》同樣以鹿三的視角書寫了時代的變遷。書寫方式轉(zhuǎn)變反映了當代作家寫作心態(tài)與立意的轉(zhuǎn)變。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xué)校講》一文中曾呼吁“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當代作家不必再全部以投槍匕首式寫作敲醒鐵屋中沉睡的人,借助仆人視角反映底層在時代巨變中的彷徨。當代作家嘗試回答:現(xiàn)代性啟蒙這樣一個宏大的命題如何兌現(xiàn)在日常生活圖景之中,如果啟蒙事件是由一部分先進的人發(fā)起,那么最終如何在普遍意義上獲得推介,而敘寫普羅的覺醒相當于揭示個人在宏大時代、深久歷史、厚重文化面前如何尋找確定自我價值、完成自我啟蒙與精神獨立的過程。而這樣的寫法也反映出,當代作家以對隱性的、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變革的探討取代了對結(jié)構(gòu)性的社會階級問題的追問。
現(xiàn)代作家與新時期作家同處外來文化輸入的高峰期,影響現(xiàn)代作家更多是現(xiàn)實政治氛圍與憂患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所以在寫作中常懷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立意在反抗。當代作家擁有更自由開放的文化視野,更強調(diào)個人意識與反思意味。
仆人形象在小說中的敘事功能從展示社會悲劇與表征伏低卑劣的人性,到當代小說中擔當起文化故土、民間精神象征與現(xiàn)代性啟蒙意味的敘事意義。作家們書寫仆人形象的立意也從現(xiàn)代尖銳批判突出“憐憫與恐懼”,到當代小說中拆解奴性、書寫有血有肉的人。當代作家保留仆人作為傳統(tǒng)底層平民具備如敦厚淳樸、真摯良善的典型性格,也放大其生命活力與表現(xiàn)力,使其形象從類型化、符號化到差異化、個性化呈現(xiàn)。“只有所有人的人性化取代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一對矛盾:再也沒有壓迫者,也沒有被壓迫者,只有正在獲得自由的過程中的人—在這一時刻。被壓迫者才真正獲得解放。”(李云雷《“底層文學(xué)”研究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