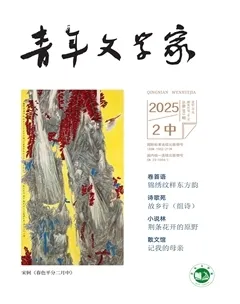以王維詩歌中的落花意象論“言有盡而意無窮”


無論《詩經》還是《楚辭》,其中都氤氳著花的芬芳。“人之生死,事之成敗,物之盛衰,都可以納入‘花’這一短小的縮寫之中。因之它的每一過程,每一遭遇,都極易喚起人類共鳴的感應。”(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花卉意象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元素,不僅象征著自然循環與生命變遷,更是深層次地反映著文人對于自身存在狀態的認知與感悟。而“落花”這一形象更是超越了一般靜物表層視覺美感與表意內涵,成為觸發情感共鳴與思索哲理的關鍵媒介。正是因為花的嬌艷,依照季節開放凋謝,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等諸多特點,使得文人騷客面對“落花”尤為憐惜。而“落花”作為另一種生命形態的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與“花開”有所不同的審美意趣。其他詩人筆下的“落花”,多半是傷春惜時的象征,但在王維的詩中,“落花”因為浸染著冷靜悠遠的禪思而顯得蘊藉玲瓏,進而需要讀者走進詩人構造的透徹境界,對詩歌進行再加工,自覺或不自覺地延長對詩歌的情感體驗,從而構成了“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滄浪詩話》)的美學體悟。而這樣的架構,在外在看來,體現了目擊與神遇后的有無相生;在內在層面,則展現了禪宗對自然與生命的深切關懷,以及瞬間即永恒的澄澈境界。
一、目擊與神遇
從外在表現來看,王維詩歌中的落花意象并非象征著同時代詩人筆下的“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劉希夷《代悲白頭翁》)對紅顏易老的悲嘆,也并非“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李白《聞王昌齡左前龍標遙有此寄》)的離別之苦。以上皆是詩人睹物而自然生發出的思緒,“落花”在詩歌中只是作為現實存在,是引發詩人們思考的物質前提,其所造之境是“有我之境”,而王維詩中的“落花”似花非花,是經由詩人目擊并對其進行藝術加工后的呈現。“落花”在其筆下蛻變為一種高度凝練的美學符號,作者、讀者與宇宙之間借“落花”達成了某種有效連接,這種美的表達已遠遠超越了前人面對自然變遷的感性反應,成了王維營造“無我之境”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目擊”并非現實意義上的視覺結果,而是“神遇”的一個手段。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闡述了“神遇”的概念,即“神遇不是感官感知,也不是言辯和思考,而是主體在無意識狀態下不斷解除感性和理性的束縛,來達到對主客兩方面的直覺體驗,并進而獲得高層次美感的心理過程”。他同時也肯定了自唐宋以來,莊子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與禪宗思想中“妙悟”進行了融合互滲。這一理論同樣可以視為《滄浪詩話》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另一個側面解讀。
目擊與神遇在王維的詩中通過有無相生得以表達,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王維《鳥鳴澗》)。王維只用了幾個短小有限的“拙語”,卻能帶給讀者無限的遐想。《滄浪詩話》中嚴羽評道:“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王維的詩即是如此,他的語言從不過分精巧雕琢,卻圓融玲瓏,首先因為他忠實于自己的文字,深切地觀照自身及自然萬物,并真摯地敘述于詩歌之中。王維不刻意追求辭藻的華麗,而是直接將自己的情感與觀察訴諸筆端。無論是描寫桂花飄落的寧靜,還是春山靜謐的空曠,他都力求保持一種原始的純真,避免過多修飾帶來的矯飾感。正是這種對純凈文字的堅持,使得王維的詩歌擁有了超越表象的力量,讓讀者在簡約直白之中體會到含蘊豐富的情感與哲理。
其次是禪宗“空”的思想,文字終究可以窮盡,而所需要表達的心緒卻是無窮的,于是,王維的詩句在有無、虛實、動靜之間形成了無限的張力。那么,詩人以何等的靜穆去捕捉桂花飄落的瞬間?又是如何聽到空山之中一片花瓣墜落的聲音呢?其答案正是因為人閑心定。故而可得,“桂花落”是詩人的“目擊”,而“春山空”則是他的“神遇”,前者是外在的具象,后者則是內在的感悟,它們共同傳遞出詩人對“有”與“無”的深邃認知。在其詩句之中一切物象已然被剝去了善與惡、美與丑、感性與理性,一切的“有”最終歸于“無”。
正是因為“落花”的精微意象,才能最大地發揮出詩歌中言語的力量,使得花落之撲簌,朦朧了山的存在,王維在有無的思考中漫游于天地,在動靜之間俯拾得禪心,將意境混融于天地之間,引導讀者同步邁進他所建構起的無限宇宙中去。
二、自然與自我
前文提到過,王維深切地關心自然,忠誠地將“目擊”轉化為“神遇”。如果我們對此種外在表現進行追根溯源,大抵要從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再到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最后再到世尊的“拈花微笑”。整體來看,“無論易、莊、禪(或儒、道、禪),中國哲學的趨向和頂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學”(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也就是說,儒、道、禪的共通之處在于其哲學追求的終點是美學的而非宗教的、虛幻的,而是以真切之心關懷自我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物我合一”的境地。
禪宗“不立文字”的傳統極大地解放了參禪者的思想枷鎖,鼓勵他們超越教條,關切個體自身的“悟”,直接從個體經驗和直觀感知中汲取真理。這種精神導向催生了禪宗獨特的修行方法,即著重于內在體驗而非外在形式,強調個體對自然界的細微觀察,以期在與萬物的親密接觸中獲得頓悟。在這一過程中,自然界的每一分子,無論是一草一木,抑或一花一葉,都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同時,佛教本就主張萬物皆藏有佛性,這意味著世間萬物在本質上并無高低貴賤之分,每個生命都值得尊重和關懷。這一信念進一步強化了修行者對自然界的敬畏之情,促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謙遜與慈悲之心,視萬物為平等的生命伙伴。這種思想在王維的詩中大量出現,如“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歸嵩山作》),以及“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積雨輞川莊作》)等。
而作為“花”這種嬌艷卻轉瞬即逝的意象,自然而然地使詩人以我之思寄以“落花”之飄零,可以說“落花”寄寓著詩人獨特的生命美學思想,既有對死亡,衰老這一永恒課題的憂愁,又有渾然淡泊的禪宗思想,同時也蘊含著盛唐特有的“哀而不傷”與悠游。由此“落花”成了王維與自然溝通的一帆舟楫,“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嚴羽《滄浪詩話》)。
王維在《秋夜獨坐》中寫道:“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果是花的另一種狀態,山果不僅與詩人當前的人生狀態有所暗合,皆是青春(花)走向成熟乃至衰敗(果)的結果。同時,這兩聯蘊含的生命意識自“落”與“鳴”中自然地流露而出。秋夜獨坐令人倍感凄苦,鬢已微霜則更添惆悵,但正是因為山果墜落的細微聲響,秋蟲鳴叫的熱烈掙扎,生命的意味便破詩而出。王維并不多言,其“神妙”留予讀者在詩境之外去捕獲,由此可見王維對生命與美的感觸之深刻。
王維的另一首詩《山居即事》中,詩人在創作“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時,自覺地將稚嫩的“綠竹”與半衰的“紅蓮”作對比。在王維的山水田園詩中,始終彌漫著一種靜美,并非一片了無生氣的死寂,而是在紛擾表象背后流露出的純粹的生命之音,這又何嘗不是詩人以自我觀照自然,又從自然獲得妙悟的證據呢?自然生生不息,周而復始,衰微的緊依著新生,而萌發的接續著敗落,這是一種無目的性、無意識的“大道”,于此就越發增添了詩人對生命的訝異與歡欣,以及靜謐的哲學禪思。
三、瞬間即永恒
“落花”這一形態極為短暫,自枝頭紛紛揚揚飄落至地面不過一瞬,但這一時間上的瞬刻,卻能包容整個人生與宇宙的永恒與浩渺。從禪學的視角來看,參禪在本質上是一種瞬刻的直覺感觸。在這一瞬刻,人不再將自身與萬物相割裂,而是與宇宙渾然一體。所有感性層面的感官限制以及理性層面的思維框架的束縛都蕩然無存,時間與空間的邊界也變得模糊不清,難以分辨。這一過程就像是從有盡的“點”向著無盡的“空”發生轉變,進而達到了南禪宗所極力推崇的“頓悟”境界。而這種“頓悟”境界與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闡述的“妙悟”的含義大體上是一致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王維早年因為家庭原因主要信奉北禪宗,后經過一系列社會變動,仕途的起伏等諸多因素,王維開始接觸南禪宗,并且將南禪宗的“空幻”“頓悟”等思想融入自己的詩中,進而促成了王維詩歌中“瞬間即永恒”的禪思,完成了由“有盡”向“無窮”的深刻轉換。
王維經常以畫家的繪心去捕捉瞬刻的畫面,在他的詩里有廣袤綠田驀地飛過的幾只白鷺,也有被月光一寸寸照過的青苔,但“落花”因為自身便隱含著由開到落,由動到靜等諸多意趣,使其成了王維表達禪思的更優之選。花朵的生命本就無比短暫,從盛開到飄散成泥不過一陣風雨,短暫到無法與世間堅韌物作對比,而其散落的飄飄灑灑中又洋溢著生的歡欣與死之靜美。“落花”入詩后,是由死的剎那抵達至生的永恒,而附著在其上的禪思便越發廖遠含蘊,如夢似幻。
王維在《辛夷塢》中寫山中盛放又凋零的辛夷花,“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山花生空谷,從不因無人欣賞便失去顏色與芳香,它熱烈地將自己的生命力展現給整個山谷,這是花的本性。于是,在無數次花開花落的瞬間里,王維仿佛觸摸到了花的內在本性。他從目擊到的花開花落這一現象出發,憑借神思與之相遇,從而由實在的景象得到虛靈的感悟,從動態的表象觸及靜態的本質,穿透了紛繁復雜的“幻象”,進而見到了常住不滅的永恒。在這個過程中,詩人自身的存在仿佛逐漸變得稀薄起來,宛如化作了溪澗中的一滴水,或者花蕊上的一粒花粉,彌散、融入這永恒的無盡之中,詩歌的意境也因此變得更加廣博開闊,充滿了寧靜祥和的氣息,這正是南禪宗“瞬刻即永恒”的思想在王維詩歌創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跡。
但在王維的詩歌中,“瞬刻即永恒”這一境界的宗教性質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學性質所讓步。王維詩中的落花意象,是詩人將情感與景色、目擊與神遇、主體與客體相互融合之后所產生的直覺感悟,最終指向的是“美”而非“佛”,是介于“學術境界”的“真”,和“宗教境界”的“神”之間的“美”的“藝術境界”。于是,在王維的詩中,“有盡”向“無窮”一次又一次進行突破,在“瞬間”中完成對“永恒”的構建。
于是,在其他盛唐詩人或為花謝花飛而傷春自憐,或為分離而憂傷,或為紅顏易隕而嘆惋時,王維則以詩人的忠實、畫家的敏銳、僧人的空寂去觀照這些“落花”,這些紛亂的花兒經由王維的“神遇”而超越了自身有限的絢爛生命,在王維的詩歌中獲得了永恒。也正是因為王維極為關注周遭的一切,帶著對感性認知的全面肯定以及對世間萬物的同等尊敬,才能將無限的情思、意蘊、禪趣融于有限的文字之中,寥寥數筆,就將這樣淡泊、寧遠的心緒,與人生、宇宙相連,營造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意蘊。可以說,在王維的詩中,“落花”已成了讀者們神馳的一個錨點,即便不參禪,不知佛理,讀者亦能在其有限的詩行中體會到靜穆永恒的空寂之美,這正是“落花”這一可親可感意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