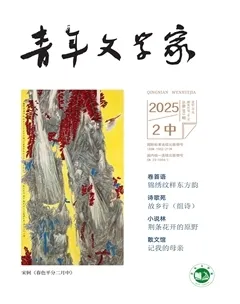論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贊美沉默》的敘事藝術
《贊美沉默》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于1996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主要講述了四十二歲的無名敘述者在英國生活二十多年后,由于故鄉新政府的成立,重新回到桑給巴爾看望家人,三周以后敘述者發現自己已經和故鄉格格不入,又再次重返英國的故事。在小說中,作者采用回憶錄的手法,將桑給巴爾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主人公在英國的二十多年的經歷融合在一起。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將二十年前的回憶與二十年后的現狀混合在一起,敘述者頻繁往返于英國和桑給巴爾之間也造成了空間位置的不斷變換,這種敘事時空的交錯縱橫以及獨特的敘述視角讓這部小說獨具匠心。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瑞典學院曾高度評價他毫不妥協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身處不同文化和大陸之間難民的命運。近年來,他的作品也受到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在《贊美沉默》中,他以獨特的敘事藝術賦予流散小說永久的魅力,傳神地刻畫了一個游走在母國和居住國,也就是桑給巴爾和英國之間的夾心人形象。
一、不可靠敘述者
敘述者是敘事學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敘事文之所以為敘事文的重要標志。不可靠敘述也是西方文學批評界,尤其是敘事學界討論最多的論題之一。在《贊美沉默》小說的第一部分,四十二歲的無名敘述者“我”回憶二十年前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并開始新的生活。第一部分屬于“我”的一個回憶錄式的敘述,這里面牽涉到了敘述自我和經驗自我,以及作為外聚焦的經驗自我時的敘述者是否為可靠的敘述者的問題。
對于不可靠敘述的定義,通常采用的是韋恩·布思對其的設定,即韋恩·布思在《小說修辭學》里首次提出的“當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范式(即隱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時,敘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作為韋恩·布思的高足,費倫提出了“疏遠型不可靠性”(estranging unreliability)和“契約型不可靠性”(bonding unreliability)。在這部小說中,敘述者就是契約型的不可靠敘述者。
由于這部小說中的時間線交錯縱橫,敘述者會站在故事內部對曾經自己所經歷的往事進行回憶,也會站在故事外部作為聚焦者講述他人的故事,所以對于小說第一部分的分析,即小說第一部分中的主人公是敘述自我還是經驗自我,需要借用里蒙·凱南對于敘述者的定義。敘述自我是回顧往事的我的視角,經驗自我是正經歷所發生事情的我的視角。根據里蒙·凱南的《敘事性虛構作品》,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的敘述自我眼光是外聚焦,同時,從相對于故事位置來看,聚焦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內部的。小說中有兩個故事,故事一是敘述者二十年前與愛瑪的聊天兒故事,故事二是敘述者父母的愛情故事。那么,故事一中的敘述者是內聚焦,是敘述者自我講述自己與愛瑪聊天兒的故事。但是敘述者的位置相對于故事二而言,變成外聚焦,所以在經驗自我上出現了外聚焦和內聚焦雙重視角。哈希姆、父親、母親是故事中的人物,是內聚焦。講述父母和哈希姆的往事的人,是作為外聚焦的經驗自我。所以,本文是探究作為外聚焦的敘述者,在描述故事二時,與隱含作者和作者的讀者之間的關系。
在閱讀文本時,作者的讀者會發現文本中存在大量悖論式的句子。在小說第一部分當中,敘述者對自己的求學經歷、家庭狀況,甚至父母這一代人的故事都進行了虛構,個人記憶出現了虛假和真實混雜的情況,目的只是迎合威洛比夫婦和愛瑪。但是,這種不真實的成分是可以讓作者的讀者清晰地意識到和感知到的,所以作者的讀者是可以明確敘述者的報道,闡釋等皆是虛假的,在這一點上,敘述者和隱含作者之間的距離就會縮小,也就是說,作者所塑造的主人公需要表現出這種謊言屬性,這是他作品主題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作者的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時刻了解到的信息。在小說第二章中,愛瑪與他閑聊時想要進一步了解他的童年經歷,他向讀者坦白,自己對愛瑪撒謊了,為自己設置了完美的家庭背景,父母輩的浪漫愛情,傳統的家庭模式以及其他細節,“我既沒有舅舅,也沒有父親。我根據自己的繼父,或多或少為愛瑪創造了這兩個人物”。有了這樣的人物設定,讀者們就會警惕敘述者的話語,因為“我”有可能是在杜撰故事,這些矛盾使主人公“我”成了不可靠敘述者。對于故鄉桑給巴爾和英國,“我”都沒有保持絕對的忠誠,在與母親書信往來時,“我”隱瞞了英國生活的真實情況,讓母親以為我在英國居無定所,勉強維持生活;在初次與威洛比夫婦見面時,“我”將童年生活和教育經歷進行包裝,以便維護脆弱的自尊心。敘述者不喜歡欺騙,卻在難以融入的英國和非洲社會中不得已選擇了編造謊言,這凸顯了他身為邊緣人的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他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向作者的讀者坦言,自己經歷的虛構性,以及自己編造的每個謊言,他不斷向隱含作者的倫理價值觀念靠近—流亡移民人的痛苦生活,也使得作者的讀者在情感倫理上不斷走進他—同情這位流亡的黑人知識分子,這也就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通過這種契約型不可靠敘述能夠達成的敘述效果和謊言背后獨特的沉默美學。
二、敘事時間的藝術
譚君強在《敘事學導論》中提出,文本時間不可能與真正的故事時間嚴格地保持一致。在《贊美沉默》小說的第一部分第二章,敘事文本的時間和故事文本的時間相互交錯,造成了一種過去、現在和未來時間復雜交織的場景,這樣的時間安排避免了情節的平鋪直敘,形成了一種更為復雜的敘述結構。文章時間的敘述有快有慢,給讀者一種閱讀沖擊。同時,錯位的故事時間如同時空中穿梭的碎片,代替了西方文學中傳統的線性敘事時間。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采取這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相互融合的方法,很好地展現了當代流散人群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
《贊美沉默》小說第二章中的故事時間是:(1)父親七歲開始的童年生活;(2)母親的哥哥阿巴斯逃亡;(3)母親的父母相繼離世;(4)父親的姐姐賣金鐲資助他上學;(5)父親十八歲來到鎮上準備讀師范學院;(6)露臺事件,哈希姆察覺異樣;(7)哈希姆打聽父親的相關情況;(8)哈希姆與父親來往次數增多;(9)父親回家找他父親說親事;(10)父親家親戚上門提親;(11)父親和母親舉行婚禮;(12)父親和母親開始新婚生活;(13)父親的姐姐上門蹭吃喝,求援助;(14)哈希姆處理妥當,給錢置辦;(15)幾年過后,本土惡霸當權,哈希姆靈活操作;(16)父親心態發生變化,父親和母親情感狀況失衡;(17)“我”出生;(18)父親的姐姐再次上門“幫忙”;(19)父親畢業,找到一份教書工作;(20)愛瑪與“我”的聊天兒;(21)二十年后,“我”回憶此事。但是,小說的文本時間并不是按照這樣的時間順序進行組織的。小說的文本時間可以用序號來表示:(2)(3)(6)(5)(6)(7)(8)(10)(11)(15)(12)(1)(4)(6)(7)(9)(10)(11)(13)(14)(16)(17)(18)(19)(20)。
如果將第一部分第二章的“我”與愛瑪的一次聊天兒定為某一個時間不明確的“現在”,那么第一部分是四十二歲的“我”回憶自己二十年前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求學并開始新生活的故事,這種回憶式的記錄,就是“將來”的事情,而“我”給愛瑪講述的是關于母親、父親以及舅舅哈希姆之間的故事,這就是屬于“過去”的事情,所以第二章節形成了三種時間混雜在一起的敘事結構。從敘事空間來看,“現在”所處的空間是英國,“我”與愛瑪開始了新的生活,而母親和父親的故事發生在非洲的桑給巴爾。所以,敘事時空交錯縱橫的結構特征生動呈現出身處錯位,流散狀態中移民的生活樣貌。
從時間距離的角度來看,敘述者拉長或縮短時間的跨度,使得時間距離長短不一,形成了敘事作品多種多樣的節奏。從第二章的開篇提到的母親的哥哥阿巴斯的逃亡,到母親的父母相繼離世,(2)(3)之間時間的距離是幾個月,在敘述中有明確地表明時間節點,“我母親的哥哥逃跑時,他們的父親還活著……他在人世的最后幾個月再也沒有提及兒子的名字……對于父親不久之后的離世,大家自然把責任歸咎于兒子離家出走”,所以,從阿巴斯的出走到父親離世大概時間跨度為幾個月,“幾個月后,他們的母親也出人意料地去世了”。(3)(6)之間的時間距離是五年的時間左右,文中提到母親的父母離世時,母親十三歲,舅舅哈希姆二十五歲,而哈希姆與母親露臺聊天兒事件是發生在母親與父親戀愛開始之后,“那時,我父親剛從農村來到親戚的那棟房子里安頓下來,他要到鎮上的師范學院讀書。一年前,他在十八歲的時候……”可知,露臺事件時父親十九歲,而從后文可以推斷出母親與父親年紀相仿,所以此時母親大約是十八歲。(6)(5)之間的時間距離是在一年左右。在這個段落中,時間的跨越可以達到二十年。“我對愛瑪說,我不太明白我的父親如何會變成這樣,為何這種依賴他人的恐懼會把他壓垮。對當時的愛瑪而言,一切東西……”這段話是結束“我”講述父母故事的節點,時間開始回到“我”與愛瑪的聊天兒當中。按照之前我們所設定的,將“我”與愛瑪的一次聊天兒定為某一個時間不明確的“現在”,那么“對當時的愛瑪而言”,敘述者用的不是對愛瑪而言,加上“當時”一詞,暗示此時的敘述者是站在了四十二歲的“我”的視角,回憶二十年前與女友愛瑪的生活,所以此時時間跨越到二十年后,四十二歲的我對當時的愛瑪作出的評價,下一句,時間又回到了二十年前,也就是“現在”的聊天兒當中,“她聽完之后不假思索地說:‘他恨自己。’”在一個段落四行之內,時間的跨度卻長達二十年。敘述時間的跨越長短不一,讓故事處在回憶與現實、真實與虛假當中,不僅讓受述者愛瑪充滿著好奇,也讓書外的讀者帶著疑問不斷閱讀和思考,增強了敘述故事和“我”移民生活的真實性。
三、內聚焦者
里蒙·凱南還提出了聚焦的各個側面的問題,她將聚焦分為感知側面、心理側面和意識形態側面來解釋聚焦的問題。從里蒙·凱南的定義來看,哈希姆、父親、母親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即內聚焦者。
小說第二章著重描寫了哈希姆和母親坐在露臺上閑聊,發現父親在暗處窺視的事件,在事件當中有關于玫瑰花香味的兩次描寫,呈現了哈希姆在發現父親的存在前后心理的變化。小說中以母親進屋端咖啡為時間節點,先是描寫了母親端咖啡前,哈希姆坐在露臺上,嗅出了母親種植的玫瑰花的香味,香氣幽微,是一種“淡淡的幽香”。隨后,哈希姆讓母親將咖啡端到露臺上。“他坐在她剛起身的墊子上面。當他坐下的時候,他透過眼角的余光看到什么在動,等他轉身察看的時候,發現有人從附近一棟房子的窗戶前移開了。”此時哈希姆已然發現父親的存在,并且察覺到他在暗中窺視母親。接著,“他坐在陰暗處,再次被玫瑰的香味觸動。只是這一次,這氣味讓他想到了敗壞和混亂”。短時間之內,同樣的玫瑰花香從幽香轉變為一種讓人感到惡心、混亂的氣味,不難看出內聚焦者的主觀性。第一次的玫瑰花香具有中立的特征,并沒有摻雜哈希姆的個人情感,第二次的花香已經和他當時震驚、失控和大難臨頭的感覺,氣急敗壞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密切相關。“我的母親具有了女人的身體……當有客人或朋友來訪,她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她們渾身散發著活力,各個歡快地嬉戲作樂……她們的香水和脂粉,她們的檀香和麝香,從熱情的肉體中呼之欲出,就是他坐在另一個房間,這也會讓他喘不過氣來。”這兩處透過聚焦者哈希姆目光進行的氣味描寫,是哈希姆對他人命運的絕對領導權受到動搖,心情憤懣、壓抑的表現。可見,哈希姆所認同的社會價值理念是,女性沒有自由戀愛的權利,婚姻之事應當由年長的男性決定,這也是父權制社會體系的產物。哈希姆作為當地的權貴,維持小鎮良好的秩序,而父親的出現,介入母親的生活,是企圖動搖哈希姆統治地位的代替者。所以,母親與父親的事情讓他感到意外,也讓他覺得一直處在掌控之中的母親,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脫離了控制,而代替哈希姆位置成為母親未來生活可能的支配者—父親,在哈希姆的印象里,他只是一個毫無身份地位的外來者。哈希姆認為父親無錢無權,一個來自農村的讀書人,不能成為動搖他地位的人。所以從這兩個帶有哈希姆主觀色彩的詞語中,可以折射出他的價值理念:擁有錢財和權力便可以掌控這個社會的秩序,知識分子和外來者都屬于這個社會的底層人物,女性也應是男性的附屬品。所以,這既是聚焦者心理側面的情感成分表達,也是從聚焦者的意識形態側面的表達,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僅僅通過花香的描寫,就映射出人物的心理和潛在的意識形態上的不同。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通過塑造流亡知識分子,展示了敘述者為生存而編織謊言的復雜性格特征。他借助內外聚焦與不可靠敘述等手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敘事風格。為真實再現流散群體的生活經驗,他突破傳統線性敘事模式,巧妙地將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于同一敘事框架之中。這種非線性的時間結構,結合時間跨度的靈活變化與空間位置的頻繁轉換,為小說增添了獨特的敘事張力與吸引力。此外,內聚焦敘述者的語言承載了豐富的信息與隱喻意義。這些敘事特色共同構成了小說持久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