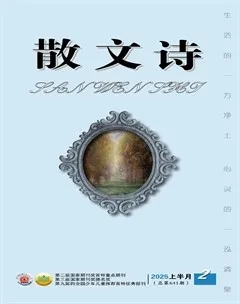場(chǎng)景
第廣龍 1963年生于甘肅平?jīng)觥,F(xiàn)居西安。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詩(shī)歌學(xué)會(huì)理事。參加《詩(shī)刊》第九屆“青春詩(shī)會(huì)”、《詩(shī)刊》第九屆“青春回眸詩(shī)會(huì)”。甘肅詩(shī)歌八駿。作品發(fā)表于《人民文學(xué)》《詩(shī)刊》《星星》《中國(guó)作家》《十月》《北京文學(xué)》《上海文學(xué)》《散文》等刊物,被《新華文摘》《小說(shuō)月報(bào)》《青年文摘》轉(zhuǎn)載。獲中華鐵人文學(xué)獎(jiǎng)、冰心散文獎(jiǎng)、敦煌文學(xué)獎(jiǎng)等,多篇文章被大學(xué)、中學(xué)生輔導(dǎo)教材、中考現(xiàn)代文閱讀題及各種文學(xué)選本收錄。已結(jié)集出版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十部詩(shī)集,十部散文集。
名 字
你愿意自己的名字被喇叭聲叫到嗎?我愿意。
我的名字,還在顯示屏上顯示,我看見了,別人也看見了。
我也愿意。
這是在醫(yī)院。
我早早就來(lái)了。就等著,盼著名字被顯示,被叫出來(lái)。
可以說(shuō),我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我的名字上了,眼睛看著,耳朵聽著,生怕錯(cuò)過(guò)漏過(guò)。我的名字,就是病人的名字。
是的,我病了,我到醫(yī)院看病來(lái)了。
那么多的名字,一大堆名字,一長(zhǎng)排名字,我都不認(rèn)識(shí),也被喇叭叫著,也在顯示屏上滾動(dòng)著。
這么多名字,什么時(shí)候才能輪到我本人啊。
就這,我也是提前一周預(yù)約,還要趕頭班車到醫(yī)院,在自助機(jī)上報(bào)到,拿到一張小紙條,上面有一個(gè)號(hào)碼,才有讓名字被喇叭叫,在顯示屏上出現(xiàn)的資格。
也許兩個(gè)鐘頭,也許一個(gè)上午,著急不管用,還不敢離開,我守在醫(yī)院的走廊上,守著我的名字。
我病了,我的名字也跟著病了。
只有名字被叫到,我才能見到大夫,才能對(duì)我的病做出診斷。
我?guī)е业拿謥?lái)到了醫(yī)院。名字和我分開了,分處兩個(gè)地方,叫到我的時(shí)候,才能合二為一。
與平時(shí)比,我在意我的名字,關(guān)心我的名字,里頭有一份沉重,壓在我的名字上,也壓在我的心上。
相遇相識(shí)
只要外出,總會(huì)遇見人。
在飯館,就是吃一頓飯,即便人滿了,和別人坐了同一張桌子,吃畢擦擦嘴就離開了,招呼都不會(huì)打。
在風(fēng)景區(qū),都在看山水,忙著照相,跟人面對(duì)面也留不下印象。在街上,人流擁擠成一個(gè)個(gè)疙瘩,就是碰一下,踩一下,分開也各走各的方向。
在火車上就不一樣了。
是那種慢車,坐一天一夜都常見。還是硬座,看窗外,看別處,也一個(gè)看著一個(gè)。一上午不說(shuō)話,起身出去,回來(lái)坐下,側(cè)身,拐腿讓行,就說(shuō)上話了。到了吃飯時(shí)間,雖然各吃各的東西,你一句我一句地說(shuō)著話已經(jīng)很自然了。
在旅館就不一樣了。
幾十年前,登記旅社,都是登記一張床。另一張床,是不認(rèn)識(shí)的人,卻要住在一起。別扭是一定的,不說(shuō)話反而不正常。天南海北吹牛,像是很熟悉了,看上去依然不是一家人。雖然沒有啥值錢的,還是把各自的東西看得緊。
在病房就不一樣了。
都是住院的,同病相憐,話題容易展開。照顧的人也是話題,誰(shuí)來(lái)看了,帶什么東西,也是話題。相處幾天,一個(gè)先出院,畢竟是在醫(yī)院這個(gè)特殊地方,不會(huì)舍不得離開。但給另一個(gè)說(shuō)上幾句安慰話是一定的。
這三種場(chǎng)所,相對(duì)封閉,人在其中,少有別的因素干擾,容易產(chǎn)生交流的愿望和行動(dòng)。
不過(guò),也是一別兩寬,很難再有掛念。遇見的是誰(shuí),叫什么,家住哪里,當(dāng)時(shí)就沒有問(wèn)過(guò),過(guò)后也無(wú)從尋覓,其實(shí)一開始就沒有進(jìn)一步交往的打算。
如果真的保持聯(lián)系,就成為一段佳話,一段緣分。
有一對(duì)夫妻,之前還分屬不同省,坐了同一列火車,坐在同一個(gè)車廂,因上廁所謙讓,就認(rèn)識(shí)了,就互相有了好感,進(jìn)而產(chǎn)生了感情,走到一起了。有對(duì)錯(cuò)嗎?開端像是注定的,結(jié)局誰(shuí)也沒有預(yù)料到,兩個(gè)人開始恩愛,后來(lái)吵架,廝打,過(guò)不下去,離婚了。旁人就說(shuō),還是了解不夠,畢竟一輩子的大事,這也太沖動(dòng),太草率了。這個(gè)看法,針對(duì)個(gè)案正確,但并不能適用于普遍。因?yàn)椋灰婄娗椋腋R簧睦樱部梢耘e出許多。
這屬于題外話了。
場(chǎng) 景
背景是工房,或者是街區(qū)的一角,像一幅貼紙畫。
應(yīng)該喧鬧、嘈雜,卻定住了一般,靜靜的,像是被遺忘了,像是流逝的歲月有意遺留下來(lái)的。又分明保持了熱度,是那種人體的熱度,是那種勞動(dòng)產(chǎn)生的熱度。
天氣在反復(fù)演化,之后,一只鷹無(wú)聲飛過(guò),翅膀是展開的,天空就穩(wěn)定下來(lái)了。云彩剛升上去,處于懸停狀態(tài)。云彩的形狀有的像奶牛,有的像風(fēng)車。扇形的光線,就從云彩上折射下來(lái),打在磚墻上,又彈射出去,改變了部分街道的顏色。磚墻是老舊的,是很早以前建成的。有多早呢,反正要是有人回憶的話得往上數(shù),數(shù)上起碼兩代人三代人,是那時(shí)候的人,一代一代傳下來(lái)的這個(gè)說(shuō)法。
其實(shí),墻后面,工房里面,一直是繁忙的。天車,機(jī)床,都在運(yùn)轉(zhuǎn);堅(jiān)硬的物體,被熔鑄、冷卻、切割、搬運(yùn);敲打的聲音,能傳出兩個(gè)街區(qū),讓那里的一棵樹發(fā)生搖晃。不過(guò)正是中午,就像按了一下開關(guān),就連電風(fēng)扇,也定格了一般,出奇地安靜。可以肯定,工人都下班了。
街區(qū)曾經(jīng)人來(lái)人往,似乎突然就騰空了。身影,腳步,都消失了,但不像遭遇了什么重大變故。好像就需要這樣一個(gè)時(shí)刻,人在其中,又不在其中。人是在變換的,每一時(shí)刻的人,都是不同的人,這一時(shí)刻的人不在了,這之前所有時(shí)刻的人都不在了。人又會(huì)回來(lái),還是那些人,那些面目熟悉又陌生的人。
只是,時(shí)間未到。
只是,一杯咖啡還沒有泛起泡沫。
那長(zhǎng)條狀的,長(zhǎng)方形的招牌,那上部是半圓形的門窗,經(jīng)歷了時(shí)間的做舊處理,還能再舊下去,讓招牌上的字跡成為歷史,讓門窗失去作用。門里沒有人進(jìn)出,窗戶沒有人在早晨打開,晚上關(guān)上。窗戶后面的那個(gè)少女,也不再?gòu)椙伲辉馘谙搿?/p>
這樣的場(chǎng)景,在異域,還是近前,我都會(huì)被觸動(dòng),長(zhǎng)久地注視,神情專注,仔細(xì)觀察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
我看不到一個(gè)人,又看到了許多人,他們我不認(rèn)識(shí),又非常了解。我曾經(jīng)在場(chǎng),曾經(jīng)是其中一員,把笨重的物體抱起來(lái),額頭上滾動(dòng)著汗珠。我穿著海藍(lán)色的工服,有兩個(gè)大口袋,一些部位染上了污漬。或者吹著口哨,從一個(gè)商店前走過(guò),我聞見了烤面包的香味,只是稍稍停了一下,似乎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趕著去完成,我重又邁開了雙腿。
不過(guò)此時(shí)此刻,我只是靜靜坐著,眼睛看向側(cè)面,身體盡量保持一個(gè)姿勢(shì)——
一個(gè)街頭畫家,正在給我畫頭像素描。他看看我,又看看畫板,抬頭,低頭,手中的畫筆在擺動(dòng),畫得專注又認(rèn)真。畫出來(lái)是什么樣子,我還不知道。背景肯定被省略了,看不到房子,看不到街道,看不到被動(dòng)什么。只有我占據(jù)了畫面,有些嚴(yán)肅,又略略露出笑容。我只是無(wú)法確定,畫像的時(shí)候,我是在畫面之中,還是在畫面之外。
陰 晴
熱鬧的場(chǎng)合,人散開,走的方向不同。回去了,繼續(xù)過(guò)著各自的生活。
啥味道都有,也是自己嘗出來(lái),自己咽下去。
黃昏的霞光里,這一家有爭(zhēng)吵,哪一家在喜慶,這不能交換。
也許過(guò)一天,風(fēng)雨降臨到另一家,那也得承受住。
柴米油鹽的日子,是重復(fù)的,又分出了不同。愛吃面的,也不是頓頓吃面。如果正在氣頭上,是沒有心情看一場(chǎng)電影的。
誰(shuí)家沒有個(gè)是是非非呢。就這么煩惱著,也愉悅著,構(gòu)成了生活的基本底色和成分。
沒有永遠(yuǎn)的歡樂(lè),沒有永遠(yuǎn)的煩惱。
世上的人,經(jīng)營(yíng)屬于自己的天地,順應(yīng)著變化的天氣和四季。其中有一些人,穿過(guò)艱難的峽谷,來(lái)到了光亮處,愿意把屬于自己的幸福,分出去,給認(rèn)識(shí)不認(rèn)識(shí)的人。
這些人的幸福,被放大了。
這個(gè)人間,涌動(dòng)著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