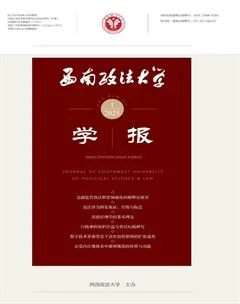實驗法理學的基本理論
摘" 要:
實驗法理學以思想實驗為基點,通過對廣泛的思維判斷進行經驗研究,來反思、深化法理學命題,是一種新興的法理學研究路徑。實驗法理學奠基于深厚的法理學傳統,從實驗對象、實驗方法和實驗取向三個層面探索了法理學研究的大眾性、科學性和反思性,因而是必要的。實驗法理學溝通了理性世界和經驗世界,具備充足的理論資源和高效的現實工具,因而是可行的。當今的實驗法理學呈現出一種總體議題、具體問題與本土語境之間的互動,既隨時代發展而不斷拓展,又限于學科品性須保持必要的限度。一方面,實驗法理學無法取代傳統概念分析和規范分析理論,其面對的仍是經典法理學問題;另一方面,實驗法理學又為法理研究與社科知識的結合提供了一條新進路,使其相互關聯、相互成就。總的來說,實驗法理學既面臨諸般挑戰,又具備廣泛的前景。
關鍵詞:
實驗法理學;直覺;思想實驗;科學性
中圖分類號:DF03"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5.01.04"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文章編號:1008-4355(2025)01-0043-17
收稿日期:2024-11-11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建構研究”(2023JZDZ013)
作者簡介:
于夢涵(2001—),男,河北石家莊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研究方法上,傳統的法理學長期依賴封閉的研究范式,未能有意識地從經驗角度形成一般化理論。盡管這些方法在解析某些法律問題時能夠提供有效的視角,并在理論、形式上顯得推理嚴密、體系精致,但在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和法律實踐時卻顯得力不從心,以至于所謂“一般化”的法理學命題常常受到經驗世界的廣泛質疑,導致價值與事實、理論與現實、技術性與大眾性之間發生割裂。因此,法理學研究亟須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以構建理論框架,填補法理學研究中的現實鴻溝。
科學的實驗方法逐漸融入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之中。在此背景下,實驗哲學、實驗經濟學和實驗政治學等學科獲得發展。與此相應,實驗法理學作為法理學研究中一個較為新穎的領域也在不斷崛起。實驗法理學的研究者主要通過喚起、調查不同主體對法理學命題及眾多概念的判斷及其背后的深層心理機制,來揭示、反思法理學領域內的種種爭論。在發展過程中,實驗法理學卻在獨立性、正當性和可行性等方面受到廣泛質疑,受到如專家優勢不足、方法落后、客觀性缺失等批評。
See Brian Flanagan, The Burning Armchair: Can Jurisprudence Be Advanced by Experiment?, 15 Jurisprudence 325,334-336 (2024).這一方面使得實驗法理學在法理學領域中的價值與意義未能得到彰顯,另一方面也導致實驗法理學的內涵與指向極為模糊,無法形成方法上的自覺,更無法凸顯其作為法理學研究范式的獨特性。因此,實驗法理學的首要任務是對自身在研究范式層面的證立,說明其確實值得研究、可以研究且已被廣泛研究。這是其融入法理學研究、實現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前提。
一、實驗法理學的興起與發展
在某種程度上,識別一個學科的最直接、最現實的方式就是探究該學科的學術脈絡與研究現狀,對應到實驗法理學的證立過程中亦是如此。通過梳理實驗法理學的興起與發展,來明確實驗法理學的內涵、傳統與議題,就成為證立實驗法理學的起點。
(一)何為實驗法理學?
從構詞的角度來看,“實驗法理學”由“實驗”和“法理學”兩個部分組成。“實驗”一詞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法理學研究中常見的“思想實驗”,第二層含義是對于“思想”所采用的“實驗方法”,意指通過系統的方法收集數據和檢驗法理學命題的過程,通常涉及實驗設計、變量控制和結果觀察,其強調通過實際觀察和測試獲取真實數據,而不僅僅依賴理論推導和抽象推理。對于“法理學”一詞的理解,應采取一種包容性的立場,其并不涉及某種特定的方法論特征,即只要聚焦“法理”的研究,并且涉及關于法律概念及解釋的概念分析和描述性問題,以及法學應當是什么的規范性問題,都可以被視為法理學研究。
“思想實驗”是“法理學”的基點:既然法理學追求一種一般性,那么這種一般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法理學研究的常見方法之一是訴諸心理層面的原初判斷,這種判斷既可以作為理論假設,也可以作為證據和理由,而引發這種判斷的往往是思想實驗。這些思想實驗可以是抽象的或具體的、實際的或假設的,目的在于激發一種法理學直覺,從而促進對法理學理論的獲得與反思。思想實驗通常作為概念分析和規范性研究的基礎,具有一種“元”地位。
See Roy Sorensen, Meta‐conceivability and Thought Experiments, in S. Nichols e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magination: New Essays on Pretence, Possibility, and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57-258.以關于道德的討論為例,考慮一個標準:一個行為被認定為善的,是因為它實現了預期的福利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法理學者如何評價這一關于善的定義呢?他們可能會將這一定義與湯姆遜的器官移植案例進行比較:我們是否會為了拯救其他五個人而殺死一個健康的人并摘取他的器官?答案往往是否定的。由此可見,思想實驗所引發的直覺反應,可以作為法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基點,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以此為依據,進一步反思和修正我們的命題。
“實驗方法”可以作為法理學的辯護方式:法理學家的直覺判斷作為法理學理論的基點,是否真的是穩固的?特別是在考慮法理學學科的一般性追求時,這一基點需要實現一種正當化辯護。這種辯護主要分為兩個層面,最直接的辯護方式當然就是一種普遍性的辯護,也即只要這種直覺判斷是公認的、普遍的,其就是正當的;另一種辯護方式是專家辯護,當面對大眾直覺判斷與專家直覺判斷的差異,就需要訴諸其他理由,證明專家判斷的優越性。
參見梅劍華:《洞見還是偏見:實驗哲學中的專家辯護問題》,載《哲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98-100頁。無論采用哪種辯護方式,都需要以對直覺判斷的反思與檢驗為基礎,都需要關注其普遍性特征。然而,許多法理學者,或因疏忽,或因自負,很少對這種直覺判斷的普遍性進行反思和檢驗。這導致法理學研究往往成為一種坐而論道的“扶手椅”(Armchair)式討論,缺乏事實性的證據支持,穩固性和實踐意義不足,進而導致各種法理學觀點歧義紛爭、莫衷一是,甚至影響了法理學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直覺判斷的普遍性檢驗必然呼吁一種實驗方法的介入,向更大范圍的人群尋求反饋,來反思、強化、重塑法理學命題。
欲確立實驗法理學,就必不能混淆其實質性內涵,所謂的實驗是對內在思想實驗的實驗,而不是外在的行為實驗。因此,可以將實驗法理學理解為一種以思想實驗為基點,通過廣泛的經驗方法,指向法理學的概念分析和規范性研究,并以此追求一般性的法理學研究范式。實驗法理學拓展了傳統法理學研究的疆界,為克服法理學研究中的局限性指明了方向,這一立場和意義同樣可以在實驗法理學的傳統積淀中得到印證。
(二)實驗法理學的理論來源
1.從實驗哲學到實驗法理學
實驗法理學的發展與實驗哲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具有同步性,且二者在處理如道德、指稱、同一性等問題上有所重合。早在古希臘時期,在法學作為哲學的附屬知識而并未從中獲得學科的獨立性時,哲學家就開始用經驗的方法理解人類、社會和自然的知識。例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就認為,事實才是最初的東西,需要以本性來理解、定義,進而平衡不同的哲學問題。
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0-21頁。
近代哲學中,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更多尋求的也是人類實際的心理事實,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思辨。參見[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115頁。培根、波義耳、牛頓和洛克等人建立了英國經驗主義傳統并引入了實驗哲學的概念。因而在傳統哲學理論中,法學、哲學與科學從來都是統一且不可分割的,其后隨著知識體系的進一步成長與分化,哲學的思辨氣息逐漸濃厚,這些學科才從包羅萬象的哲學學科中分化出來。
然而,即使哲學的思辨氣息達至一種復雜的、分析的特質,但其從未從自然科學的交錯中抽離出來,從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到蒯因,新一代分析哲學仍然保留了這份精神,其仍然注重常識、日常直覺與語言實踐。不僅在分析哲學中,在傳統的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形而上學中,直覺也從未缺席,如蘇格拉底的辯論、羅爾斯的反思平衡、蓋梯爾反例、特修斯之船,都不自覺地運用了直覺。實驗哲學正是要通過科學的實驗調查來發現哲學問題所依賴的各類直覺,或支持、或質疑、或限制這些經典的哲學問題,對應到實驗法理學研究中亦是如此。當然,實驗哲學在法理學領域的映射主要還是實驗法哲學的研究,在方法上對應的主要還是概念分析方法,這是實驗法理學的核心議題,然而,法理研究的廣泛性意味著實驗法理學不能僅僅從實驗哲學中獲取資源,其也不應成為實驗哲學的附屬工作,還應該立足于法學本身的現實主義傳統來獲得生機。
2.法律現實主義下的實驗法理學
實驗法理學的一個來源是法律現實主義傳統。法律現實主義強調法律的實際運作和社會效果。其核心觀點在于,法律不僅是一系列抽象規則,更應被理解為在具體社會和文化環境中實際應用的結果。法律現實主義者批判傳統法理學的形式主義,認為僅僅依靠法律文本的解釋無法充分反映法律的真實意義和影響。在霍姆斯看來,“正是對法院實際上可能做什么的預測,而不是其他什么虛偽矯飾之辭,方為我所謂的法律的含義。”
[美]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法律的道路》,明輝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49頁。因此,他們主張通過觀察與研究具體案例,從中了解法律的功能、效果及其對社會行為的影響。通過強調法律與社會實踐之間的緊密聯系,法律現實主義推動了對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批判與改革,引入了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方法,以此促進了“實驗方法”的產生。然而,傳統法律現實主義由于缺乏系統性和嚴謹的理論框架,往往偏重事后的觀察,而“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絕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
參見陸宇峰:《法律現實主義新論》,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97-98頁。,這使其理論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受到質疑。也正是這些缺陷引發了對“實驗方法”之取向的深刻反思。
法律現實主義發展至今,也逐漸開始重視一般理論的構建,最直接的體現便是聲勢浩大的“新私法運動”(New Private Law Movement)。在立場上,其主張形式大于實質,密切關注法律體系的系統化和類型化特征,因而貼合合法性和法治;在方法上,關注法律概念、范疇和論證,嚴格認定法律規則的例外情形,更具科學性和穩定性。實驗法理學和新私法具備廣泛共識,都認為大眾不僅僅是法律的客體,更是法律共同體的重要成員,都能夠在法律及其理論中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當代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賦予了實驗法理學以實質內涵和根本立場:其避免了傳統現實主義的不可知論和康德式的一元道德論,開始擁抱多元主體、多元價值和多元方法,既注重哲學式的概念分析路徑,也關注法學領域特有的規范分析方法,并力圖克服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的二元張力。從這一傳統來看,實驗法理學就不僅僅是實驗法哲學,還是一種實驗的法學方法論。
(三)名與實的結合:當代實驗法理學
事實上,僅就“實驗法理學”之名來說,其最早是由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弗蘭克在1934年提出,借以強調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等科學的方法進行法學研究。
See Jerome Frank,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New Deal”,78 Congressional Record 12412, 12412-12414(1934).其后貝特爾撰寫了以實驗法理學為主題的相關著作,尤其主張在立法和執法中科學方法的介入。
See Frederick K. Beutel, Some Implications of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48 Harvard Law Review 169, 169-197 (1934); Frederick K. Beutel, Some Potentialities of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as a New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57.在我國法理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田野實驗、計算機實驗、仿真實驗、行為實驗、神經工程實驗室的表述,但這些觀點的主要指向仍然是對個別的、具體的法律行為的評估和預測,其經驗性的主張只能算作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方法和材料,為法理學研究的實驗轉向奠定了基礎。但就實質而言,其對于思想的探討不足,缺少命題上的一般性,廣義上仍可以落入法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可能僅有“實驗法理學”之名,無“實驗法理學”之實,并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實驗法理學。
2017年10月,實驗哲學的領軍人物約書亞·諾布(Joshua Knobe)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舉辦的研討會上,探討了實驗法理學等概念的應用問題。
See Law Workshop: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https://cogsci.yale.edu/event/law-workshop-experimental-jurisprudence (last visited Oct. 9, 2024).2018年6月,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的法律、行為與認知中心舉辦了首屆關于實驗法理學的會議。
See Experimental and Naturalistic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 https: / / zrsweb. zrs. rub. de / institut / clbc / inaugural-conference / (last visited Sep. 30, 2024).至此,實驗法理學才脫離傳統法律實證主義的預測理論,尤其致力于法哲學問題的解決,獲得了學科上的獨立性。眾多學者在實驗法理學這一旗幟下,開始廣泛的實驗法理學研究。至此之后,實際從事實驗法理學的學者開始有意為自己樹立實驗法理學的標簽,實驗法理學的實與名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重合。而今,實驗法理學在議題和方法上都更為豐富,呈現出多學科融合、大數據技術應用、研究方法多樣化等發展趨勢,諸多學者投入對于法概念、因果關系、合理性問題、公民權利、內在觀點、人格同一性、損害、解釋、所有權等諸般問題的研究工作之中。也正因如此,布萊恩·弗拉納根(Brian Flanagan)才頗有信心地認為“法理學的未來是實驗的”。
Brian Flanagan, The Burning Armchair: Can Jurisprudence be Advanced by Experiment? 15 Jurisprudence 325, 340 (2024).
我國在實驗法理學的研究中雖占得先機,但整體關注度仍顯不足。早在2013年,朱全景教授就發表了《法學實驗論綱》朱全景:《法學實驗論綱》,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4期,第24-34頁。一文,作者以實驗哲學、實驗經濟學為比照,尤其關注了法學實驗的可重復化特征,在學術洞察力上絲毫不遜色于西方學者,但其后數年間,卻鮮有對于實驗法理學的研究。直至2020年,杜宴林教授發表了《法理學實驗研究的興起與中國法理學觀念的更新》杜宴林:《法理學實驗研究的興起與中國法理學觀念的更新》,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1期,第31-47頁。一文,才重新喚起了學界對于實驗法理學的關注:一方面,作者以獨特的視角關注了實驗法理學的發展動向,對實驗法理學的研究進展進行了概述;另一方面,這篇佳作可能僅具有說明意義,并沒有對實驗法理學的深層次原理作出批判性分析,且部分內容可能仍有待商榷。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實驗法理學研究沒有充足的資源,正如杜宴林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及的,我國的法律現實主義、相關裁判理論的研究也頗為豐富,法理學學科內部,孫笑俠、陳柏峰、郭春鎮、陳林林等多位學者早已通過一定的經驗方式對如直覺、認知、民意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也有非法學學科的學者采用合作的方式對廣泛的經驗問題進行了調查。雖然由于其立場和問題導向,很難將其確切稱作實驗法理學,但其勢必可以為當今純正的實驗法理學研究提供充分且鮮活的方法和原料。
二、法理學研究為何需要實驗
實驗法理學的正當性不僅應從學科發展的角度進行論證,還須從應然層面深入考量其在法理學研究中的必要性,旨在回答“法理學研究為何需要實驗”這一直接且關鍵的問題。
(一)實驗對象與大眾融入
做實驗就必須選定實驗對象,實驗法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大眾,也即實驗法理學考察的是更為廣泛的群體的法理學判斷。這一立場所面臨的最直接問題,就是為什么法理學研究需要一種大眾性?尤其在具備法理學專家的情況下,在法理學命題日趨抽象與精密的情況下,大眾對于諸般命題的理解為何仍然是必要的?
首先,大眾性保證了法理學理論的普遍適用。這種普遍性可以從兩方面進行理解,一種是理論上的普遍性,也即法理學理論與哲學理論相同。雖然對于理論整體來說,其并不需要大眾的直接理解,例如,我們并不會以大眾是否理解摹狀詞、同一性、權力意志等復雜理論來說明理論本身的正當性。然而,追溯、還原這些命題背后的根本預設,其通常還是一種直覺判斷,其穩固性就必須得到更廣泛的認同,需要被看作一種常識、共識或自明之理。另一種是實踐上的普遍性。大多數法理學理論都是以實踐為導向的,其直接地影響法律實施與法律適用,如所有權、承諾、侵權、合理性等理論需要在實際生活中面對最多數的群體,保證社會的普遍性預期。此外,在確定性要求和民主原則之下,對于法律文本中的眾多語詞,如蔬菜、武器、交通工具、金融機構等,也需要考量大眾的理解,追求一種通常含義,提高語言的嚴謹度、精確度和清晰度。諸般理論和概念一旦脫離了大眾的實際經驗和認知,就有可能導致法律的適用變得模糊不清,偏離社會的現實需求,甚至使法律在社會中失去其應有的權威和信任。
其次,專家的判斷也并不總是優于大眾的判斷。專家群體在很大程度上被賦予了更高的期待,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專家受到更為系統的專業訓練,具備更為深厚的知識儲備,也不易受到無關因素的影響。因此,專家判斷往往被視為一種理論權威,比大眾判斷更具優越性。這種優越性在自然科學領域自然是難以撼動的。例如,在數學中,抽象公式建立在堅實的數理基礎上;在醫療領域,各種處方通常依賴于大量的臨床試驗數據,這都使得自然科學的理論相對客觀和可驗證。然而,這種優越性并不能直接移植到法理學的研究中,因為在法理學中,諸般理論的最終證據還是體現為一種私人化的判斷,需要依賴于外部觀察、比較和反思。此外,廣泛的經驗調查表明,理論專家的直覺判斷在諸般問題上同樣表現出顯著且激烈的沖突。他們在認知過程中亦可能受到性格、順序效應、框架效應等認知偏差的影響。
參見曹劍波、王云卉:《實驗哲學調查普通大眾直覺的合理性》,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78-79頁。如果再考慮到法理學領域的專家概念并不明晰,法官、律師、法學家由于身份差異,又可能進一步產生迥異的法理學立場,那么專家判斷就更需要面對實驗調查的廣泛質疑。因而專家與大眾的理解并非簡單的優劣之分,而是各自存在對應的特性和局限性。
從本質上來看,“法實踐的正當性需求刺激著法理生成,法理在法實踐空間中證成并推進著法實踐。”
郭曄:《法理:法實踐的正當性理由》,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2期,第137頁。法理并不只是抽象的理論構建,而是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法理學及其相關的倫理學、政治哲學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它們共同反映了人們在社會生活和政治實踐中所形成的初步倫理觀和政治立場。實際的社會生活和政治互動讓人們在經歷不同的事件和沖突時,形成自我理解和認知,繼而產生相應的倫理和政治觀念。法理學的任務在于對這些觀念進行系統的反思和理論化,理解其背后的邏輯,分析其合理性與適用場域。一方面,在大眾的參與下,法理學摒棄了傳統法理學中的精英主義傾向,不預設任何身份、背景或階級的門檻,只要求所有參與者具備啟蒙后的基本理性能力
參見梅劍華:《洞見還是偏見:實驗哲學中的專家辯護問題》,載《哲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0-102頁。,法理之探求并非少數學者的專屬話語,而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過程;另一方面,所謂大眾融入,也并不意味著大眾性在法理學理論中占據支配地位,更不意味著法理學理論是一種少數服從多數的過程,與之相反,其注重的是專家和大眾在何種層面上可以互動,何以達成進一步的反思,何以獲得進一步的共識。以此立場,法理學才能真正反映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并在不斷的實踐中更新與發展。
(二)實驗方法與科學支撐
誠然,實驗方法被廣泛應用于自然科學領域,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通過控制變量、觀察現象和驗證理論來探索自然規律,這使其與“硬科學”理念密切相關。然而,實驗方法并非任何一門科學所特有,也并非一開始就存在。當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現有理論無法有效解釋實際情況時,引入實驗方法就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
實驗方法可以作為連接科學性和法理學研究的橋梁。關于科學性的話題,在法學研究中常常引發顯著爭議。在社科法學看來,法學需要符合一般科學的標準,尤其是在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論中,主張“對給定的外部標志和符號進行解讀”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本質》,王紹喜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頁。,強調實證研究在對現實的預測與調查中的重要性;在法教義學看來,法學的獨特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理解、反思和規范性論證上,需要追求法律平等而普遍地適用。
參見舒國瀅:《論法學的科學性問題》,載《政法論壇》2022年第1期,第155-159頁。現有的討論往往沒有將這兩種科學性結合起來進行深入分析,這限制了法理學研究的全面性,而實驗方法的引入恰巧可以為法學研究中這兩種科學性的充分對接提供橋梁:一方面,實驗方法通過系統性地收集數據和統計分析,符合一般科學的標準,增強了對法律現實主義的支持,突出了實證研究在現實預測與調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促進了對法教義學的理解與反思,使研究者能夠探索一般理論的適用性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實驗方法通過鼓勵跨學科的交流,彌補了傳統法學研究的局限,減少了法學界的爭議,增進了共識,證立了社科知識依然具有法哲學和法教義學方面的適用場域。
重復性是實驗方法科學性的基礎。在實驗中,通過嚴格控制實驗條件,明確研究對象及其現象之間的確定性關系,使得在相同條件下這種關系能夠反復出現,從而實現主觀假設與客觀現實、個別現象與實驗結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重復一個實驗必定會得到同樣的‘效果’,這并不是經驗得出的結論,而是先驗的必然。”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認識與興趣》,郭官義、李黎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頁。在法理學實驗中,實驗的可重復性不僅強化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也為深入理解復雜的法律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方面,需要通過消除偶然因素和干擾,揭示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之間的確定性聯系;另一方面,通過對法律現象的實驗研究,使法理學能夠精準檢視法律規范的適用效果及其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從而幫助研究者驗證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契合度,使其理論基礎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接受,增強其實踐意義和理論深度。
實驗方法通過引入量化研究和質性分析來達至這種科學的可重復性。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問卷調查、腦電測試等方法,通過系統性地收集數據,利用統計學分析對參與者的反應進行更為客觀的評估。這一方法不僅揭示了命題判斷的普遍性,還幫助識別出潛在的變量和影響因素,如性別、年齡和教育背景。然而,在進行量化研究時,實驗法理學也意識到在樣本選取和問卷設計中面臨著諸多挑戰,如語言翻譯的差異和樣本的代表性問題。為了解決量化研究的局限性,實驗法理學進一步引入了質性分析,通過口頭訪談、敘事研究和話語分析等方法,獲取參與者更為開放的回答,從而捕捉到更深層次的觀點和經驗。質性研究使實驗法理學得以深入理解參與者在特定情境下的認知與情感,而這些往往是量化方法所忽視的。通過將量化研究和質性分析相結合,實驗法理學一方面排除了影響理論建構的無關變量,解決了實驗可重復性難題;另一方面也更為深入地探究了法理命題的深層次理由,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參與者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最終實現了一種“對教義的非教義分析”
Matthew Mitchell, Analyzing the Law Qualitatively, 23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102, 104 (2023).。
(三)實驗取向與反思平衡
一般認為,無論是實驗法理學還是實驗哲學,其主要研究對象還是某類群體的直覺判斷,但這一觀點早已受到了客觀性缺失、概念模糊、穩定性不足等廣泛批評。因為在事實上,我們很難區分直覺背后有沒有深層次的反思因素,絕大多數哲學命題都是需要進一步審視的。
See 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Wiley Blackwell, 2021, p. 440-441.思想實驗不可能僅僅激發直覺而不促進更為深入的思考,專家的直覺也必然包含經驗性的反思,與其以狹隘、模糊的直覺概念來限制實驗法理學的研究場域,不如直接從更為多樣的判斷出發,關注直覺與反思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直覺判斷旨在推動進一步的反思,而反思則能夠塑造更精準的直覺;另一方面,反思指向的概念分析和規范分析成果,也有助于塑造更為優良的實驗,喚起更為精準、廣泛的直覺。
直覺和反思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呈現一種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互為成就的態勢。這種關系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廣義的反思平衡過程:反思平衡通過一個動態的、循環的過程來識別和定義諸般命題,并與現有理論進行比較,以發現潛在的不一致之處。隨后,通過反思與修正,調整理論或直覺以實現更高的一致性。
See Carl Knight, Reflective Equilibriu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ov.27, 2023), Edward N. Zalta amp; Uri Nodelman (eds.),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23/entries/reflective-equilibrium/(last visited Oct.16,2024).實驗方法提供了一種實證研究的框架,使法理學的理論能夠在實際情境中進行檢驗:量化方法能夠為反思平衡提供數據支持,使道德直覺的理論在具體數據面前得到檢驗;而質性分析則為反思平衡的過程提供深刻的背景,幫助理解人們在道德判斷中的復雜因素。反思平衡在這一過程中發揮整合作用,通過對直覺和理論的反思與調整,形成更具一致性和合理性的判斷,以驗證法理學中的諸般理論假設。
實驗是為了更為充分的反思。在社會環境不斷變遷、科學技術不斷革新的背景下,法理學需要對其基本理論進行檢驗,以發現并修正潛在的偏差和盲點。反思有助于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效互動。法律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其理論層面的構建,還依賴于實際應用中的反饋。通過對實踐經驗的反思,法理學者能夠識別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推動理論與實踐的融合。此外,反思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當今的法律問題往往涉及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多個學科,通過反思,法理學能夠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提升法律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豐富法理學的內涵和外延,使其研究成果更具多樣性和包容性。反思還有助于構建法理研究的共識與對話,包括但不限于社科法學家與法教義學家、法哲學家之間的對話,以及法理學家與部門法學家、法學家與其他學科專家乃至實踐領域的對話。通過“我看人看我”,借助社科法學的“他者視角”,各方才能夠在對話中達成更深層次的理解和包容。
參見雷磊:《法教義學在中國:歷程、疑問與反思》,載《法商研究》2024年第4期,第4-5頁。
反思與深化旨在更好地前行,雖然實驗法理學往往質疑理論背后某種基礎性判斷的普遍性,
但其批判性本質并非純粹解構,而是通過驗證與修正推動科學建構。
三、實驗法理學的可行性保障
為何在法理學研究中對廣泛的思維判斷進行實驗研究是可行的?更進一步,如果是可行的,那么這種實驗方法何以從現有理論和現實中汲取資源,使其更為充分高效地進行?認識論前提保證了思維判斷成為理性與經驗的通道,保證法理學問題可以被實驗研究。理論資源和現實工具的積淀和發展,確保理論成果能夠轉化為研究實踐,并展示了多學科交叉的潛力和新科技的助力。
(一)實驗法理學的認識論前提
實驗研究具有認識論前提。雖然自笛卡爾以來,理性被視為獲取知識和真理的核心手段,理性與經驗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領域,二者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系,甚至相互對立。
See Peter Markie amp; M. Folescu, Rationalism vs. Empiric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 2021), Edward N. Zalta amp; Uri Nodelman (ed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ationalism-empiricism/(last visited Oct.16,2024).但實際上,理性與經驗其實可以進行充分的溝通:理性和經驗分別源自思維與感知兩種認知過程,理性強調邏輯推理、抽象思考和概念構建的能力,而經驗則基于個體的感官體驗和具體觀察。理性幫助我們構建理論框架來解釋經驗現象,而經驗則為理性提供實際案例和數據支持,從而豐富和驗證理論,形成一個更全面的認識框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同樣表明,人類的思維過程并非單一依賴理性或經驗,而是在兩者之間靈活切換。
See Antoni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Quill, 1994, p. 253-267.在法律領域,這種結合就顯得更為明顯,因為法學不僅僅局限于理論推理,更直接與社會實踐息息相關。例如,在探討“懲罰”這一法律概念時,盡管理性分析可能得出理論上的結論,但道德運氣、情感、動機和社會背景等因素會顯著影響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因而法理學所凸顯的這種“實踐理性”,為理性與經驗的結合提供了基礎。
思維判斷作為一種理想通道,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理性世界與經驗世界之間的張力,并在多個層面上促進這兩個世界的關聯。首先,思維判斷可以被經驗塑造,因為思維判斷并非孤立存在,它受到個體生活經歷的深刻影響,人們的直覺和反思往往源于個人在生活中積累的經驗,這些經驗為我們的判斷提供了背景和框架。其次,思維判斷不僅是內在的認知過程,它還需要通過概念和語言表述出來。這種表達使得思維判斷可以在經驗世界中得到驗證與調查,這種語言和概念的轉換使得思維判斷不僅具有觀念上的抽象性,同時也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其表現和應用,因而我們至少可以對這種語言現象進行經驗調查。此外,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通過實驗研究追蹤思維判斷背后的生物學基礎。例如,神經科學的進步使得科學家能夠觀察思維活動時大腦中神經元的活動模式,甚至探討某些判斷是如何通過神經傳遞和化學物質的釋放來實現的。這種研究不僅能夠揭示理性思維和經驗之間的聯系,也能為理解復雜的認知過程提供生物學的依據,使思維判斷的研究走向一個更加多維和科學的層面。
See Oliver R. Goodenough amp; Micaela Tucker, Why Neuroscience Matters for Law, in A. D’Aloia amp; M. C. Errigo eds., Neuroscience and Law:Complicated Crossings and NewPerspectiv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p. 60-68.概言之,思維判斷不僅反映了個體的經歷和認知過程,也可以通過語言的表達和科學的方法,使得相對抽象的理性思維與具體的經驗現象被充分調查和研究。
通過實驗設計,研究者可以將經驗發現普遍化,將具體的經驗觀察轉化為更廣泛的理論框架。實驗方法的一個關鍵優勢在于能夠有效控制變量,這使得研究者能夠精確地隔離特定因素對思維判斷的影響,從而深入探討因果關系。通過精確控制實驗環境和條件,研究者能夠分析特定變量(如情境影響、信息完整性等)是如何調節個體的判斷與決策的。此外,實驗設計的多樣性也是其可行性的重要體現。研究者可以采用多種設計方法,如隨機對照試驗、雙盲實驗和交叉實驗,以增強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這些設計方法可以考慮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情境下的思維判斷,從而確保結果的廣泛適用性。實驗的靈活性使研究者能夠及時調整實驗策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研究需求,從而提高實驗的有效性和可重復性。
綜合認識論層面的支持,借助思維要素對理性和經驗的充分溝通,通過靈活且標準化的實驗設計,可以看到,法理學層面的實驗研究不僅是普遍的、可行的,也是同樣具備充分的理論和科學依據的。
(二)實驗法理學的理論資源
實驗法理學具備充分的理論資源。盡管實驗法理學被視為一門相對新穎的法理學研究領域,初看之下似乎缺乏傳統法理學的理論支撐,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實驗法理學的新穎性主要還是體現為傳統理論與現代實證方法的新結合,不是理論之新,而是進路、立場和方法之新。實驗法理學并不是要否定傳統理論資源的價值,而是試圖通過借鑒豐富的經驗性方法,在其基礎上進行反思、批判、創新和發展,以外在視角來豐富內在視角。與之對應,實驗法理學的理論資源也可以被分為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兩個方面。
內在視角的理論資源主要是傳統法理學發展中所深厚積淀的概念分析資源和規范分析資源,這些基礎理論源自法學經典文獻、學術探討和現代爭論。許多法律概念,例如,“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法律體系中,其內涵和外延不斷演變和完善,但這些概念追求一般化的目標始終保持不變。正是在經典法學理論的發展與爭論中,諸多概念才逐步得以明確和清晰,對概念的邏輯、語義、歷史及應用的考察也成為法理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第一,概念分析方法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基本思路與材料,并提出了可供質疑的理論對象。第二,思想實驗的設計也要求研究者具備較強的概念分析能力,越為精妙、形象的思想實驗越有助于研究者客觀、簡便、準確地獲取實驗數據。更重要的是,概念分析促進了實驗法理學者與傳統法理學家之間的實質性對話,使得實驗法理學在學術爭鳴中、在回應與批判中證立了自身正當性。
規范分析旨在深入探討法律規范的內在結構、邏輯和應用。該方法強調對法律文本、條款及其相互關系的細致分析,以揭示法律背后的意圖和適用條件及制度運行中的潛在問題和不足。
See Theresia Anita Christiani,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ir Usefulness and Relevance in the Study of Law as an Object, 219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 201-202 (2016).首先,規范分析具體體現在實效分析、法律論證和價值判斷三個方面,而現有法理學研究在這三個方面都積累了大量理論成果,有助于實驗法理學的研究者從實證、邏輯和倫理等多個方面深入探討法律規范的實際效果與合理性,這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增強了其研究成果的獨特性;其次,規范分析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探索法律規范在實際操作中的表現和效果,幫助理解法律的實施過程,評估法律的有效性與適應性,從而推動法律改革與發展;最后,更重要的是,規范分析提升了實驗法理學理論成果的融貫性,從實效分析到法律論證,再到價值判斷,規范分析的抽象層次逐漸加深,與概念分析相互銜接,證立了“法哲學具有法教義學上的適用功能”
雷磊:《“法哲學”講什么?— —馮·德爾·普佛爾滕〈法哲學導論〉導讀》,載《中國法律評論》2017年第3期,第176頁。。
外部視角下,實驗法理學大可廣泛借鑒眾多社會科學理論和實證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理論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對法律與社會行為之間復雜關系的深入理解:其中,社會學分析法律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探討法律如何影響社會規范和個體行為;心理學關注個體對法律的認知、態度與情感,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響道德判斷和決策過程;認知神經科學利用神經影像技術和行為實驗,揭示個體在面對法律時的心理過程與大腦機制,從而幫助理解法律決策中的認知與情感反應。實證研究采用定性與定量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對相關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涉及如何控制變量和隨機分配,如何收集個體對法律的態度、體驗和行為的數據,如何分析法律變量與其他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在此過程中,實證研究通過扎根理論、話語分析、民族志、現象學等方法,通過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使得直覺獲得深思的檢驗。
實驗法理學需要外部視角,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必須要進行外部視角的創造。即使某些創造經驗數據的人并不有意識地使其數據服務于實驗法理學的研究,但只要這些數據存在一種法理分析的潛力,只要實驗法理學者有意挖掘這些數據,并在考慮一般化的法理學命題時分析這些數據,即使該學者并未進行任何新的實驗,仍可以認為其做出了實驗法理學的重要貢獻。
See Kevin Tobia,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8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35, 778-782 (2022).例如,諾布和夏皮羅對于因果關系的分析就利用了大量現存的實驗數據,并未進行新的實驗研究,但這一研究無疑還是可以被歸為實驗法理學的典范。
See Joshua Knobe amp; Scott J. Shapiro, Proximate Cause Explained: An Essay in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8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65, 181-199 (2021).這既說明了實驗法理學理論資源的廣泛性,又說明了其在結合方式上的靈活性。
(三)實驗法理學的現實工具
1.從抽象到具體— —思想實驗的廣泛性
思想實驗作為實驗法理學的原初起點,從抽象到具體,表現為多種形式,具備廣泛性:哲學思想實驗是較為抽象的實驗形式,主要涉及對法律和倫理問題的深層思考。此類實驗通過設定假想情境來探討理論命題,幫助研究者分析抽象原則的合理性。例如,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的“電車難題”是一個經典的思想實驗,它探討了緊急情況下的道德決策問題。這種形式側重于觸發直覺反應,促使人們反思法律背后的根本理論和倫理框架。思想實驗同樣可以拓展到具體案件或法律問題之中,法學領域不乏這種實驗形式。例如,案例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具體的實驗形式,通過分析真實或假設的法律案件,研究者可以檢驗法律理論在實際情況中的適用性。
參見凌斌:《思想實驗及其法學啟迪》,載《法學》2008年第1期,第32頁。模擬法庭則是這種研究的一種形式,參與者通過扮演法官、律師和證人等角色,在設定的情境中進行辯論。這種方法不僅能讓參與者實踐法律程序,而且還能觀察和評估法律理論在實踐中的表現,從而推動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此外,思想實驗也可以
借助簡單的提問,對法律概念或原則進行直接質疑。這種方法通過開放性問題,引導參與者思考和討論特定問題背后的深層含義。從日常情景到課堂討論再到學術研究,實驗法理學能夠從抽象理論向具體實踐逐步深入,為法律的理解和應用提供豐富的視角。
2.從思維到語言— —數據收集的豐富性
思想實驗引發思維判斷,思維判斷源自思維,又輸出為語言,因而在數據收集上,實驗法理學存在較多可加以利用的方法:認知科學研究通過行為實驗與腦成像技術,一方面可以揭示法律決策的認知機制,使研究者能夠深入各類群體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動和情感反應,另一方面有助于識別出各類認知偏差,排除隱形、無關的變量的干擾,使其理論框架更具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問卷調查通過系統化的調查工具靈活收集公眾和專業人士對特定法律問題的看法,確保了數據的多樣性與代表性。此外,現代網絡問卷形式的發展為實驗法理學的跨文化及廣泛地區研究提供了更為便捷和低廉的資源,其允許研究者迅速部署調查并獲取反饋,因而解決了地理限制帶來的挑戰。通過互聯網,研究者可以輕松觸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者,從而增強樣本的多樣性和代表性;深度訪談、結構化訪談、焦點小組討論等質性研究方法,能夠深刻揭示法律概念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補充定量研究不能觸及的細節。
See James Andow, Qualitative Tools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29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128, 1130 (2016).最后,語料庫涉及對文本、語言的統計和分析,例如,利用大型法律文本和司法判決的語料庫,分析法律語言的使用習慣、關鍵詞和語言模式,可以揭示出法律語言和日常語言的演變與使用特點,使其與思維判斷的關系得以清晰呈現。
See Kevin Tobia, Testing Ordinary Meaning, 134 Harvard Law Review 726, 746-747 (2020).
3.新科技的介入— —數據分析的高效性
在數據分析階段,研究者當然可以借鑒統計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技術,例如,方差、均值、p值和t值的檢驗與考查。然而,在新科技時代,我們
更應關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實驗法理學的賦能。大數據技術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法律文本、案例、法律評論及公眾意見
See Christian Dpke, The Importance of Big Data for Jurisprudence and Legal Practice, in T. Hoeren amp; B. Kolany-Raiser eds., Big Data in Context:Leg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sight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 13-14.,擴展了實驗的領域,使研究者能夠深入挖掘法律現象背后的深層模式和趨勢。人工智能算法,特別是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有效處理和分析復雜的數據集。傳統的法律研究不再僅限于定性分析,通過統計學習、可視化技術、文本挖掘等方式,研究者可以采用量化方法評估法律效果、識別實驗之間的相似性,并提取關鍵特征。這些數據分析方法不僅加快了分析的速度與準確性,還使研究者能夠構建更為復雜的理論推理模型。此外,新技術的預測模型為實驗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通過分析大量歷史案例,實驗法理學能夠模擬不同因素對思維判斷的影響。這意味著實驗法理學的數據分析不僅限于對新創建實驗的分析,還可以針對歷史和現實中已發生的實驗進行評估。
四、實驗法理學的問題域及其限度
(一)實驗法理學的問題域
1.實驗法理學的總體議題
實驗法理學的總體議題主要關注其自身的范疇、證據和指向等方面,強調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對具體經驗數據的利用和分析較少涉及。實驗法理學的范疇可能涵蓋多個相互關聯的概念,例如,直覺與深思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如何相互促進。又如,如何界定專家,以及在法律領域中哪些群體可被稱為專家。
See Kevin Tobia, Legal Concepts and Legal Expertise, 203 Synthese 107, 112-113 (2024).其需要對不同的概念進行區分,探討哪些概念需要保持其通常含義,哪些概念確實具有技術性。
See Brian G. Slocum, Ordinary Meaning: A Theory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 11-14.更為宏觀的,實驗法理學考察經驗與理性之間的關系,探索為何法理學實驗是可行的。在指向上,具體議題的獲取及如何將概念分析的成果助力實驗設計,這些都是實驗法理學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內容。這一領域涉及諸多學科的參與,但其并不必然預設理論者跨學科能力的門檻,也即只要該理論者從其學科的角度對某一項議題作為貢獻,都可以助力實驗法理學的研究。
考慮到實驗法理學是一個相對新興的領域,其亟須通過闡明自身的總體議題來向學界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首先,學術界對新興學科的認可通常依賴于其理論的連貫性和實踐的有效性,通過開展系統的總論研究,實驗法理學能夠展示其獨特的學術貢獻,從而獲得廣泛的認可和接受,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從文獻上看,總體議題的探討就近乎占據了實驗法理學的半壁江山。總體議題的探討幫助研究者界定實驗法理學的核心概念、主要問題和研究方法,從而增強學科的內部一致性。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對于吸引更多研究者參與到這個領域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助于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
2.實驗法理學的具體問題
在總體議題的奠基之下,實驗法理學者投入到對于廣泛的法理學問題之中,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體現為更廣泛的法律和哲學意義上的一般法理學問題,另一方面體現為對于法律理論或實踐中的特定法律概念的具體研究。
在一般法領域,實驗法理學也可以分為兩個研究角度,第一個角度就是對于法律或規則概念的分析,實驗法理學考察了普通人是否共享某種關于法律本質的法理學直覺,特別是考察是否存在統一的大眾性的法律概念;第二個角度就是對于指稱理論與法律文本的解釋研究,例如,托比亞檢驗了而今對法律文本的通常含義的考察工具(詞典和語料庫)在多大程度上真實地映射了普通人使用語言的方式,并提出了這些工具的局限性。
See Kenneth Einar Himma, Replacement Natu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14 Jurisprudence 348, 370-373 (2023).
現今對于實驗法理學的更廣泛研究集中在特定的法律概念之上:有些概念與大眾判斷相一致,例如,立法者和法官在解釋刑法時經常以“普遍的正義感”為依據;在刑法和侵權法理論中,因果、懲罰、明知等概念往往占有重要地位;在合同法中,亦需要從一般人— —合同當事人的角度來判定如同意、所有、合理等概念。也有些概念可能與大眾判斷產生距離,例如,刑法中的故意、過失,立法意圖、融貫性等。在這類廣泛研究中,具體的法律概念的公共性、明確性、一致性等價值在專家判斷與大眾判斷更為一致時候會更好地實現,法律理論與法律實踐的鴻溝也能得到進一步填補。
而今,實驗法理學一方面明確了自身的界限,不減損其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吸納了更多的議題和方法,開始更具包容性。例如,對于法律文本中通常含義的調查,對于法律論證的客觀性調查等。與此同時,雖然調查大眾直覺已經成為實驗法理學領域中的主流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調查直覺是實驗法理學的唯一要義。實際上,當代實驗法理學逐步擴展了其議題范圍,如對法律的行為調查、價值判斷分析及跨文化研究。同時,還有部分研究與法經濟學研究、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等學科具有聯系,雖然對于這些研究是否可以整齊劃一地落入實驗法理學可能存在爭議,但至少也應承認其與實驗法理學議題的相關性。可以看到,對具體問題的探討更要求學者的跨學科知識和跨學科合作,這種探討
以大眾判斷為核心,并逐步在內容、對象和方法上革新和拓展。
(二)實驗法理學的必要限度
1.法理學實驗不能與科學實驗完全等同
法理學實驗與自然科學實驗存在顯著的差異。首先,法律現象的復雜性是一個關鍵因素。法律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規則體系,還深受文化、社會、歷史及政治等多元因素的影響。法律行為與實踐涉及個人、社會和權力結構的復雜互動,遠非簡單的因果關系所能解釋,對其實驗標準也很難做到嚴格遵循。其次,法律實驗往往關注的是人類行為,這些行為因多種心理、情境和情感因素的驅動而變得不可預測。這種不可預測性使得法律實驗的重復性面臨挑戰,參與者可能因監控或實驗情境而改變判斷。最后,實驗設計中涉及的倫理問題也是一大障礙。法律實驗可能需要對參與者施加某些條件或限制,涉及個人權利和隱私,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實驗的自由度。并且,實驗結果的普適性也是一大壁壘。法理學實驗的結果通常局限于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常常隨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有顯著不同,這進一步降低了實驗結果的通用性。由于以上多重局限,法理學實驗無法完全替代嚴謹、系統的科學實驗。然而,這一限度同樣呼吁了法理學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跨學科合作,通過多樣化的實驗設計,增強數據的代表性;通過持續的反思和調整,結合定量與定性研究,增強其可重復性。
2.實驗法理學不能替代傳統法理學進路
實驗法理學并沒有在空白的學術背景中生長,相反,它是在傳統法理學理論的積累與演變中逐步形成的。傳統法理學不僅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土壤,還對其研究進路、方法論和反思方向提供了借鑒,在這種情況下,實驗法理學的“神韻”與傳統法理學密不可分。實驗法理學解決的是傳統法理學中的一些經典議題,使得我們能夠從更為具體、廣泛的角度理解這些議題的深層次內涵。實驗法理學在其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如概念分析和規范分析,實際上都源于傳統法理學的理論成果。概念分析幫助研究者厘清法律中廣泛概念的具體含義,使其在法律實踐中更為明確,也有助于在實驗過程中獲得更為準確的結論。規范分析則為研究者提供了探尋法的效力基礎的方法,實驗法理學利用規范分析,溝通了法定的邏輯秩序與法律運行的實踐秩序,實現一種“應然”到“實然”的融貫過程。由此可見,實驗法理學的有效性和深度需要依賴傳統法理學的概念和規范體系。實驗法理學在探索和分析相關問題時,無意也無法替代傳統法理學的研究進路和研究成果,反而指向了對傳統法理學理論的延續與深化。
3.實驗法理學難以對命題達到完全確證
實驗法理學的批判性較強,但建構性往往不足,很難對命題達到完全確證。首先,法律現象的復雜性使得實驗法理學在實證研究中難以完全捕捉真正的法理學焦點,受訪者可能受到如社會、文化、經濟、語言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非常復雜,很難在思維層面完全排除影響。其次,實驗法理學的實證研究往往受到樣本選擇和研究設計的限制。例如,特定的案例或數據集可能無法代表所有理論情景,導致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受到質疑。最后,法律環境和社會觀念是不斷演變的,前期得出的結論可能在未來被新的證據或變化所推翻。因此,實驗法理學的結論可能也是有時效性的,面臨著被更新的實證研究所挑戰的風險。但這一限度并非否定了實驗法理學本身的理論意義,因為實驗法理學本身就是以批判、反思為本質的,是為了豐富法理學討論的。
See Raff Donelson, Experimental Legal Philosophy: General Jurisprudence, in A. M. Bauer amp; S. Kornmesser eds., The Compact Compendium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De Gruyter, 2023, p. 324.實驗法理學真正注重的是反思平衡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可能在理論確證上有一定的開放性,但通過質性研究與量化方法的結合,通過多學科的廣泛合作,已經朝著更加正確、更加科學、更加普遍的方向前行良久,這一過程本身就是充滿意義的,這種持續探索的精神,才是法理學研究的應然品性。
五、結語
“貼近實在法、貼近法律實踐問題,就是貼近人類生活本身。”
舒國瀅:《在歷史叢林里穿行的中國法理學》,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1期,第34頁。法理學研究始終包含著一個以專家和大眾、理性和經驗、語言和概念為中心的實證工作,也正是在此前提下,實驗法理學才具備廣闊的前景和廣泛的研究內容,也理應受到法理學界的關注。實驗法理學改變了傳統理論家坐而論道的方式,溝通了理性世界與經驗世界,聚焦、區分不同的語言實踐,可以說是一種向著法理學之本性的回歸。正所謂舊問題、新進路,實驗法理學無意替代也不能替代經驗調查、概念分析、規范分析等法理學研究進路,而是在尊重和承認這些傳統的基礎上,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用實驗的精準性為社科知識與法理學的合作提供一條新路徑。
不可否認的是,從誕生之日起,實驗法理學就一直飽受爭議,對其獨立性、可靠性、可行性的質疑從未停止,但應對并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就是實驗法理學逐步走向成熟、走向完善的過程。對待實驗法理學,更理想的是一種“謹慎而包容”的支持態度:一方面,需要積極接受實驗方法,并將其融入法理學研究中;另一方面,也要正視實驗法理學所存在的問題與缺陷,期待或推進其解決。而今,新科技的發展為實驗法理學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和豐富的研究可能,為法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可以肯定地說,實驗法理學的未來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頗具挑戰的。JS
Basic Theory of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YU Mengh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p;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is an emerging approach to jurisprudential studies based on thought experiments. It expounds and delves into jurisprudential proposition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a wide range of cognitive judgments. Rooted in the rich heritage of jurisprudence,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is highly valuable in that it explores the folklity, scientificity, and reflectiveness of jurispru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objects, methods and orientation of experiment.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bridges the rational world and the empirical world, and is feasible as it is endowed with ampl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highly-effective practical tools. Contemporary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overarching themes, specific issues, and local context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hile remaining within necessary limits dictated by its na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On one hand,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cannot replace traditional conceptual and normative analyses, as what it is purported to address remains classical jurisprudential ques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tegration of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allowing for mutual connection and enrichment between the two. Overall,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is faced with both challenges and promising prospect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 intuition; thought experiment; scientificity
本文責任編輯:董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