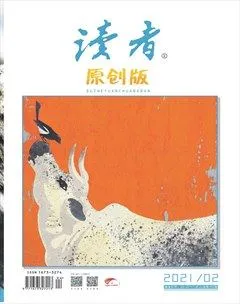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1803
謝鶴醒
一
起初,我想要搬出來住,是因為難以忍受父母的嘮叨。從我畢業那天起,家里的氣氛就像籠罩著一層陰云,時不時會因為我的工作或婚戀問題澆下傾盆大雨。終于,我得到一個改變現狀的機會:跳槽到離家很遠的郊區去工作。
新工作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教師編制考試得到的。熬了四年,終于擺脫了父母口中“臨時工”的身份。我沉浸在“終于有理由搬出來”的喜悅中,無暇他顧。
入職前,在爸媽擔憂、無奈的眼神下,我歡天喜地地找了好幾天房子。最后被中介小楊哥的營銷能力打動—一室大開間,從陽臺望下去就是地鐵口和商業綜合體,上班單程步行只需20分鐘……非常符合我“離單位近但是又不想住在單位旁邊”的矯情需求。
“喏,你的1803。”簽好合同,小楊哥把鑰匙交給我—我終于有了自己的獨立空間。
二
不是沒有擁有過夢想中的“自由”。

畢業前,我曾在重慶短居。離開擁擠的宿舍,一個人在觀音橋步行街附近的酒店開了房間。那間房的書桌旁有一扇正對著嘉陵江的窗。那年春天的重慶鮮有晴天,我總在埋頭寫論文的間隙,一邊活動著僵硬的肩頸,一邊看細雨綿綿。
在重慶短居的一個月,我通常在寫完一個章節后出去找飯吃,然后走到江邊,從正午坐到黃昏,也從暮春坐到初夏。那時,總在想遙不可及卻又近在咫尺的未來,覺得一切迷茫卻又充滿期待……
然而,畢業后的日子幾乎是失控的。兜兜轉轉,我在30歲這年才考取了父母眼中“穩定”的工作,才有底氣搬出家,尋求獨立。
30歲未婚,即便是在這座所謂的新一線城市,怎么看也還是像個笑話。
更可笑的是,我高估了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
搬進1803室的第一晚,我就因為不會使用熱水器,先是百度查詢,然后通過電話、微信問了一圈人。遠在濟南的橙子遠程協助我解決了這個問題,隔著手機,我都能感受到他欲言又止的憂慮:“你這回是徹底搬出家了?”
“當然!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嗎?”我故作瀟灑地調侃道。
“那倒沒有……挺為你高興的,總算邁出這一步了,不過肯定什么事都得自己操心了。”
沒錯,我很快便切實體會了橙子的擔心。更措手不及的是,新工作的忙碌程度超乎我的想象。以至于一個人住了快兩個月,原先幻想過無數次的獨居的美好場面—清晨煎蛋,夜晚喝酒,站在18樓的陽臺傷春悲秋,再回到桌前靈感爆棚地搞創作……實際上都因為疲憊和懶惰而簡化成了“住旅館”—不做飯、不種花、不養寵物,每天匆匆忙忙地早出晚歸,幾乎每個周末都要加班……
而我頭一次感受到滿滿的“生活氣息”,是因為衛生間的地漏堵了。
我的第一反應是給我媽打電話。
我媽回:“你去樓下小賣鋪買個皮搋子。”
“皮搋子是啥?我會用嗎?”聽完我媽簡潔的回復,我略有些擔心。
“你去買了就知道了,自己摸索!”電話毫不留情地掛斷—她仍對我執意搬出家門之事“耿耿于懷”。
我硬著頭皮去了小賣鋪,老板得知我的下水道堵了,熱情地教我正確使用皮搋子的方法。我似懂非懂地接過皮搋子,道謝后幾乎是逃出了小賣鋪—我長得那么像不會通下水道的樣子嗎?
但當我憑借一己之力疏通地漏后,內心深處是從未有過的平靜,好像獨居了兩個月后,在這一刻,才是真正過日子。
等等,洗臉池下面是什么?我頭一次蹲下身子,探索衛生間的邊邊角角—是前任租客留下的一把九成新的皮搋子。
三
類似的烏龍事件發生了不止一次。通常是在我購置了物品后,才發現房間里明明就藏著同款。有一次,我媽帶齊了工具來幫忙貼墻紙,我才知道,我的床頭柜抽屜里有膠帶和剪刀。
“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我媽狠狠瞪了我一眼。
不是沒有后悔過這個匆忙的決定。
因為如果沒有搬出家門,我可能不會發現自己不懂的事兒有這么多。我的烹飪水平停留在煮方便面的階段;我總是記不住去物業充電卡的步驟,每次都要拖著小楊哥幫我操作;陽臺的紗窗破了,衛生間的浴霸壞了,水龍頭一直滴水我卻束手無策……所有的小問題,被我用一句“湊合著吧”暫時掩蓋。工作后的人生太累了,當年在重慶愜意寫論文的日子不會再來,現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能自己承擔。
然而,現實總是適時地“教訓”我的懈怠—永遠忘不了那個尋常的傍晚,當我下班回到1803,看到整個廚房變成“水簾洞”的震撼。傻眼了的我站在水中央,我該跟誰商量?找鄰居索賠需要吵架嗎?
不如先給小楊哥打個電話吧。
小楊哥讓我去找物業公司,先查明原因:“你別害怕,漏水用臉盆先接上,拍視頻留好證據,方便的話在物業公司留把鑰匙,明天我來看看。如果房子壞了,我會去找鄰居索賠的。”
感謝靠譜的小楊哥,我終于冷靜下來,趕緊穿上外套,拿好手機、鑰匙去找物業了。
情況比我預想的要好些,21層水管爆裂,已經搶修完畢;但積水太多,導致20層和19層被淹,到我這里已經算是尾聲了。物業大爺安慰我:“明天應該就好了。”
明天,真的會好嗎?我默默收拾著被水和陳年油污浸泡的地面,心疼自己嶄新的鍋具和餐具此時已經一片狼藉……窗外是“應時應景”的毛毛細雨。我望著仍在滴水的天花板,發了一條“朋友圈”:“此刻,我非常想和月亮干一杯……”
某“損友”在下面評論:“此刻,你需要一個男人。”
忍了又忍的委屈感遮天蔽日。臨睡前給媽媽打電話訴說了悲慘境遇,她一改往日的嚴苛,居然輕聲安慰道:“今晚放心睡覺吧,水不會滴到床上的。”
“我就是很郁悶,為啥漏水偏偏讓我碰到!”我撒嬌地抱怨了一句,而我沒敢說的是:除此之外,我今天工作繁忙、學生搗蛋、獎金沒發、感興趣的“相親男”突然不理我了……
怎么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對?!
“很正常啊。遇到困難解決困難。天花板臟了沒關系,下次我拿點兒漆去給你補一補就行了。”
從我媽一反常態的灑脫態度中,我似乎讀出她對我已放手的信號,一時間百感交集。
第二天到了單位,平時總愛開玩笑的體育老師很認真地問我:“看你‘朋友圈,發生什么事了嗎?”
我沒好氣地說:“樓上水管爆裂,給我漏了一屋子水。”
“你咋不叫我幫忙呢?現在解決了嗎?如果需要,我很方便。”
我笑著捶了他一拳。手機亮起,是小楊哥發來的消息:“水已經不滴了,順便幫你修好了衛生間的燈。鑰匙我放回物業公司了啊。”
我想起許多個失眠的黑夜,我站在陽臺上,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循環變換,晚風拂面,我若有所失—自由的代價當然少不了孤獨無助,但好在不是一個人的寂寞與煎熬,社會的生機就能將我療愈。
四
我終于意識到,青春時代所理解的“自由”,全跟吃喝玩樂有關,是灑脫放松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但那不是生活本來的面目。
也是在搬出家這一年,我深深感受到我和父母之間的聯結感陡然下降。這些年,我無數次埋怨他們對我人生的干涉、左右、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在謀劃著出逃,但我一直都明白,無論走到哪里,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離開過他們。
一年的時間轉瞬即逝,我去找小楊哥續租。爸爸得知后,頭一次松口建議我該考慮買房了,要知道,他這個老古板,從前一直堅持“女孩的首要任務是嫁人,買房是男孩的事”。
“如果有喜歡的樓盤不要猶豫,首付我們支援你。”
我終于等到了家人的理解和尊重,三十而已,只要我愿意,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我的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