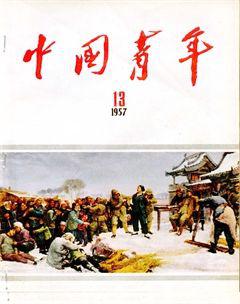不能沒有靈魂
王牧
前不久,在知識青年主要是大學生中間,刮起了一陣子小臺風。蒼松翠柏,屹立而不為所動,有些脆弱的柔枝嫩葉,一時隨風搖擺了。疾風知勁草,原來腳跟站得不大穩(wěn)當的,不免被吹得跟蹌了幾步。
在風浪中,特別是青年,一時的搖擺并不足怪,但要在風浪中得到鍛煉、提高、茁壯地成長起來,第一步是貴在有自知之明。對于右派的言論,也許你沒有公然的喝采、鼓掌、隨聲附和,但在二三知己的交談中,在自己思想感情的深處,是否有所同情和共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嚴格地檢視自己,理一理思想脈絡,找一找不對頭的地方,這就會使我們在今后的斗爭中獲得較多的免疫力。
可以回想一下,對于儲安平那段謬論,有些人覺得雖然“稍有偏激”或“用詞不當”,但也不無中肯的意見。其實,怎么能設想這種資產階級右派政客的重要發(fā)言會像我們在小組會上那樣無拘無束呢?儲安平的發(fā)言曾由羅隆基審查過,便是一個明證。不難明白,他們在遣詞用字引用例證的時候,都是經過反復推敲精心設計的,其目的也不是希望黨吸取什么有益的意見,而是要“打中要害”。對于章伯鈞的發(fā)言,經過揭發(fā),大家是清楚了:原來那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其實,章伯鈞的發(fā)言也并不怎么難懂,他說:“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共產黨是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正是章伯鈞最痛心疾首的地方,因而不遺余力地攻擊。話是說得夠明白了,但是我們許多人卻嗅不出,中了毒氣還不自覺,十月革命以后的第八年,蘇聯共產黨“關于青年團工作”的決議中就說:“新的青年階層中間令人可怕的政治上的無知……乃是極其嚴重的現象。”政治上無知,就可能被資產階級右派牽著鼻子走,離開黨和社會主義。
無知不是罪過,從無知到知本來需要一個過程。但政治上的無知往往不是什么知識問題,我們的新社會比舊社會好,社會主義制度比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無比地優(yōu)越,黨的領導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等等,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論,而是生活本身所證明了的真理。但是,“除了公有制之外,一切都可以否定”,“‘三害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共產黨不超過人口百分之二,極少數人決定一切問題是危險的”之類的反動言論,其荒謬本來比公然要共產黨“下轎”“下臺”的叫囂并不更精致些,工人農民憑著直覺就認出這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我們一些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卻糊涂起來,甚至欣賞這些論調是“大膽”、“勇敢”、“見解新鮮”、“善于獨立思考”。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這樣的知識青年,也學過馬克思主義,也許考試成績還是五分,但是他們在學習的時候,并沒有認真地讓馬克思主義和潛存在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交鋒,把資產階級思想打垮,為自己取得鞏固的無產階級立場。在自己的思想中原就是香花與毒草并存,而香花又沒有全部戰(zhàn)勝毒草,這樣,怎么能清楚地分辨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
整風聲中,我們反對“三大主義”,右派也反對“三大主義”,但目的卻不同。我們提意見本心是為了黨好,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更快地前進,右派則是要反掉黨的領導,反掉社會主義,用資產階級思想“整”掉無產階級思想。如果我們頭腦中資產階級思想不少,在右派的沖擊下,剛學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會忘記,立場就會動搖,根本的是非——是否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也就劃不清界限,對右派,就只能欣賞他們的“勇敢”了。
自覺地走回頭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知識青年中間是極其個別的,較多的是聽見民主、自由就興奮,聽見集中、紀律就有些頭痛,反教條主義時是勇士,反修正主義時就成了書生,對人性論極力強調,對階級性則覺得多少是個壓力。自然,民主、自由都是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但不要集中的民主,不要紀律的自由,只能是無政府主義;教條主義是應該反的,但反對教條主義的有各種各樣的人,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意在反掉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至于人性,在階級社會中總是有著階級烙印的。在政治思想問題方面,對某一系列的東西歡迎,對另一系列的東西厭惡,這種傾向性不能不說是階級立場使然。
右派分子對于階級斗爭、階級立場是很反感的,他們對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一直是深惡痛絕,認為是把他們的“靈魂”給整掉了,雖然那時只不過是要求在思想上劃清敵我界限,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只不過部分地受到批判。今年春天,他們雖還覺得“乍寒乍暖”,但朦朧地以為可以卷土重來了,他們的“靈魂”是資本主義的,因而要“招魂,實際上就是在整風中,把被壓抑的資產階級思想,揭開蓋子,“大鳴大放”出來,向我們進行階級斗爭。他們否認階級斗爭,不談階級立場,其目的則是把一些不懂階級斗爭,階級立場不穩(wěn)的人拉過去,給他們當俘虜。這一場激烈、尖銳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使我們增長很多見識,也得到不少教訓。重要教訓之一就是:社會上還有階級斗爭,我們的頭腦中也在進行階級斗爭;思想意識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上還需要相當是的時間才能決定勝負,我們知識青年則應當充分自覺地使無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頭腦中盡快地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要做一個社會主義建設者,就不能沒有社會主義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