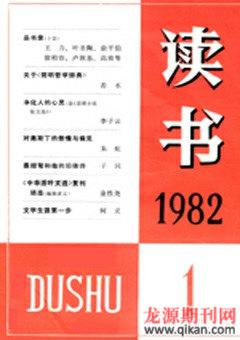讀《關于王國維的功過》
甘 孺 張樹泉
這篇文章(載《讀書》一九八一年第八期),我讀后,感到作者對王國維一生功過做了分析,認為研究王國維的功與過,要從他的著作和著作外去多方發掘,說明作者在處理問題上是按著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從事物的內部去找根本原因的。作者又把晚清許多同時代人的旨趣與成就相對比,他說,比來比去就能發現他們每個人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決定著他們的行動。作者這樣做法,就比前人把王國維和魯迅單純對比進步一些。作者歷舉王國維之死的四種流傳說法,其中第三種以郭老《歷史人物》為代表,第四種說法以溥儀《我的前半生》為代表。作者對這兩種說法所作的駁難,基本上是對的,是合情合理的。誠如作者自己說:“我們評論王國維,首先要以唯物主義作指導,清除寧左毋右的壞學風在頭腦中的殘余,同時還要不為權威人士成說所囿。”時至今日,不是還有人作文章說王國維不是殉清而死,但他所提出的有力證據,仍不外掇拾郭老和博儀的舊說法,這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我作為王國維的姻家晚輩,出生晚,知識水平低,但對于王國維,自信要比有些人了解得多而且真實。我五六歲就見過他,一九二三年,他應博儀之召從上海來北京,到一九二六年這幾年間,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時已經十二三歲,至今對他的聲音笑貌還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
他的書札,我家積存很多。因為轉換幾個人手,難免有散失,等挨到我手里,止剩百六十余通。一九六二年,我才把它全部輯錄為《觀堂書札》。交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中華不同意出版而要留作資料,我又從中華取回。經過“文化大革命”,幸輯錄本未遭劫(原跡已損失大半)。去年湖北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編印《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摘錄其中有關論學的部分一一八通。《書札》內容豐富,論學、論政、論時事、論人,以及家常瑣屑,無所不有。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吳澤教授正在編輯《王國維書信集》,將我的《觀堂書札》全部采錄,惟尚未出版。
最后要向作者商榷的,就是作者文末下的結論。說王國維之死是由于從小多病,中年又患腳氣病,晚年還沒有好,兼患肺結核和咳血,本來就厭世,加上病魔折磨,所以不得不死。這個結論,不能令人同意。王國維從表面看,體質不算健康,但平日并不多病,在日本患過腳氣,是一種地方風土病,后來雖曾舉發,未成大患。《觀堂書札》里提到足疾的有兩處,文如下:“維足疾雖不進亦不見退,服藥四五日,尚未見效,尚擬覓他醫,決定何病,如系腳氣,或須作津沽一行,藉圖良晤。”“維之足疾,甚與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蓋是一種地方病,豈已二十余年乃重發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須俟醫生診斷決之”(一九一八年居上海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王國維終年病纏在身,如何能在學問上做出驚人的成績呢?
至于王國維和我家的關系,我在《永豐鄉人行年錄》(一九八○年十月江蘇內部印行)一書里已敘述詳盡,這里不再多贅。另外我還寫了《王國維政治思想》一文,主要取材于《觀堂書札》中的自白和他的一篇未正式發表的《政論奏稿》,應該說這才是研究王國維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已寄交華東師大,收入他們編輯的《王國維學術論文集》里。至于王國維之死,作者在本文不是也舉例說,他為什么說《頤和園詞》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是平生最滿意之作呢?又為什么北京大學聘他為文科教授,他堅決不干,接到宣統的詔書后,很快就離滬北上呢?這不已接觸到問題的關鍵了嗎?
長春甘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關于王國維的功過》一文中說:“過去從來沒有人把他(指王國維——引者注)的健康狀況和死因聯系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不應當有的疏忽。”這說法不確。不是“從來沒有”,而是“確曾有過”。誰?就是郭老。《屈原研究》一文中,郭老在談到屈原自殺的原因時曾說:“更何況他(指屈原——引者注)的死,就和王國維是因為肺病和經濟逼迫一樣,也還可以有別的生理上的原因。”在這句話里,郭老不是很明白地把“王國維的健康狀況”與他自殺的原因“聯系起來”了嗎?
狗尾續貂,不一定正確,權作肖艾同志文章的一點補正。
讀者·作者·編者
甘孺/張樹泉 這篇文章(載《讀書》一九八一年第八期),我讀后,感到作者對王國維一生功過做了分析,認為研究王國維的功與過,要從他的著作和著作外去多方發掘,說明作者在處理問題上是按著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從事物的內部去找根本原因的。作者又把晚清許多同時代人的旨趣與成就相對比,他說,比來比去就能發現他們每個人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決定著他們的行動。作者這樣做法,就比前人把王國維和魯迅單純對比進步一些。作者歷舉王國維之死的四種流傳說法,其中第三種以郭老《歷史人物》為代表,第四種說法以溥儀《我的前半生》為代表。作者對這兩種說法所作的駁難,基本上是對的,是合情合理的。誠如作者自己說:“我們評論王國維,首先要以唯物主義作指導,清除寧左毋右的壞學風在頭腦中的殘余,同時還要不為權威人士成說所囿。”時至今日,不是還有人作文章說王國維不是殉清而死,但他所提出的有力證據,仍不外掇拾郭老和博儀的舊說法,這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我作為王國維的姻家晚輩,出生晚,知識水平低,但對于王國維,自信要比有些人了解得多而且真實。我五六歲就見過他,一九二三年,他應博儀之召從上海來北京,到一九二六年這幾年間,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時已經十二三歲,至今對他的聲音笑貌還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
他的書札,我家積存很多。因為轉換幾個人手,難免有散失,等挨到我手里,止剩百六十余通。一九六二年,我才把它全部輯錄為《觀堂書札》。交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中華不同意出版而要留作資料,我又從中華取回。經過“文化大革命”,幸輯錄本未遭劫(原跡已損失大半)。去年湖北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編印《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摘錄其中有關論學的部分一一八通。《書札》內容豐富,論學、論政、論時事、論人,以及家常瑣屑,無所不有。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吳澤教授正在編輯《王國維書信集》,將我的《觀堂書札》全部采錄,惟尚未出版。
最后要向作者商榷的,就是作者文末下的結論。說王國維之死是由于從小多病,中年又患腳氣病,晚年還沒有好,兼患肺結核和咳血,本來就厭世,加上病魔折磨,所以不得不死。這個結論,不能令人同意。王國維從表面看,體質不算健康,但平日并不多病,在日本患過腳氣,是一種地方風土病,后來雖曾舉發,未成大患。《觀堂書札》里提到足疾的有兩處,文如下:“維足疾雖不進亦不見退,服藥四五日,尚未見效,尚擬覓他醫,決定何病,如系腳氣,或須作津沽一行,藉圖良晤。”“維之足疾,甚與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蓋是一種地方病,豈已二十余年乃重發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須俟醫生診斷決之”(一九一八年居上海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王國維終年病纏在身,如何能在學問上做出驚人的成績呢?
至于王國維和我家的關系,我在《永豐鄉人行年錄》(一九八○年十月江蘇內部印行)一書里已敘述詳盡,這里不再多贅。另外我還寫了《王國維政治思想》一文,主要取材于《觀堂書札》中的自白和他的一篇未正式發表的《政論奏稿》,應該說這才是研究王國維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已寄交華東師大,收入他們編輯的《王國維學術論文集》里。至于王國維之死,作者在本文不是也舉例說,他為什么說《頤和園詞》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是平生最滿意之作呢?又為什么北京大學聘他為文科教授,他堅決不干,接到宣統的詔書后,很快就離滬北上呢?這不已接觸到問題的關鍵了嗎?
長春甘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關于王國維的功過》一文中說:“過去從來沒有人把他(指王國維——引者注)的健康狀況和死因聯系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不應當有的疏忽。”這說法不確。不是“從來沒有”,而是“確曾有過”。誰?就是郭老。《屈原研究》一文中,郭老在談到屈原自殺的原因時曾說:“更何況他(指屈原——引者注)的死,就和王國維是因為肺病和經濟逼迫一樣,也還可以有別的生理上的原因。”在這句話里,郭老不是很明白地把“王國維的健康狀況”與他自殺的原因“聯系起來”了嗎?
狗尾續貂,不一定正確,權作肖艾同志文章的一點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