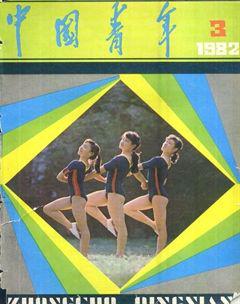《鄰居》
馬林
1973年,我終于離開了“學制”極長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事出偶然地來到了清華大學,整整生活、工作了4個年頭。于是,便有幸結識了許多從事自然科學工作的新老知識分子、校辦工廠工人,剛剛恢復工作的領導干部。在他們身上,留著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打下的深淺、色彩各不相同的印跡。但是他們那種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忘我勞動、獻身科學的精神,卻使我深為感動。我的這些同事和鄰居,就漸漸在我的腦海中活動起來。我開始產生了表現他們的愿望。
但是,選擇影片《鄰居》中表現生活的特定角度,醞釀的時間卻要長遠得多。我國歷來有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四人幫”肆虐時期,我對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當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好心的鄰居送來一碗面條,或者讓孩子遠遠地喊你一聲“叔叔”,都會使你感到莫大的溫暖。我覺得,鄰里之間,猶如嚴冬的人們互相用體溫取暖一樣,彼此關懷和幫襯,成為你堅強地生活下去的一種鼓舞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幾十年來的各種原因,目前我國城市住房問題相當尖銳。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家人擠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五六家人共用一間廚房,或者索性擠在樓道里做飯的情景。他們有煩惱,也有歡樂,有牢騷,更滿懷希望。我們的合作者達江復同志當時就住在《鄰居》中那種筒子樓里。這簡陋、狹窄的筒子樓,簡直象是一面鏡子,不僅從一個角度映照出現實生活的大千世界,也集中反映著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高爾基說過:文學是人學。文藝的重要功能,在于表現人和人的精神,發掘和謳歌生活中的美。它當然不能解決住房一類的實際問題。物質的問題歸根結蒂只能靠物質手段去解決。但是文藝可以而且應該幫助人們正確認識和對待種種實際問題。從我國的生活實際看,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對于各種困難并不是不能諒解的,只要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共度時艱,困難也就能很快地克服。但是黨內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卻時時象噪音一樣破壞著生活的和諧,有時造成并激化著種種矛盾和沖突。基于對生活的這種認識,我們在創作劇本時,便把筆觸主要用來描繪劉力行和他的鄰居們的崇高的精神美,同時也對不正之風作了應有的揭露和針砭,從而為《鄰居》定下了現實主義的、質樸的、尖銳潑辣的、光明向上的基調。
影片攝制完成后,我多次直接間接地聽到一些青年朋友的疑問。他們問:在現實生活里,有劉力行這樣的好干部嗎?我不了解這些青年朋友的經歷和處境。面對這個問題,我總感到一言難盡。我投入革命隊伍時不滿18歲,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我感到,正是我周圍到處可見的老劉那樣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好干部,使我們黨贏得了人民,取得了勝利,也使我認識什么是共產黨以及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進城以后,物質條件優裕了,但保持著戰爭年代優良傳統的好干部,仍然不乏其人。譬如,已故的北京電影劇團團長田方同志(曾在影片《英雄兒女》中飾演軍政治部主任、王芳的生父王東),早在30年代,他就是電影明星,以與金焰、王人美合拍的《大陸》等影片而蜚聲一時。抗戰爆發后,他離開上海奔赴延安。解放后,曾擔任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的職務。舉一件小事來說明他的品質:三年困難時期,他離開電影局回到北影廠。電影局的工作人員在清理他的抽屜時,發現當時發給領導干部的每月幾斤肉蛋供應卡片,仍是一片空白,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的小事,在他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不勝枚舉的,因此,他始終得到了大家的愛戴和懷念。再譬如大家熟知的電影界老前輩夏衍同志,他現在已退到二線做顧問了。“十年動亂”中,他的腿殘廢了,但他不顧傷殘,也不顧80多歲高齡,兢兢業業地為黨的文藝事業工作著。為了扶植新人新作,他閱讀了大量劇本。后來眼睛壞了,又改為聽讀劇本。他曾說,我愿意象過去坐在馬路邊的“縫窮婆”那樣,用自己包袱里的各色零碎布頭,為別人認認真真地打補釘。再拿房子問題來說吧,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匡亞明同志,上任后幾次把分給他的套間讓給居住困難的群眾,自己卻長時間地擠住在學生宿舍樓里。真的,每當我為黨內某些不良現象而痛心疾首,甚至感到些許失望時,我總是會不期而然地想到田方、夏衍、匡亞明那樣的老前輩、好同志。我確信,我們黨集結了一大批為國為民、有膽有識、立志改革的有志之士,他們不謀私利,埋頭苦干,從不炫耀自己,因此也很少為人們所知道。他們是社會的脊梁,國家的中堅。我們沒有理由失望、失去信心。我們集中力量塑造劉力行的形象,正是希望把這種感受傳達給觀眾。只有美的心靈和眼睛,才能真正發掘美的事物、美的生活,而這一點,恰是面對嚴峻現實時最不可缺少的。
《鄰居》攝制組有的同志曾開玩笑地說:“想不到我們青年廠卻拍了一部老頭電影。”由于主題和題材的限制,我們未能把較多的篇幅用于表現青年人,但是,其中也出現了劉小京、明玉朗、馮衛東這些形象。這些表現,對于生機勃發的現實生活中的青年一代,是太薄弱了,我們深感歉然。而且表現得是否準確真切,還有待于廣大青年朋友的評價和鑒定。作為五十年代北影廠第一任團委書記,我希望在今后能夠更多更好地反映我們大有希望的一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