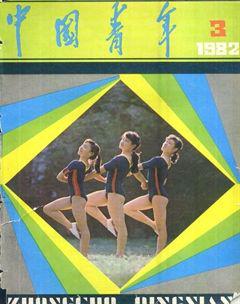卡列寧的靈魂和安娜的悲劇
小弟:
你好!來信已經收到。你們對正在播映的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展開了爭論,這是很自然的。一部世界名著及其人物形象所蘊含的思想意義,一般都比較復雜,而人們在欣賞時,又總是帶著各自的生活感受,并受著認識和欣賞水平等的限制,有不同的看法是不足為怪的。
《安娜·卡列尼娜》創作于19世紀70年代。當時,俄國正經歷著一個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到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急劇變革的時代。這使世界觀本來就充滿矛盾的列夫·托爾斯泰,在思想和創作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創作這部作品歷時5年(1873—1877),一再改變構思,把原先“帶有‘私生活性質”的故事,改為藝術地表現當時俄國動蕩復雜的社會生活,提出并努力探索經濟、政治、家庭、道德……等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在托爾斯泰的三大名著中,《安娜·卡列尼娜》是唯一以主人公的名字作為書名的,這不僅表明托爾斯泰對安娜命運的社會意義的重視和強調,也使我們看到這部作品在他從《戰爭與和平》通向《復活》的轉折性作用,這就是從貴族和地主的立場轉向俄國人民。正因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一出現,就截然有別于當時充斥俄國文壇的那些家庭—教誨意義的小說,得到了廣泛的注意和好評。俄國著名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當即撰文,認為在這部作品中,“所有我們俄國現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了”。德國著名作家、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托馬斯·曼贊揚它是“全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社會小說”。英國廣播公司制作的電視連續劇,其基本情節是忠實于原著的,但對原著主要精神的表現,卻不夠突出鮮明,幾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分寸,也有不夠準確之處。因此,全面準確地評價這幅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社會生活的畫卷,就應該立足于閱讀和研究原著,了解當時俄國的社會歷史狀況,這就不是一封短信所能企及的。
但是,對你提到的一個問題,我愿意談點看法。你說,有的同學比較同情卡列寧,認為他是無辜的受害者,安娜應對家庭生活的破裂負全部責任。怎樣認識卡列寧其人以及他和安娜的關系?回答這個問題,盡管不能代替全面去理解作品的主旨(作品中還有一條描寫列文和吉提的關系的重要線索),但確實是通往作品主旨的一條重要渠道。弄不清卡列寧的面目,就不可能正確評價安娜,也就很難理解作品所具有的偉大的社會意義。
那么,卡列寧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有趣的是,他的名字也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他。這是托爾斯泰從希臘詞匯“KAPEHOM”音譯過來的,意思是頭腦。卡列寧具有一個精密計算自己功名前程的“頭腦”,是一個從頭到腳自命不凡而又冥頑不靈的沙俄官僚的化身。大學一畢業,他就馬上“完全沉迷于功名野心”,他使自己的全部心力、意念和愿望都服務于官場衙門,成天“沉湎于與生活相敵對的事務之中”。電視連續劇通過卡列寧多次到部里開會而和安娜分別、很少和家人在一起吃飯等來著意刻劃這一點。安娜這樣一針見血地指出:“功名心,成功的欲望—這就是他靈魂中所有的唯一的東西”。卡列寧的這種靈魂,使得他完全離開了人類的正常情感,同時,也成為他在處理家庭生活時的唯一尺度。
對卡列寧來說,家庭生活—妻子和孩子,只是一種“責任”和“義務”的關系,而理解他們,愛他們,他不僅從未想到過,而且反而認為是“有害的、危險的”。他和安娜的相識乃至結合,本來就不是愛情的產物。那時,他在外省擔任省長。安娜的姑媽、這個省有名的貴族小姐把他和安娜撮合在一起,使他面臨著難堪的選擇:不是提出求婚就是離開這個城市。他不愿意為了這而犧牲前程,就向安娜提出求婚。面對這樁由姑媽“一手操縱”的婚姻,面對這個比她大20歲,無論志向、性格還是興趣都毫不相同的官僚,安娜不是沒有猶豫過。但她聽從了這樣的勸告:“忍耐—就能相愛”,便應允了。等到安娜意識到她犯下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時,已經太晚了,他們同床異夢,毫無感情地度過了8年的夫妻生活。安娜曾這樣憤怒地回擊那些為卡列寧辯護的人:“他們說他富有宗教心,道德高尚,正直,聰明;但是他們沒有看見我所看到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八年來他是怎樣摧殘了我的生命,摧殘了我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他甚至一次都沒有想到過我是一個需要愛情的女人……”我想,你一定不會忘記卡列寧在彼得堡車站迎接安娜的場面吧。在寒冷、喧鬧、飄散著煙霧的站臺上,卡列寧顯得那樣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活象一個被外交禮儀操縱的木偶,在他身上,人們絲毫也感覺不到夫妻重逢時應有的親昵和欣喜,甚至看不到渥倫斯基的出現和鐵路職員的慘死在他冷漠的臉上激起的反應。他把安娜送上馬車,匆匆趕回官場去了。而安娜呢?踡縮在馬車角落里,為了鐵路職員的悲慘命運而渾身顫抖,一言不發,和卡列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使安娜最難以忍受的,是卡列寧時時刻刻、處心積慮地要把安娜納入他所習慣并奉為神圣不可更改的常軌之中,這就是以維持外表的體面為準則的上流社會的禮儀。托爾斯泰通過對奧布浪斯基家、薛杰巴茨基家、培脫西·特維斯卡雅公爵夫人等家庭和人物的描寫,揭示了上流社會的種種“混亂”和“不幸”:夫妻、父子、親眷間完全是一種互相欺騙玩弄的關系,通奸被看作是具有“幾分優美和偉大”的韻事……在這樣一個充斥著墮落和腐化的貴族社會中,維持外表的體面的唯一辦法就是說謊和虛偽。卡列寧正是一個虛偽透頂的人。他沉醉于“俄國不能沒有你”的奉承,而熱衷于勾心斗角、追逐名利,是虛偽;他對安娜毫無愛情可言,卻處處以一個體貼、忠厚的丈夫面目出現,也是虛偽;而他在安娜親口向他證實了和渥倫斯基的關系時的所作所為,更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虛偽。卡列寧為之憤怒而不可容忍的,并不是妻子的“不貞”,而是他的生活的正常秩序將被破壞,這一家庭“丑聞”將傳播開來,成為他的政敵攻擊他的口實,從而斷送掉他的官運。安娜之所以敢于向他和盤托出,是因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象水中的魚兒一樣,在虛偽中游泳、享受。不,我不讓他得到這種享受。我撕破了他想纏在我身上的虛偽的網,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反正一切都比虛偽和欺騙來得好些”。可是卡列寧呢?他語調鎮靜,措辭準確,冷冰冰地使人震驚:“好吧!但我要求保持現在這種表面上的常態,直到我采取維護我榮譽的措施時為止,我會把這些措施通知您的。”他不同意離婚的決定,實際是在繼續編織虛偽的網,使他自己顯得寬容,卻纏住安娜,把她推到一個受人譏笑唾罵而又無力掙脫的境地;當安娜病重,打電報叫他回去時,他固然擔心這是個“圈套”,他的在場將使孩子“合法化”,但更多的卻是考慮,如果他不回去,安娜真的死了,大家都要“責備”他。他怕這樣的責備,連夜趕回彼得堡,一路上卻盼著安娜快些死去;最后,他終于發展為從安娜那兒奪去了兒子謝寥沙,并且不準安娜和兒子見面,把殘酷的折磨從安娜推及到無辜的孩子身上。
卡列寧的冷漠、虛偽和殘忍,根子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而這正是當時俄國上流社會和官場的根本特點。顯然,卡列寧這一典型形象,已經成為托爾斯泰極力揭露和批判的沙皇專制制度和貴族階層的化身。因此,安娜對他的背棄和反抗,其意義也就由家庭沖突,而擴及為相當程度的對舊社會制度的反叛和挑戰。正是這一點,使她受到了整個上流社會的攻擊。可借的是,安娜把愛情的追求寄托在骨子里仍然不過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渥倫斯基身上,這就擺脫不了悲劇的命運。安娜和渥倫斯基的始合終離,同時也表現了安娜作為當時社會中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的貴族婦女的局限性。托爾斯泰的巨大同情和愛,顯然是傾注于安娜的。他引用《新約·羅馬人書》中的“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作為扉頁的題詞,可以說是替不得不走上臥軌自殺道路的安娜向舊的社會制度發出的強烈控訴!
托爾斯泰的這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廣泛的社會內容和激烈的批判精神的著名作品,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當時的俄國社會,得到巨大的藝術美的享受,同時當然也會給我們許多思想上的啟示。但是,如果因此便去硬充和效法某個角色,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或者以為欣賞者一定會去硬充和效法,便主張把它和欣賞者“隔絕”開來,無疑都是不正確的。說清楚這一點,我想,你的同學們的不同看法,大約可以開始接近了吧。
拉雜談這些,算作我參加討論的一點意見,自然是僅供參考。
此致茍禮!
華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