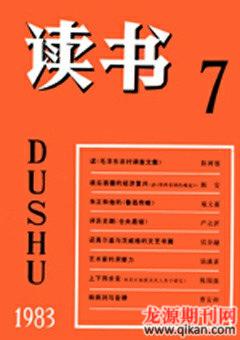譯語問題
1983-07-15 05:54:46吳希義
讀書 1983年7期
吳希義
今年的《讀書》第四期載了張隆溪同志的《管窺蠡測》,其中談及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的anti-hero現象,筆者共鳴頗多。
西德當代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倫茨就在他的《燈塔船》(Das Feuers-chiff)中讓主人翁弗賴塔克說:“我從來不是英雄,我也不想成為英雄。”十分有趣的是西德另一作家艾利希·凱斯特納也發表過十分相似的言談:“我不會是或變成英雄。而且我從未成為過英雄。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英雄。”海明威短篇小說《在異邦》(InAnother Country)中的美國兵身佩勛章卻為意大利孩子們所不齒,他想:“我曾經受過傷,這是真的,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實在地說來,受傷只是出了一次事故而已。”這樣的異邦、這樣的心境自然是
不過,筆者以為把anti-hero譯為“反英雄”稍嫌不妥。考anti-這個英語前綴,包含漢語的“反”、“抗”、“防”、“排除”等多種意義。就文學中的anti-hero而言,以筆者之管窺蠡測,似乎這個anti-里“排除”的味道更足更濃,作家們對傳統的英雄觀是取外位態,而非取對抗態,所以把anti-hero譯為“非英雄”值得一薦。筆者揣想,漢語的“非”更能傳神地譯出anti-hero中所蘊含的消極的否定和幽默的嘲弄。
筆者自感研討西方文學尚在藩籬之外,不敢存深入堂奧之想,僅以讀書寸得獻丑于前輩、內行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