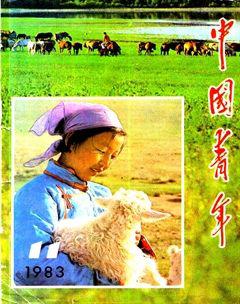社會達爾文主義遠溯近觀
肖紀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什么樣的理論呢?在一些青年看來,它似乎挺新穎。其實,他們對它的了解正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同樣處于朦朧、甚至無知的狀態。這就使我們感到很有必要對社會達爾文主義作一番歷史的回顧,對它復活的社會條件以及現實危害作一番考察。
一、達爾文的“失足”與赫胥黎的“鑰匙”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淵源
科學巨匠達爾文于1859年發表了震驚世界的《物種起源》一書,從而如列寧高度評價的那樣:“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看作彼此毫無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
青年時代的達爾文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學神學,他是手捧《圣經》登上英國皇家遠洋考察船貝格爾號的。五度春秋,物換星移,長期的環球考察,生物界辯證發展的真實圖景,使他從“創世說”的夢幻中幡然醒悟。《物種起源》這部被達爾文自己詼諧地稱為“魔王的圣經”的巨著,無疑是背叛《圣經》的宣言書。它象一發重磅炮彈擊中神壇,轟毀了虛幻的天國!從此,達爾文被驚慌失措的英國傳教士們視為“企圖消滅基督教的威脅者”。
達爾文不可磨滅的功績在于:他用歷史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考察了生物界,證實了整個生物界的親緣關系和共同起源,第一次科學地說明了生物進化的原因和動力,沉重地打擊了唯心主義的“神造論”和“目的論”,剝奪了上帝創造生物的權力。然而,作為一個治學嚴謹的博物學家,達爾文在闡述進化論時并未泛化到人類社會。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只是在書的結尾含蓄地提了一句:“人類的起源和歷史也將由此得到許多啟示”。但是,由于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以生存斗爭為主要內容的自然選擇學說(英文版《物種起源》的全稱即《通過自然選擇、即生存斗爭中適者生存的物種起源》),選擇學說是達爾文主義的主體,而生存斗爭和適者生存則是選擇學說的核心;又由于達爾文曾“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鄭重地聲稱“他的生存斗爭理論只是應用于整個動物界的馬爾薩斯理論”,所以達爾文實際上在這里“失足”了。這一“失足”,無異于暗示:社會學與生物學規律可以相互貫通。
如果說進化論是達爾文下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被達爾文稱為“我的總代表”的人類學先哲湯姆斯·赫胥黎曾致書達爾文,莊重表示:“為了您的理論,我準備接受火刑。”他寧愿充當“達爾文的斗犬”,決心“保衛這一高貴的著作”。經過多年對發生學、動物解剖學、古生物學、胚胎學等諸多學科的精心研究,赫胥黎冒著被斥為“一個邪惡的人”的攻擊,堅守“人獸同源”的信念,提出了“人猿同祖”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斷。這是赫胥黎作為一個達爾文主義者對進化論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然而,正如赫胥黎開誠布公地宣稱的那樣,他“一直致力于證明人和動物之間沒有猿猴本身之間還要寬的絕對的構造上的分界線”。1895年,他發表名著《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首次明確提出了“通常所謂的社會中的生存斗爭”的觀點。在赫胥黎看來,人生是一個角逐場,弱肉強食,勢所必然;勝則為富,敗則為囚,貧困和墮落不過是“社會生存斗爭”中選擇的結果。人類“競爭”的動因在于:“他們都有貪圖享受和逃避生活上的痛苦的天賦欲望”,“這是從他們的長長的一系列祖先——人類、猿類和禽獸那里繼承來的天性”,而這種天賦的“傾向力量是在生存斗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
此后,赫胥黎在論文《生存斗爭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中,提出了完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觀點。他說:“在倫理學者看來,動物界好比羅馬的格斗士場,各種生物受到很好的待遇,送去格斗。在格斗中最強健敏捷者、最狡猾者獲得生存,下一次就可以再格斗。”在人類社會中,“最弱者及最蠢者死滅。最頑強最狡猾者在別的意義上雖然并非最好,而在與環境斗爭時則是最適者,是最能生存者。人生就是不斷的自由競爭,除了狹窄的暫時的家族關系以外,霍布斯式的一切反對一切的斗爭,實際上是生存的常態。”
就這樣,赫胥黎從“人獸同源”的堅定信念出發,研究出人猿構造上的相似,推出了“人猿同祖”的唯物主義的結論;但卻從“人猿同祖”“人獸同源”得出人猿、人獸同性,并進而臆斷出人猿、人獸的社會存在同理。在赫胥黎的視線中,用倫理學的目光注視動物界,用生物學的尺度衡量人類社會,幾乎左右逢源,別無二致。從自然科學上的自發的唯物主義跌人到人類歷史領域中的唯心主義深淵,這是赫胥黎的哲學結局,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起點。
恩格斯遺憾地指出:由于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從古代世界崩潰時起,就統治著人的頭腦”,致使甚至“達爾文學派的最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赫胥黎自以為從達爾文的“啟示”中得到了啟示,找到了一把研究從猿到人的起源、進化的“鑰匙”,殊不知這是一把對不上鎖、開不了門的“鑰匙”。在奔騰不息的宇宙長河中,人類的起源和發展自有其迥異于生物進化的規律。恩格斯說:“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而以赫胥黎為主要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把歷史的發展和錯綜性的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概在貧乏而片面的‘生存斗爭中”,并斷定這是“社會永恒的自然規律”,這不能不被恩格斯哂為“十足的童稚之見”,“過于天真了”。其所以“天真”,在于他們不懂得:“一旦人們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
二、人性之光與獸性復歸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新影響
早在五十年代,作為資本主義罪惡制度、侵略政策及畸形社會現象的辯護工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已被批得臭不可聞,銷聲匿跡。可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使“斗爭哲學”充斥海內,“文攻武衛”遍及域中,父母反目,夫妻結怨,兄弟成仇……歷史的毒焰焚毀了天真的虔誠,思想的真空召喚著消逝的亡靈。社會達爾文主義被一些青年作為“新思想”接受了,發出了這樣的“崇論宏議”:
“人在社會中好比花園里的花朵,自己要盡量多地吸取營養,使自己開得更旺盛,不然養分就被別的花吸收了。”
“人就是這樣,我看透了,誰厲害誰爬得上去,誰不厲害,誰就該倒霉。”“社會就是這么發展:生存競爭,優勝劣敗。”
“人是最高等動物,但畢竟還是動物,逃脫不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生物競爭規律。人類社會是一個大競技場,人的角逐、競爭不過是涂上了文明的色彩,更高明、更巧妙、更隱蔽而已。”
人獸同源,決定了人不可能絕對超然于動物同類之外,決定了人類不可避免地要保持著它的自然屬性,有生之歡樂,死之恐懼,性之沖動,食之欲求,等等。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的知識僅足以使他比狐貍稍微狡猾些,比老虎更險惡些”;更不意味著“因而人類就不再致力于過一種高尚的生活”。人一旦從動物界脫穎而出,號稱“萬物之靈”,就有了與動物本質不同的屬性。馬克思有句名言:“人是人的本質。”這就是說,人具有他作為人的最高本質的特性,即“人是實踐的人”,“社會的人”。在人身上有著任何動物所不可能有的“社會實踐性”。人的社會實踐性,社會獨立性使人即使在自然屬性方面也遠遠高于他的祖先,也促進了人類意識屬性的產生、完善和發展。在同自然的關系中,人類不再被動地適應自然,消極地等待自然的恩賜,而是憑借自覺的能動性去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人類的勞動不僅使自然界人化,打上了人類意識的印記,同時也使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實現著自身的完善化。“作為完全的人”,他不僅有了自然的器官——“看、聽、嗅、嘗、觸”,是自然的存在物;還有了社會的器官——“思維、直觀、感受、意愿、活動、戀愛”,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一句話,具有了超然于獸性之上的人性的光芒。
我們并不簡單否認人類社會存在競爭,只是說人類的“競爭”遠非動物的競爭可相提并論。動物充其量是覓食棲身,為圖生存而爭;而人類的“競爭”呈現為人類歷史上的一系列的階級斗爭,從而“更有內容和更深刻得多”。我們也并不一般地反對競爭,只是提醒注意《共產黨宣言》中一個著名的論斷:“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改變”。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競爭”的指導思想截然不同,決定“競爭”的手段、方式等的不同。同是體育“競爭”,我國女排運動員是靠了頑強的拼搏精神,英勇奮斗,力挫群雄,兩度奪冠。她們是為振興中華而“拼”,為祖國榮譽而“搏”,為黨的事業而“奮”,為人民利益而“斗”。這決不是作為資本家的商品的資本主義國家運動員的思想境界可以相比的。同樣是科研“競爭”,在對拓撲動力系統的研究中,暨南大學講師周作領熱情幫助中國科技大學講師熊金城,而不是封鎖資料,囤積居奇。當有關部門根據熊文發表在先,決定把獎金給熊時,熊卻以周文投寄在前,拱手把“領先權”讓給了周。類似的例子在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等中國科技界泰斗中更是屢見不鮮。這與資本主義社會單純為牟取“專利”而不借沽名釣譽,剽竊成果,恃強凌弱又安能同日而語呢?足見,同是拼搏,有為公為私之別;同是奮斗,有為國為已之分。清濁不同流,涇渭兩分明。
至于說到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在利己主義支配下為了卑下的私利、庸俗的貪婪、淫蕩的情欲、粗暴的掠奪而進行的“競爭”,不過是反映了舊社會的痕跡,反映了在公有制不完善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社會弊端,說明了我們的道德觀念還需要不斷凈化。
三、哲學的迷霧與反理性色彩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存在主義的匯流
“文化大革命”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沉渣泛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再生歷史條件。“四人幫”覆滅,假馬克思主義破產。一部分青年產生了思想混亂。一時間“尋找失去了的自我”成了時髦的口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污流匯進了西方反理性哲學的濁水,復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又罩上這層濃厚的哲學迷霧,有了更大的迷惑性和吸引力。
反理性主義是西方現代唯心主義哲學的一股狂潮。它孽生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高度壟斷發展的歷史階段,一度成為壟斷資本主義政治的理論基礎。這一狂潮的祖師爺當首推叔本華,“意志決定論”就是他的思想“杰作”:意志是剛勇的盲者,理性則是完全受雇于意志的向導。人的理性不管就其起源還是實質,都“完全是服從意志的”。這一狂潮的推波助瀾者則是尼采,正是尼采用“權力意志”把叔本華的“意志決定論”進而推向反理性主義的高峰,為滅絕人性的法西斯主義“強權政治”涂脂抹粉。尼采哲學因而成為希特勒“強權政治”的理論支柱。
反理性主義的強弩之末是現代資產級階哲學中風靡一時的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這一當代反理性主義哲學的主要流派,發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布于整個世界。在資本主義哲學的殿堂中,它被一些頹廢、悲觀、空虛,“對明天失去了信心”的知識分子當作新福音供奉起來。這些失魂落魄的“西儒”視“自我”為“神座”,拾起“意志選擇”的“神簽”,唱起“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懦夫使自己成為懦夫”的“神曲”,祭起“絕對自由”的“神器”,企圖掙斷壟斷資本主義的鎖鏈,求得“存在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社會達爾文主義信徒的身上幾乎同時浸透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反理性”的汁液。馮大興就是典型的一個。他崇尚世界就是自我,覺得其他都與自己格格不入,互相敵對;感到只有在和客觀世界的抗爭、挑戰和報復中,才能取得精神的平衡、安寧和快樂。那位鼓吹“人類是個大競技場”的“斗士”洪國慶更是直言不諱:“我認定什么都是荒唐的,只有我的存在才是根本,我要拼命追求我所需要的滿足。”為此,他們將私有制社會通行的法則——“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作為自己追名逐利的道德信條。在他們心目中,為了人生之不朽,功蓋萬世固然好,罪惡滔天又何妨?“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其是非之顛倒,榮辱之莫辨,令人嘆為觀止。
請看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身上光怪陸離的反理性色彩吧:
其一、大肆宣揚“意志自由”。說什么:“我的最高信仰是自由”,“人生信條是自由”,把“個性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完善”當成唯一的生存目標。
其二、追求所謂的“人生價值”。不是有人稱頌盜竊殺人犯馮大興是“生活的強者”,“敢于向社會挑戰”,說“雖然他被擊敗了,但他的價值還存在”嗎?從而,“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價值,就應該選擇最適當的手段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其三、視“放蕩冷酷”為“生存之道”。放縱的生活,燈紅酒綠;淫蕩的情調,朝秦暮楚。尤為令人驚嘆的是他們那種冷酷:割斷了友愛,疏遠了家庭,充滿了殺機。
其四、對冒險主義推崇備至。“不成功即成仁,人生就應該如此,充滿冒險,盡管毀了,可他的名卻為人知曉,不也是一種驕傲嗎?”
其五、對金錢物質的極度貪婪。奉“金錢無臭味”為金科玉律,希圖在金錢世界中消除搏斗的困乏和填補心靈的空虛。
透過存在主義的“哲理”:“他人是我的地獄”,“我們中的每個人對別人都是劊子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真諦”:“一切人反對一切人”,“人對人是狼”,我們看到,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存在主義哲學匯合的污流濁水腐蝕著一些青年的靈魂,污染了他們的思想,甚至吞噬了他們的軀體。這樣一套危險的理論,難道還不應該引起人們,特別是青年們的警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