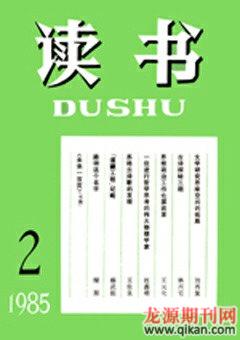東西方的不同管理藝術
戴金珊
一九八一年,美國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兩位教授合寫的《日本企業管理藝術》剛問世,立即成了一本暢銷書,并被一些美國著名大學指定為企業管理必讀書。這本只有十幾萬字的著作所以不脛而走,是因為它通過東西方管理技能的比較,向美國企業界等提出了一個嚴肅問題:為什么日本這樣一個人口十分擁擠、資源極其貧乏的國家,會在戰后不長的時期內,使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三位,會一個一個地奪走美國汽車、煉鋼、造船、手表、照相機、家用電器等工業在世界上的優先地位?
三個“S”對七個“S”
多少年中,許多美國人對自己的管理理論和成績一直十分自信,沾沾自喜。對于日本在勞動生產率和工作成果的進展數字,“先是不肯承認,繼之,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第3頁)。美國的管理果真已經盡善盡美了嗎?美國在競爭中的失利果真沒有挽回的余地了嗎?《藝術》的作者以其新穎的模型證明:美國工業的一些方面輸于日本,主要原因恰恰就在管理技能上,而不是別的。如果美國企業界正視這一點,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努力吸收外來營養,那么一定能扭轉劣勢,重振旗鼓。
作者的模型認為:考察企業經營成功與否,可以用七個“S”字母開頭的要素衡量。這七個要素是:戰略(Strategy)、結構(Structure)、制度(System)、人員(Staff)、技能(Skills)、作風(Style)、最高目標(Superordinategoals)。戰略,就是分配企業有限資源的計劃或措施,是企業達到自己目標的大政方針。結構,即企業組織機構圖所具有的特征,包括企業中不同職能部門的劃分、企業實行集權或分權等。制度,表現為各種規定的報告和例行的程序,例如定期報表、會議形式等。人員,指的是企業內部人員的組成狀況。作風,即主要經理人員在達到企業目標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性格,也包括企業的傳統作風。技能,為企業主要人員或整個企業所具有的工作能力。最高目標則是一個企業灌輸給成員的重要意義或精神價值觀念。
作者尖銳地指出:用上述七個要素來對照美國的企業,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向來過分重視三個硬性要素(戰略、結構、制度)的作用,而輕視了后四個軟要素的作用。這種狀態的直接成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學術界對硬性要素特別注意。美國商學院幾十年的努力,使“硬三角”的研究大大深化,人們對它的認識也更加深刻。這三種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較易于通過分析、定量、邏輯和系統進行調查研究,因而如果重視不同特點的另四個軟要素,就被人說成是講人情、“不科學”而不屑一顧。
與美國企業不同,日本企業不但重視硬三角,而且不放過軟四件。日本在引進西方管理理論的同時,不忘記提煉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加以折衷融合,使西方的唯理主義與東方的奇妙心靈主義結合得當。這樣,日本的企業便擁有七個管理要素。
吉寧氣派與松下風格
美日企業管理上的差異,在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日本松下電器公司的比較中,可以一目了然。
于一九七九年退休的哈羅德·吉寧,曾經主管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近二十年。任職期間,他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輝煌的:他使公司的年銷售額由一九五九年的7.65億美元,猛升到一九七七年的118億美元;銷售額對資產的比率由一九五九年的0.82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1.14。他的公司由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聯合企業,所取得的利益也為美國其他企業望塵莫及。然而,他一退休,公司的營業便隨之一蹶不振:在《幸福》雜志所舉全美五百家最大工業公司中,雖然它的銷售額居于第十一位,資產居第十二位,但凈利占銷售額的比率卻降為第四百三十五位,凈利占股東產權的比率更低到第四百五十一位。相比之下,松下電器公司的蓬勃發展并不因松下幸之助的退休而遜色。一九七九年,松下退休后的第六年,公司的銷售利潤率達到4.2%,幾乎是西門子公司和菲力普公司的兩倍;同年,公司每個職工平均銷售額相當于許多競爭者(包括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兩倍。
松下公司久盛不衰,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則由盛而衰。道理何在?追溯其最主要原因,不在戰略上,不在矩陣式組織結構上,而且也不在正式的制度上。“真正的區別是在其他要素上,即管理作風、人事政策,以及最重要的精神或價值觀上。當然,還有管理所有上述這些要素的人的技能”。
作者分析說,吉寧似乎認為:企業的其他人只是用來達到他個人目標的客體。一個主要事實是:吉寧不關心下屬的精神世界,而只是要求他們一旦進入這個組織,就象機器上的一個部件一樣發揮作用,圍繞他轉。他的管理實際上是靠個人技能來維持,只體現了個人才能、膽略和氣派。他以高超的記憶力和無窮的精力閱讀處理企業報告,窮根究底地盤問每個問題,追求“無容置疑的事實”。這確實給公司決策帶來可靠依據,但同時限制了下屬的革新愿望,迫使他們以超常的工作量完成任務。他所制定的制約和平衡下屬的方法,固然為獲得準確事實所不可少,但也使企業直線人員和參謀人員(起監督作用)間的磨擦加劇,并導致成本的增加。他以帶有質問和敵對氣氛的大型會議方式做決策,大多數下屬覺得不是滋味。有個集團副總經理回憶這種會議時心有余悸地說:“對于一個陷于嚴重困難的人來說,就好象在一個場院看見一只受了傷的公雞正要被其他的雞啄死一樣,如果吉寧已將目標對準一個人,就等于暗示參謀人員向他開火,然后他袖手旁觀。”
這種不顧一切的強硬方式,吉寧不但不視為粗暴,而且自得地認為:“只有在面對面開會的高壓鍋似的氣氛下,才可能過濾出來可靠的事實,才能將它們蒸餾成為健全而又可行的決策。”而對于他覺得不稱職的下屬,他又動不動就加以解雇。在這種高壓氣氛中工作,固然能獲得高于一般公司大約10—12%的優薪,但對于那些比較倔強、有自信心和作為,在工作中追求更高精神價值的人,他們怎么會愿意為吉寧工作很久呢?吉寧不能意識到此,因而無法培養出一位強有力的第二號人物。其結果:從他手下出走的人,往往成為別的大公司出色的總裁,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則隨著吉寧的退休而衰落。
與吉寧相比,松下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認識到:企業的其他人既是供使用的客體,也是應該尊重的主體。企業所要達到的,既是領導個人的,也是全體職工的目標。從這個思想出發,松下非常重視向下屬灌輸管理哲學。在松下公司,每個人都要接受價值準則的培訓。他們必須記住公司的基本經營原則:“認清我們作為工業家所應盡的職責是:鼓勵進步,增進社會福利,并致力于世界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記住職工信條:“只有通過公司每個成員的協力和合作才能實現進步和發展。”必須記住七個精神價值觀:“一、工業報國;二、光明正大;三、團結一致;四、奮斗向上;五、禮貌謙讓;六、適應形勢;七、感恩報德。”
每天早上八點鐘,全日本的松下職工都在朗誦這些價值準則,并一起唱公司歌曲。這在西方人看來可能是愚蠢可笑的,但是正如一位松下高級管理者所說,當全體職工都這樣做時,“好象我們已經融合一體了”。松下的成功,正是來源于職工對工作意義的更高一級的理解,來源于職工融合的力量。
當然,如果松下只是滿足于向職工宣傳這些堂皇的觀念,并不能確保其事業的輝煌。松下本人在其管理中,堅持身體力行這些觀念。在這個公司里,看不到吉寧那種咄咄逼人的領導風格。當下屬不稱職時,他們被調職或者降級,但不會蒙受羞辱和被革職,而且能得到從教訓中再成長的機會。反之,職工的建議則得到公開鼓勵和不同等級的獎賞,以至僅一九七九年一年,每個職工平均提出的建議多達二十五條。他還善于培訓、選拔、重用人才,發揮其作用,以保證企業后繼有人,代代相傳。一個有力的例子是,他能大膽重用會計專家高橋荒太郎作為自己的左右手,并在自覺年老力衰時退居二線,委以大權。對于領導如何適應不斷擴大的公司,他深有體會地說:“當你僅有一百名職工時,你必須站在第一線。……但如果這個集團發展到一千人,你就不可能再留在第一線,而是身居其中。當企業增長至一萬職工時,你就必須退居到后面,并對職工們表示敬意和謝意。”這一現身說法,表明了一個高明管理者所具有的風度。
吉寧在三個硬件之外,依靠個人的技能使企業發達,這無疑是巨大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具有濃厚的獨奏味道。松下在硬件之外,依靠企業的最高目標來培訓、使用職工,依靠自己的風格來感染下屬,也獲得巨大成就,這種成就具有交響樂的雄壯磅礴氣勢。后者無疑更加能激動人心。兩位領導人退休后兩個公司的戲劇性發展結果,提供了雄辯的例證。
民族文化和歷史包袱
《藝術》一書令我們感興趣的是,作者并非到此而止,而是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西方管理技能形成的思想淵源以及它所面臨的尖銳挑戰。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是美國企業界的一個縮影。吉寧在管理這個公司中表現出來的突出個人、獨力拼搏形象,正是西方社會數百年思想塑造出來的典型。作者引用心理學家詹姆斯·巴根托爾的話說,西方社會在五百年前就發明了個人獨立觀念,從此以后,這種觀念成為西方一個不斷增長的勢力。哲學家洛克、霍布士,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等人,更為其推波助瀾,十分強調個人至上和自力更生的社會,對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影響殊深。在另一面,被歌頌的美國歷史上的拓荒運動,要求人們的獨立冒險和進取精神,使得上述價值觀的地位更加崇高化。根深蒂固的西方個人奮斗思想,真是源遠流長。
然而,時代不同了。民族的文化傳統也可能轉化為歷史的包袱。“顯然,美國的企業管理制度曾由于強調獨立而得到了力量,但在當時是基于拓荒,即提供更多創業機會的歷史需要。五十年來,我們已從一個多數人靠獨立經營農場生活的社會,轉變為擁有許多城市的國家;從一個‘無限資源時期進入一個普遍缺乏資源的時代。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在巨大而復雜的企業中工作,與其他人密切地接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傳統的價值觀,特別是堅持極端的方式,已不適應我們的需要。美國西部的廣闊邊遠地區曾經容納過成千上萬從事艱苦開拓工作的個體戶,但是要想讓幾千個公司雇用千百萬習慣于單干并經常流動的職工,則是行不通的。”西方的個人至上該是重新看待的時候了。
吉寧對于下屬精神生活的漠不關心,同樣有長遠的根源。經過中世紀的演變,西方社會政與教分家,形成各自的獨立勢力和機構:教會是人的信仰和精神生活的監護人,而政府機構和后來出現的商業機構則起著提供人類在世間生存所需的作用。人的精神生活被理所當然地拒絕于管理組織的門外。緊接著,機器生產時代到來了,生產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概念出現了。這是形成西方對人、組織、社會看法的另一重大事件。這個時候,作為勞動力的人,在生產過程中已成為一個具體化和標準化的組成部分,如同機器零件一般。而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只在工作場所之外得到承認,他的喜怒哀樂只有在工作之后才有發泄之地。這種把人的生產和生活在時空上完全分割開來的概念持續至今,使得西方人對于工廠生活感到枯燥無味,厭惡情緒日增。
作者意味深長地指出,事實上,現代企業在職工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職工們不但在這里工作,他們的日常社交活動也在這里進行;他們和公司的關系、和工作的關系,往往成為公司以外社會的基礎。甚至人們第一次見面,所問的第一個問題也常是:你是做什么的?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美國,“大多數就業者不必為短期的‘生存而工作,他們除了待遇和發展機會以外,逐漸注意到工作上的其他收獲,例如,自己所喜愛的工作,喜歡共同工作的同事,以及工作的‘意義等。”在這種新的歷史環境下,企業主仍然對職工精神生活不聞不問,任他們在逆境中自行照料自己,或從朋友、家庭和宗教關系中去尋求不可靠的精神支持,那還能指望職工積極性得到發揮嗎?
《藝術》作者的這些見解,是發人深省的。
當我們回首中華民族近百年的歷史,不能不痛心地看到:中國經濟發展走過的彎路已經不少了。辛亥革命前,中國資產階級就曾探索過民族經濟的發展道路。他們信仰過自由主義經濟學,信仰過歷史學派經濟學,但在反復比較中,他們還是傾向信仰從日本傳進來的折衷性經濟學,并滿懷信心地構畫中國經濟的未來。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綱領,就是一個明確的表達。他們似乎要找到正確的方向了,然而失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混戰,徹底粉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理想。在艱難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革命理論與本國實踐相結合,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勝利,為中國經濟的振興提供了先決條件。遺憾的是,年輕的共和國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無知又往往造成窒息人們創造生機的教條。中國又一次走向中國資產階級曾經走過的、從單一理論出發、照搬某種現成模式的彎路。今天,不同階段走過的彎路,應該足以使我們清醒: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夠照搬某種現成模式。
中國必須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東西很多,其中包括一些經濟、經營理論和方法。這是無疑的。但我們隨時應該提醒自己: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也是特定國度、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正如《藝術》一書所揭示的,其理論和方法也有相伴的矛盾,并且不可避免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顯示其局限性。我們應該注意權衡折衷,取長去短,咀嚼消化,發展出本國適用的東西。只有這樣,經濟才能由弱轉強,趕超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