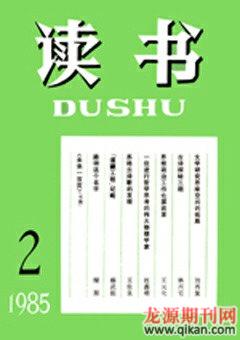一對范疇——“概念”和“存在”
孟 辯
在黑格爾的《小邏輯》中,有許多地方,把“概念”和“存在”作為一對統一而又矛盾的范疇提出來,現摘引幾則在下面:
一、“但一切有限事物,自在地都具有一種不真實性,因為凡物莫不有其概念,有其存在,而其存在總不能與概念相符合。因此,所有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毀滅,而其概念與存在間的不符合,都由此表現出來。個別動物以類為其概念,通過個別動物的死亡,類便從其個別性里解脫出來了。”(中譯本,第86頁)
二、“譬如,我們常說到一個計劃或一個目標的實在,意思是指這個計劃或目標不只是內在的主觀的觀念,而且是實現了某時某地的定在。在同樣意義之下,我們也可以說,肉體是靈魂的實在,法權是自由的實在,或普遍地說,世界是神圣理念的實在。此外我們還用實在一詞來表示另外一種意思,即用來指謂一物遵循它的本性或概念而活動。譬如,當我們說:‘這是一真正的〔或實在的〕事業,或“這是一真正的〔或實在的〕人,這里‘真正〔或實在〕并不指直接的外表存在,而是指一個存在符合其概念。”(第203—204頁)
三、“在這里,一般地必須記著,在哲學討論里‘不真一詞,并不是指不真的事物不存在。一個壞的政府,一個有病的身體,也許老是在那里存在著。但這些東西卻是不真的,因為它們的概念〔名〕和它們的實在〔實〕彼此不相符合。”(第282頁)
此外,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也對這一對范疇談了許多。在這里,沒有必要加以引述。
黑格爾用淺顯的例子來說明這對范疇。一個壞的政府,一個有病的身體,是不符合它的概念的,換句話說,要符合政府的概念,就要是一個好的政府,要符合身體的概念,就必須是一個健康的身體。在我們現代的言語中,也常有這種說法。我們也常常說,某個事物不是真正的某物,如說某個國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某個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等。黑格爾把日常語言中所說不真,不好的某種事物,界說為存在不符合概念。
黑格爾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事物都有其概念,有其存在,這兩方面是統一的,又是對立的。凡是對辯證法稍具常識的人都能理解這一點。
黑格爾是唯心論者,在他看來,“思維過程,它在觀念這個名稱下轉化為一個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現實過程不過是它的外部現象。”(馬克思語,《資本論》第一卷,XXⅢ頁,郭大力、王亞南譯)所以,他說:肉體是靈魂的實在,法權是自由的實在,世界是神圣理念的實在。在這一點上,唯物論者當然是持相反的看法的,在唯物論者看來,物質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產生的。
對于“概念”和“存在”這一對范疇,在我看來,唯物論者也是可以采用的,用以改進、豐富我們的思想方法,使我們的思想方法更精確、更科學。只是要對這一對范疇賦予新的解釋、新的內容。
世界上的物質存在,就其與人的勞動,實踐的關系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然存在的,并沒有人的勞動參與其間,更不是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日月星辰,長江大河(人造運河是例外),地下礦藏等等都是。
另一種事物是經過人的勞動、實踐所創造的,或者是人的勞動參與其生長的。各種農作物,工業產品,等等。馬克思說:“……蜘蛛的操作,和織工的操作類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還使許多以建筑師為業的人慚愧。但是,使最拙劣的建筑師和最巧妙的蜜蜂相比顯得優越的,自始就是這個事實:建筑師在以蜂蠟構成蜂房以前,已經在他的頭腦中把它構成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已經在勞動過程開始時,存在于勞動者的觀念中,所以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的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中實現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把它當作規律來規定他的行動的式樣和方法,使他的意志從屬于這個目的。……”(同上書,第172頁)
關于人的社會行為,也可以這樣說。從人的社會行為中,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首先是毛澤東同志的政治指導、軍事指導分不開的,是來源于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重大的戰略決策的。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到一八九三年熱月政變這一時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和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闡述的政治學說有關系的,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甚至把盧梭的信念寫成法國憲法的條文。
當然,人的觀念在勞動過程中的作用和在社會、政治變革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人的觀念在政治、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不象在勞動過程中那樣容易為人看得清楚。人的觀念在社會、政治變革中的作用,是指它的指導思想、政治學說、經濟學說、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等等來說的。人的觀念在社會、政治變革中起作用,要受到歷史條件、地理條件、社會心理等因素的影響,為這些因素所制約。但人的觀念在社會、政治變革中的實現與人的觀念在勞動過程中的實現,則是相同的。
在應用這一對范疇——概念與存在——觀察客觀事物時,如果把“概念”理解為觀念,唯物論者遇到了困難,因為在有些事物,——即未經過人的勞動、人的實踐活動而自然存在的事物,其中并沒有人的觀念起作用或曾經起過作用。而在黑格爾,是沒有這個困難,因為他是唯心論者,在他看來,一切事物都是觀念的外化。唯物論者要采納這一對范疇必須賦予這里的“概念”以另一種含義,而具有這種含義的這一對范疇,適用于一切事物,既適用于自然存在的事物,又適用于經過人的勞動而形成的事物。
可以賦予“概念”以這樣的含義,即任何事物中的本質的必然的規定性,反映在人的思想上就是該事物應有的規定性。這里舉一個例子。一個嬰兒生下來就是生理上畸形的,我們可以說,這個嬰兒不符合“人”這一具體事物的概念。這里所謂“人”的概念是說人生下來,就應該生理上是正常的,有正常的四肢以及各種器官,而這個嬰兒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說它是畸形的。在這個嬰兒的產生過程中,人的觀念是沒有起過作用的。當然,這個畸形的嬰兒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只是沒有人的觀點在其中起作用。
賦予“概念”以這樣的含義,即概念是事物中的本質的、必然的、應有的規定性,凡事物具有這些規定性,即是存在符合于其概念,凡事物缺乏或不完全具備這些規定性的,即是存在不符合或者是不完全符合于其概念,這樣,可以把這一對范疇、概念和存在運用于一切客觀事物,不僅可以用于經過人的實踐產生的事物,而且可以用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事物。
要詳細研究這一對范疇,需要與其他范疇做些比較,這是一項比較繁重的勞作,本文只能稍稍說一點意見,說明這對范疇與其他范疇的區別。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提出過另一對范疇。他說: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這里,他提出合乎理性的和現實的這一對范疇,他的意思是“合乎理性的”或遲或早,終有一天要出現的;凡是現實的,不合乎理性的,或遲或早,終有一天是要消逝的。他這里說是事物的變化,從有到無,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概念”與“存在”這一對范疇說的是在現存的事物中有概念,符合理性的規定性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符合概念,也可能不符合概念。這兩對范疇說的事物的不同的方面,或是說是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事物。
這一對范疇——概念和存在——和“一般”和“個別”這一對范疇也不盡相同。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個別具有“一般”的屬性,如“人”這個一般存在于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這些個別的人之中,而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具有“人”的屬性。
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提出的“概念”與“存在”這一對范疇和其他范疇的異同,需要細致的研究,本文做不到這一點。
這一篇短文認為唯物論者應該采用“概念”和“存在”這一對范疇,用以觀察事物,這個意見希望得到哲學界的指教和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