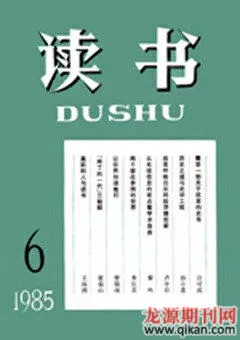樸學家的“悲”和“恨”
胡發貴
清代,尤其是乾嘉間,樸學(又稱漢學)在沉默了千余年后又忽然蘇醒、活躍起來,乾、嘉學風很快風靡全國,以至“家稱賈馬、人說許鄭”。乾嘉學派的興衰,距今不遠,可供考察、研究的典籍不少,中華書局新近點校出版的《國朝漢學師承記》是其中較為有用的,雖系舊籍,認真讀來,每可產生新意。
清代樸學的興起,固然與皇上的倡導有關,凡走這條路的大多前程如錦。但是仔細看看當時知識分子的情況,深感事實并不盡然;青紫加身、得策名廊廟的漢學家固然大有人在,但“非悲則恨”的飽學碩儒也確可指數。君若不信,請看江先生給我們描繪的兩個栩栩如生的漢學家:一位是“善哭”的武億、一位是“工罵”的汪中。
江藩寫道:(武億)“性善哭。館于笥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又,“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于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后,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見71頁)。
對于汪中的“罵”,江藩寫道:“……(汪中于)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低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見113頁)
武億,乾隆庚子年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官知縣,一身而功名利祿全矣,其悲何由?江藩曾叩之,答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71頁)。洪稚存、黃仲則庚子年與武億同考,兩人均落第,以至“流寓日下,貧不能歸”。盛世之下,文人學士如此狼狽,不能不令人唏噓。武億之涕泣明為哀友,實是在為無數優秀人才被科舉制扼殺而唱的挽歌!帖括之學不知桎梏了多少精湛的思想和熱情澎湃的情思;尤其在清代,文網密布,考官出題觸諱可殺,莘莘學子孰不懼怕!汪中曾被逼得“病怔怔”;漢學的吳派首領惠棟多次入考,均榜上無名;皖派領袖、一代樸學大師戴震更慘,一生六次入考,耗去無數心血,均名落孫山,以至一生悒郁不得志,正當壯年就溘然辭世。英才隕落,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友之不幸可泣,而己之坎坷也堪悲。武億任縣令時,和
武億之哭,“其哭有懷”;汪中之“罵”,又豈罵中無因!據江藩說,“君一生坎坷不遇”(114頁),晚年漂泊流浪,死于僧舍。汪中嘗著《自序》一文,嘆運命多蹇:“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時”;“余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余,……望實交隕”;“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由窮而悲,由悲而恨,由恨而痛罵,“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均見114—115頁),可見汪中的罵,一悲其命運之不濟,二怒世道之黑暗。汪中的凄涼和悲傷,可以說是當時漢學家們不幸遭遇的一個縮影。如《漢學師承記》的作者江藩本人,“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缽盂求食”,激憤之極,“長歌當哭”(115頁)!“博覽群書、性癖古籍”的余古農先生,“貧病交攻,……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于歌詠”(32頁);大漢學家惠棟,不僅功名不就,且又“饑寒困頓,甚于寒素”(23頁);漢學集大成者戴震,“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師,困于逆旅,
不論是武億的“涕泣有聲”,還是汪中的“赤口燒城”,都是當時廣大知識分子不平之心聲!孰使之不平?——正是崇文尊儒的列代圣君及其反動的專制統治。這一頁歷史,今天早已永遠翻過去了。但是讀一讀《漢學師承記》,對于我們研治清代學術史,仍然是不無益處的。
(《國朝漢學師承記》,〔清〕江藩著,鐘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0.7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