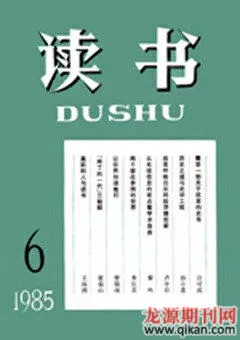鑒賞理論的搜集
臧 力 黃心村
文藝鑒賞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強調鑒賞學研究,其目的不應只限于為文藝批評增加活力,而應把鑒賞看作是從美學、心理學等多角度研究文藝消費規律的一門邊緣性學科。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鑒賞文存》(龍協濤編)一書,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長期以來對鑒賞學研究的忽視和怠慢。誠如王朝聞先生在書的代序里所說,《鑒賞文存》“預示著未來的新收獲”。
《鑒賞文存》薈萃了五四以來諸多名家談鑒賞理論的重要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所談及的鑒賞學理論問題,具有權威性的理論價值和不容忽略的代表性,建立起了一個鑒賞學理論的構架。一些文章,孤立地讀或許不大能看清其理論價值,然而一旦由編者總匯成書,就構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些富于個性的理論闡述,也就愈發引人注目了。
全書在編排方面頗具匠心。編者打破了通常的按時代和作者順序簡單羅列文章的慣例,根據鑒賞學理論所涉及到的問題的內在邏輯編排成:一、什么叫鑒賞?它與創作、批評、研究的關系;二、鑒賞活動的規律和特點;三、鑒賞力的培養和提高三輯。這樣的編排,對讀者形成系統的鑒賞學理論的知識結構是大有裨益的。編者在編后記里直述這樣編選排列的目的是:“使讀者不但能從單篇文章中獲得教益,而且通觀全書后,對整個鑒賞理論問題又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的認識,對五四以來一些重要鑒賞觀點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又有一個歷史的了解。”前一個目的,可望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對五四以來一些重要鑒賞觀點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又有一個歷史的了解,”這一目的,恐怕由于上述的編排,反而不易達到了。
本書三個專輯的編排,都能符合標題所限定的內容特點。第一輯里,編者采用循序漸進而又有所側重的方法選文。譬如在鑒賞與批評、研究的關系問題上,編者收入文章就相對多些。這方面權威性的文章,當首推毛星的《形象、感受和批評》和朱光潛的《“靈魂在杰作中的冒險”》。其它如錢歌川的《什么是鑒賞的批評》也很具特色,讀者對文中的觀點,或各有自己的見解而不必完全茍同,但它所獨有的那種深刻的啟發價值,卻是不容抹殺的。文藝鑒賞,是人們對鑒賞對象(主要是文學和藝術)的感受、體驗、品鑒和藝術再創造,是一種積極的滲透著審美意識和情感享受的精神活動。從系統論的觀點看,它又表現為一種認識活動的循環過程。其中的理性色彩是顯而易見的,但問題是如何看待它。這種理性色彩是否構成了文藝鑒賞活動的本質特點?它在文藝鑒賞活動中的地位怎樣?過于強調它對文藝鑒賞活動的影響和作用是不是恰當?這些問題都可從《什么是鑒賞的批評》一文中得到某些意味深長的啟發。第二輯里,編者挖掘出了一些論及了鑒賞學理論的核心問題、但長期被束之高閣的重要文章。如鑒賞學理論中的直覺說,由于人們歷來貶斥西方文藝理論中的直覺主義,故對直覺說的價值長期以來認識不足。收入本輯的朱光潛先生的《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一文,則對直覺說作了清澈而透辟的闡釋,指出文藝鑒賞的真諦“就在能跳出習慣的圈套,把事物擺在適當的距離以外去看,丟開它們的習慣的聯想,聚精會神地觀照它們的本來面目。”這是從美學意義上對鑒賞學理論中主觀性和客觀性的關系所作的論斷。目前出版的文藝理論和美學著作中,有的把鑒賞學理論中的直覺說,例列在謬說存照的位置上,所以重閱朱先生的舊文,是應該能起到拓展人們的思路的作用的。再如,鑒賞學理論中的移情說,這也是一個長期以來為人們所漠然視之的重要問題。朱光潛先生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一文就談到了它,不過朱先生似乎并未很明確地把“移情作用”與文藝鑒賞當成一個理論問題來闡述,故還不能稱之為專論。西方文藝理論中的移情說類似于我們的通感說。六十年代錢鐘書先生的《通感》問世,但又把著眼點放在修辭學上。直到近年,才有人從鑒賞學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出發,自覺地用理論語言概括了通感與文藝鑒賞的關系,如金開誠的《通感與藝術欣賞答問》和李丕顯的《談“移情”與“共鳴”》。這兩篇文章同談鑒賞學理論中的移情或通感問題,而觀點則不盡相同,卻又都能自圓其說。對比來看,定會獲益。第三輯將一些論述鑒賞力問題的通論性質的文章置于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的文章,諸如俞平伯的《略談詩詞的欣賞》和楊晦的《怎樣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等,則都是就某一專題而論的,有其專門性。此兩部分文章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鑒賞文存》,龍協濤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2.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