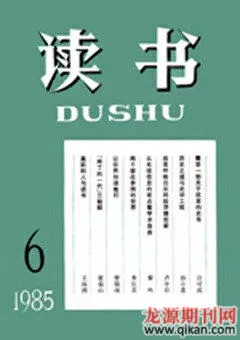書門偶拾
馮英子
講到讀書,有人說開卷有益,有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兩種說法各不相同,也各有其偏頗的一面。其實照我看來,這兩句話倒是有機地聯系,不可偏廢的。
盡信書,不如無書。這話何嘗不對,因為有些書說真話不多,說假話不少,你倘然完全相信了他,勢必上當無疑。五七年那一陣子,有些人就是太相信書上的話,對照古本,言必有據,結果掙來一頂帽子,幾乎不得翻身。有的人要燒書,有的人要摔筆,雖不屬于“吃一塹,長一智”之列,其心是可原的。不過,如果你讀了書真正動動腦筋,把說的和做的對照一下,也許能悟出一點道理,看清人世間的魍魎,不也就是開卷有益嗎?照現在的話說,這益,不僅有正面的教育,也有反面的教訓。
宋朝有位太宗皇帝,是趙匡胤的弟弟,據說他的位置是哥哥讓給他的,然而從他一做皇帝,嫂嫂那樣誠惶誠恐的樣子看,誰敢說燭影搖紅,不是千古疑案。不過做了皇帝,總是“今上圣明”,毋庸置疑。宋人江少虞編的《宋朝事實類苑》中,有一段引這位太宗皇帝的“圣訓”說:“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游觀之樂,內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看看這幾句話,不是非常非常“圣明”的嗎?可是有另一本沈德符的《野獲篇》中說:“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圖》,太宗戴幞頭,面黔色而體肥,周后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額不勝之狀。”我也看見過這張畫,說得粗俗一點,其實是這位太宗皇帝強奸小周后之圖。這個“內卻聲色之娛”的皇帝,原來是這么一票貨色。倘然只看前一段,那末盡信書不如無書;但倘若把兩段都看了,你就懂得在“圣明”的背后又是怎么一回事,不是開卷有益了嗎?
明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他殺戮功臣,是人所共知的,什么胡惟庸案、汪廣洋案、藍玉案,牽涉者幾十萬人,說實話,要不是經過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我是不會相信這段歷史的。偶翻《明實錄》,卻發現此君議論漢高唐宗的優劣時說:“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宏矣。太宗雖規摹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己用,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你看,他做的和講的,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倘在現代,把做的和說的割裂開來,那倒更是家常便飯了,而且很有點青出于藍,比古人更加高明了,假話連篇,面不改色。有一次我看見一個朋友寫的回憶,說他一生“毋負于國,毋虧于人”。其實據我知道,此君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曾向日本人獻過兩架飛機,讓日本人用飛機向中國人民頭上投炸彈。毋負于國,是那一個“國”呢?如果你不懂一點歷史,僅僅看他的文章,也非上當不可。從這里得到的印證,我以為從正面、反面兩方面去讀,那末“開卷”是應當“有益”的。
現在一講讀書,有的朋友總想開出一張書單,告訴人什么可讀,什么不可以讀,好象非要給人規定一條道路,讓后來者按著自己的節拍去跳舞,才比較放心。其實學問之道,不僅貴以專,還要貴以博,你不積累更多的知識,不懂得更多的道理,你是弄不清楚書上所講的真正內容的。我們中國歷來有一條規定,叫做“為君父諱”,皇帝和老子做的壞事,不能直書,只可用婉辭。所謂《熙陵幸小周后圖》,就是這樣的貨色。老百姓一切觸犯禁令之事,到了“君父”身上,卻變成風流佳話了。所以,明明是死亡,書上卻要寫成“仙去”,明明是被放逐或做俘虜,書上卻要寫成“巡狩”。那位宋太宗的子孫徽欽二帝,是被金人俘虜去的,坐井觀天,窮愁潦倒。正如徽宗自己所填的《燕山亭》詞中說:“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凄涼極點。但是寫史的人卻說“徽欽北狩”。倘用現在的直譯,那就是他們到北方打獵去了。你如果相信了這樣的史筆,怎么能弄清楚中國的歷史呢?幸而幾千年來,“輿論一律”這條道路始終行不通,李斯先生的“以吏為師”,董仲舒先生的“罷黜百家”,都不過是主觀的愿望,而許多在野的作品卻往往寫了一點真實。比方那幅《熙陵幸小周后圖》上,元朝有一個姓馮的學士就題過一首詩說:“江南剩有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吹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雖然他講的是因果報應,但卻道出了宋太宗丑行的真實。所以,我倒不主張非開一張書目,那些可讀,那些不可讀,因為任何一本書,如果你用一點心去看,都可以找到點什么的。
有些朋友把社會上偶然出現的事物,歸之于某些書本的引誘,如有人去峨嵋山求仙,有人去少林家學武等等,其實這不是讀書太多,恰巧是讀書太少的結果。讀《紅樓夢》便以為自己是寶哥哥或林妹妹,讀《水滸傳》便想學武松和魯智深,不能說絕無此事,但畢竟是少之又少的個別現象,不能怪書本的。薄伽丘的《十日談》,其實是鞭撻宗教的作品,而有的人卻把它當作“淫書”,也正如《金瓶梅》被人歪曲一樣,抽掉了現實意義,追求不健康的部分了。但是總起來說,今天社會上許多做壞事的壞人中,歸根結蒂,還是不讀書或少讀書的人占多數吧。把有些由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發生的現象,歸咎于書本,無論如何不太公平。
盡信書,不如無書。而要懂得這個不如無書的理由,找到不如無書的根據,卻還是要靠讀書,讀各種書。宋人講的“格物致知”,不格物是不能致知的,其實讀書也是一種格物。一個人不打防疫針,是很少免疫力的,在這一點上,我以為開卷有益的益,也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