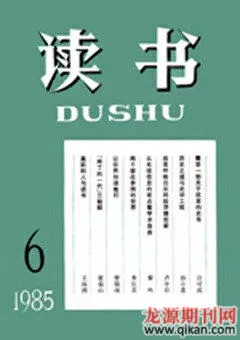布雷斯林《從現(xiàn)代到當(dāng)代》
徐海昕
對(duì)西方二、三十年代以艾略特為標(biāo)志的現(xiàn)代派詩歌,國內(nèi)外評(píng)論和介紹的文字很多。那么在現(xiàn)代派之后詩歌發(fā)展的情況如何呢?最近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伯克萊分校的文學(xué)教授詹姆斯·布雷斯林出版了《從現(xiàn)代到當(dāng)代: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間的美國詩歌》一書,是系統(tǒng)研究美國當(dāng)代詩歌為數(shù)不多的著作之一。
布雷斯林在書中提出,美國詩歌的歷史是一種非連續(xù)性的發(fā)展。詩人的創(chuàng)作能量總是不斷地爆發(fā)出米,使詩歌離開原來的“錨地”,“駛?cè)胄碌姆较颉薄C绹?dāng)代詩歌從現(xiàn)代派的錨地升錨啟航的時(shí)間是五十年代末,打出的旗幟是金斯勃格的《嚎叫》(一九五六),羅勃特·洛厄爾的《生活研究》(一九五九)和唐納德·艾倫的選集《美國新詩》(一九六○)。這次歷史性啟航的前前后后就是作者要研究的主題。
這本書的敘述方法首先是綜述由現(xiàn)代派到當(dāng)代詩歌的轉(zhuǎn)變,接下來分別論述五位詩人,這些詩人代表了六十年代開創(chuàng)美國當(dāng)代詩歌局面的五大詩派,他們是“垮掉派”詩人艾倫·金斯勃格,“自白派”詩人羅勃特·洛厄爾,“黑山派”詩人丹尼斯·萊弗托夫,“深意象派”詩人詹姆斯·賴特和“紐約派”詩人弗蘭克·奧哈拉。最后作者表述了對(duì)八十年代詩歌與批評(píng)狀況的看法。
五十年代末,在美國開創(chuàng)當(dāng)代詩歌局面的已經(jīng)是二十世紀(jì)的第三代詩人了。在他們之前第一代詩人是二十年代的現(xiàn)代派,第二代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新批評(píng)”大旗下的詩人。五十年代末時(shí)這三代人都在,美國的詩壇真可謂是三代同堂了。這個(gè)大家里,爺爺們顯夠威風(fēng),父輩的人被管教得唯唯喏喏,結(jié)果還是作孫子的起來造了反。
當(dāng)然,第一代詩人和第二代詩人之間也并不是相安無事的。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這一段時(shí)間不象人們常說的那樣,是詩歌發(fā)展上一段極平靜的時(shí)期,這時(shí)的詩人和現(xiàn)代派的詩人處在一種非常不合諧的關(guān)系中。現(xiàn)代派已經(jīng)造就了一代詩風(fēng)和一代讀者,繼起的詩人要想拋開這些去另辟蹊徑,就會(huì)受到冷遇。不少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詩人,諸如比肖普、庫尼茲等,就有過一段這樣的命運(yùn)。當(dāng)時(shí)的情況正如后來的批評(píng)家所指出的那樣,“原來帶有革命性的現(xiàn)代主義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變成一種僵死、跋扈、帶壓抑性的東西了。”(W.D.斯諾德格拉斯語)
其實(shí),現(xiàn)代派在二十年代以后也并非一直走運(yùn)。例如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艾略特一味強(qiáng)調(diào)詩歌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且又皈依宗教,顯得和沖突四起的社會(huì)很不合拍。那時(shí)在美國有影響的是英國詩人奧登。有位叫夏皮羅的美國詩人在一九四五年時(shí)曾這么寫道:“那個(gè)在我們的修辭上留下印跡/十載統(tǒng)治詩歌的人/在倫敦、悉尼和紐約都叫奧登。”
使現(xiàn)代派從不景氣的境地中解脫出來又交上紅運(yùn)的是“新批評(píng)”在美國的發(fā)展。“新批評(píng)”家以嘲諷的力量做為詩的價(jià)值,以詮釋做為詩的方法,五十年代時(shí)在詩歌批評(píng)中取得統(tǒng)治地位,二十年代現(xiàn)代派的詩威也因此復(fù)興起來。那時(shí),美國當(dāng)代詩歌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洛厄爾已經(jīng)開始成名了。他的詩集《威利老爺?shù)某潜ぁ帆@得了普利策書獎(jiǎng)。他自己說,“我是什么樣的詩人主要取決于我是在‘新批評(píng)的全盛期里成長,有艾略特對(duì)文字神奇般的細(xì)微安排做批評(píng)的樣子。”洛厄爾和威爾伯、梅里爾、里奇等不少詩人,構(gòu)成了第二代詩人中的“新形式主義者”(newformalist)。他們?cè)噲D把現(xiàn)代派對(duì)詩歌形式的試驗(yàn)和更早些時(shí)候的詩歌形式諧調(diào)起來,表面上繼承了二十年代的傳統(tǒng),實(shí)際上又在發(fā)掘更早的詩歌傳統(tǒng)和形式的時(shí)候,把現(xiàn)代派悄悄地?cái)D到了一邊。現(xiàn)代派成了一件漂亮的衣裳。他們這樣做倒很象艾略特當(dāng)年跳過自己的直接前輩,向十七世紀(jì)的玄學(xué)詩人多恩求助。
“新形式主義者”總想把現(xiàn)實(shí)生活納入一個(gè)框子。威爾伯曾以畫為比,說“在塞尚的名畫里,人們總能看到現(xiàn)實(shí)中雜亂直接的實(shí)體,同時(shí)也能感到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頭腦把這些東西安排起來。”可是通觀這些詩人的詩,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并沒有什么力量把生活經(jīng)驗(yàn)中的雜亂理出一個(gè)頭緒來,而只是把它們嵌進(jìn)了形式的框子。為此,詩人的真實(shí)情感也難免被框住。正如里奇自己后來說的,“那些年里本來可以光著手干的事情,卻都要戴上石棉手套”。生活和藝術(shù)形式脫節(jié)了。奧登是明眼人,他說美國詩歌在五十年代變成了一種“封閉的系統(tǒng)”。
第二代詩人中有不少人逐步看出現(xiàn)代派和“新批評(píng)”的毛病。例如洛厄爾就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他說:“和我同輩的詩人,還有特別是更年輕的詩人,已經(jīng)太會(huì)運(yùn)用這些(固定的)形式了。他們用恐怕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一種極復(fù)雜的技巧,寫出非常富有音樂性而且很難懂的詩。可是,這樣的寫作總感和文化脫離,是一種太專門的東西,不能對(duì)付多少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并且已經(jīng)流于一種純粹的技藝。因此,必須要有某種回到生活的突破。”這里關(guān)鍵的話是“回到生活的突破”。洛厄爾本人從寫《威利老爺?shù)某潜ぁ?一九四六)到《生活研究》(一九五九),花了十多年的時(shí)間才完成了這個(gè)突破。
使詩歌突破形式的束縛而回到生活,恐怕是第三代詩人的共同特點(diǎn)。這從廣為流行的“后現(xiàn)代主義”(Post-modernism)這個(gè)術(shù)語的使用和人們對(duì)此的闡述中可見一斑。“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gè)術(shù)語既指一段時(shí)間,又帶有很強(qiáng)的評(píng)價(jià)性。于是人們對(duì)“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做了許多區(qū)分。例如斯科內(nèi)多認(rèn)為現(xiàn)代派曾一度被說成是不講形式,現(xiàn)在卻顯出它是把固定(形式)和流動(dòng)(生活)用一種相互矛盾的關(guān)系捆到一起,創(chuàng)造了新形式;而當(dāng)代藝術(shù)卻是要打破生活與藝術(shù)的區(qū)別,造就一種“動(dòng)力運(yùn)動(dòng)的酒神式的流動(dòng)”。哈桑在他的《后現(xiàn)代主義:實(shí)用書目》中也說:現(xiàn)代主義由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中心無法保持,便創(chuàng)造出自己權(quán)威的形式;后現(xiàn)代主義卻趨于無政府,更深入地與崩潰的事物建立起復(fù)雜的聯(lián)系。
本書的作者認(rèn)為“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gè)術(shù)語太籠統(tǒng),故意把它撇開不用,而將注意力集中在當(dāng)代詩歌的發(fā)源時(shí)期的五大詩派上,認(rèn)為他們樹立起來的權(quán)威足足影響了以后二十年詩歌的發(fā)展。他從不同的詩派中選出有代表性的詩人,既研究他們的獨(dú)特性,又研究他們的共同關(guān)注。在不同詩人的詩中他看到:金斯勃格《嚎叫》中對(duì)城市生活種種煎熬分類式的寫照;洛厄爾《生活研究》中自傳式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奧哈拉午餐詩中每日生活的細(xì)節(jié);萊弗托夫抒情詩中的家庭瑣事;賴特對(duì)城市和自然景色入微的描寫——而所有這些都說明詩歌開始敏銳地觀察現(xiàn)實(shí)存在,有明確的實(shí)在性,完全不同于象征主義超越的總體想象,也不同于“新批評(píng)”和形式主義詩人更加隱蔽而又超越的想象。
這些詩人摒棄了上一代詩人所用的形式,并不是要淹沒于生活的“流”。他們實(shí)在是在找尋一種不違反即時(shí)性而又能把形式和流動(dòng)聯(lián)接起來的辦法。引人注目的是形式被看成是一個(gè)展開的認(rèn)識(shí)過程。一位叫羅勃特·鄧肯的詩人說:“當(dāng)我寫作時(shí),作品對(duì)我講話。”前面已經(jīng)提到過的里奇也說:“我發(fā)覺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能再用掌握的材料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來寫詩。寫詩本身就產(chǎn)生新的感受和認(rèn)識(shí)……我現(xiàn)在的詩本身就是經(jīng)歷,而不是關(guān)于經(jīng)歷的。”
六十年代初造反的那些詩人,到了八十年代都有了一些名望和地位,如今在美國正是這一代詩人在主持著一個(gè)有生活氣息卻較少有急劇變革跡象的詩壇。正在出現(xiàn)的第四代詩人(一九四○年以后出生,一九六○年左右開始寫作的詩人)還沒有要脫離前一代詩人的跡象。偶然出現(xiàn)一些諸如“語言詩人”(Ianguagepoets)之類的派別,也沒有多大影響。出現(xiàn)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yàn)榈谌娙藳]有形成一個(gè)中心人物(如第一代的艾略特)或一個(gè)領(lǐng)導(dǎo)派別(如第二代的“新批評(píng)”)。現(xiàn)在的批評(píng)界雖有勢頭很大的“分析主義”(deconstruction),卻也不能壓倒其它的派別。多中心的分散局面倒使得年青詩人無從造反了。這個(gè)局面看來還要延續(xù)一段時(shí)間。
(JamesBreslin,F(xiàn)romModerntoContemporary:AmericanPoetry,1945-1965,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