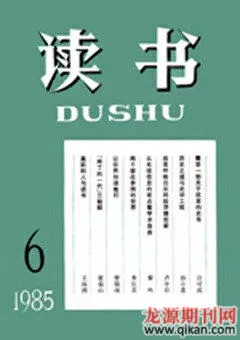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硅谷熱》
黃方毅 范新宇
距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市西南約五十公里處,有一個曾以盛產水果聞名的秀麗的山間谷地。靠了現代電子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片不大的谷地竟集中了八千多家高技術公司,一躍而成為國際聞名的電子工業中心,信息社會的典型,這就是著名的“硅谷”。
一九八四年春季,美國紐約基礎書籍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埃弗雷特·M·羅杰斯與朱迪恩·K·拉森合著的《硅谷熱》一書,對硅谷這一高技術產業基地進行了全面描述和系統分析,并對其未來發展作了展望。為供讀者參考,這里選刊了該書部分章節的內容。它描繪了由工程技術人員、風險資本家和企業家形成的信息交流網絡,及其對促進硅谷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還反映出美國高技術產業方面的劇烈競爭,以及它給硅谷人的生活方式帶來的巨大影響。全書中譯本由范國鷹等人合譯,將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
信息交流是硅谷一個突出的主要特點,因為技術創新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所以它特別有賴于信息。
“硅谷”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不僅僅是微電子工業的主要中心,甚至不僅僅是那幾千家高技術公司,而且“硅谷”已成為一個網絡。一個有閱歷的半導體工程師說:“我熟悉某人,他們熟悉某人,然而我并不認識他們所認識的所有的人。”這一網絡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每一個參加者都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都知道我們認識硅谷中很多人。這主要歸因于工作的高度流動性。在硅谷,諸如某家公司的信譽,某人的成功業績,某人從某公司離職,新面市的產品等消息不脛而走,傳播得極快。這種傳聞制造廠“以驚人的速度制造著這類消息。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這些公司靠得極近。從你的辦公室窗戶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其它的公司。”
一家從阿塔里計算機公司分離出來的影像游戲公司的經理比爾·格拉布,提到這一網絡時曾說“在我們售出我們的首批產品之前,我們的副經理和我就已經曉得我們這一產品百分之九十的潛在買主了。我們立即著手與這些潛在的客戶,例如西爾斯公司、J.C.查公司以及RUS玩具公司等簽訂合同,這樣,我們便持續不斷地發展起來。”
作為硅谷特點的這種緊密相連的信息網絡賦予了它能夠超過其他地區的優勢。諾蘭·布什內爾闡述這一點說:“硅谷有大量的網絡編織工作,這一點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擬的。最近,我訪問了正在倫敦從事新產品研究的一個工程師小組,他們與硅谷的一組同行們展開競爭。雙方幾乎是同時起步開展研制的,然而硅谷這批人的工作進展卻超出了他們同行六個月。我們的這批人中有一個工程師,他有一個朋友在因特爾公司工作,這個人從公司里竊取了他們正需要的一種新的集成電路芯片的幾個樣品。這種電芯片很快就拿到市場出售,但是它還未列入產品目錄。因特爾公司也頗有益處,因為這樣一來,馬上就贏得了一些買主。這六個月時間說明,我們擁有一種巨大的優勢,這就是硅谷總是著著領先的原因所在。”確實如此,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分析,美國半導體工業的獨一無二的力量,正是來源于它的公司之間能夠迅速地相互仿制出不斷創新的集成電路芯片。
就如同沙山路3,000是風險資本的中心一樣,在卡米諾—瑞爾路的佩奇米爾路口,坐落著帕洛阿爾托廣場大樓,這里是為高技術服務的法律事務所中心。據最近統計,帕洛阿爾托共有八百六十五位律師,這個數字是十年前的兩倍,是二十年前的六倍。
為高技術服務的法律業務在日趨繁榮。一位受雇于芬威克-斯通-戴維斯一米斯特公司的律師戈登·戴維森,常常在他工作周的每一天都要受理一個新創公司的有關事宜。戴維森對于新創公司來說,起了關鍵的編織的作用,他協助企業家們去寫成他們的企業計劃書,并為他們尋求風險資本。他具有堪稱楷模的學歷,有資格擔當這種媒人的角色,他除了有法律方面的學位之外,還是個電子工程學理學士和計算機科學碩士。這種學識有助于他為那些新分離出來的微電子公司判斷一個重大問題——這位創業者是否從過去的雇主那里拿走了交易秘密。
為了獲得信息,就必須給人家信息。在微電子行業中,由技術信息交流過程的性質所決定,需要在其參加者們之間有一種高度的互惠性。
一位年輕的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中心實驗室工作的博士提供了這種面對面交流的一個例子。他在一次專業會議上向與會的半導體工程師們介紹了他本人的研究與發展項目。他的公司同事中有些人擔心他泄漏“秘密”,然而,這位博士曉得他能夠走多遠。他說:“我完全曉得界限應當劃在哪里,我危險地向它逼近,而且在公開討論我的學術成果時,我的一些競爭者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本身,就對我顯示出了他們已經掌握了多少,而這對我們的公司來說,就是有價值的信息。”
硅谷技術信息網絡的重要人物都在鉆研如何駕馭他們所具有的知識。一家半導體公司的工程師卡爾·哈林頓對我們講起:“沒有人會和盤托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這就象是在玩紙牌,如果你要扣下點什么,它就能向你提供某些就業保險。沒有人會告訴你所有的成功訣竅和細微的奧妙所在。你留一手,以便今后能再交換。我可以向有朝一日我或許會到那里去工作的某家公司提供有關設備的信息。但是,我決不能夠提供會危及當前我所在公司的情報。”
數據查詢公司是微電子行業市場研究的中心,它每年秋天為半導體公司舉行一次會議。到會的人們是公司的行政首腦和經理。數據查詢公司利用一臺電子計算機的程序來編排進餐和參加討論會的席位,使得鄰座都能彼此相識,并且避免發生令人不快的組合。舉例來說:一個顧客被安排在一個與賣主相鄰的位子;兩個日本人則不會被安排坐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希望與美國人談話;然而,正在直接進行競爭的公司的代表們是不會被安排坐在一起的。
德國的一家電子公司洛倫茨標準電氣公司的技術中心負責人漢斯、賴納爾,談到他第一次跟硅谷的信息交流網絡打交道時的驚異之狀說:“我被公司派去訪問我們的代理人,為了就一個他們已經著手解決的整體技術問題求得幫助。我們的人已經掌握了部分的答案,而且他也曉得從哪里去得到答案的其余部分。工作之余,他把我帶到硅谷的一個酒吧,隨即,他招來了坐在鄰近一些桌子的工程師們,他們都認識他。這些人非常樂意告訴我們應當如何去做。到晚上九點鐘,我便有了解決我們公司問題的方法。第二天上午,我飛回了斯圖加特。在加利福尼亞州,人們是如此自在地合作,我確實對此驚異不已。”
在一家新公司的創立過程中,私人之間的關系可能也是重要的。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生命線通訊公司,人們稱它是從一堆馬糞中拾到的。
在洛斯阿爾托斯山區——硅谷技術專家新富翁們的聚居地。艾爾·霍利并沒有打算與他的鄰居談論業務方面的問題。然而有一天,霍利的妻子吉妮特走過去找這位卷發的得克薩斯人,目的是為她家的花園要一些馬糞。碰巧這個得克薩斯人擁有一家計算機公司。吉妮特·霍利回家后要自己的丈夫去會會這位鄰居,霍利此刻回憶說:“那一天是幸運的一幕,毫無疑問是那次會面導致我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個鄰居叫詹姆斯·特雷比格,是坦德姆計算機公司的創建人。那個星期六的下午他與艾爾·霍利邊談邊飲,喝了幾瓶啤酒,并且,后來霍利又邀請特雷比格到他的汽車房,去觀賞他的一個原型衛星接收機,這是霍利用一些薄金屬板制作的。幾天后,特雷比格就帶來了一批他的管理人員,以便決定坦德姆公司是否有可能使用這種衛星接收機將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計算機連接起來。特雷比格還向霍利介紹了他的風險資本家:克萊納、帕金斯、考爾菲爾德、拜爾斯。不久,亨利就有了二四○○萬美元的資金作后盾。
兩年以后,艾爾霍利的生命線通訊公司一些衛星系統的年銷售額就達到五百萬美元。而他的第一位客戶就是特雷比格的坦德姆公司。或許,人們可以說生命線公司是從一堆馬糞之中拾到的。
在硅谷,餐館不只是飲食進餐的場所,它們還是洽談生意和交流信息的好地方。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組織,在個人與公司間形成非正式網絡的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在這類聚會場所中,歷史最老而又最有名氣的是沃爾克的車輪酒吧兼餐館,它坐落在
這些酒吧和餐館提供了一個中立的場所,昔日曾一度共事,如今受雇于互相競爭的不同公司的那些老朋友們,在這里聚集一堂。他們一邊飲下一杯加州生產的白葡萄酒,一邊閑談,不是談他們的家庭、體育運動或業余愛好,而是談論著存儲器、觸發電路、計算機。
在胡椒磨坊餐館用早餐如今是硅谷的一種傳統,對于那些從事半導體推銷的人們來講尤其是這樣。因特爾公司的一位銷售經理說:“早上八點鐘我去胡椒磨坊餐館,我在那里總是能遇見我認識的人。總而言之,這就是硅谷。所有我的客戶們,所有我的對手們,大約五百來人,經常在這里吃早餐。實際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誰人坐在我相鄰的小間里。從偷聽鄰座的談話中,我可以得到許多信息。所有的批發商都在那里,他們就是我與之共事的一些伙伴。或許我的一個顧客同我的一個競爭對手正坐在那里,但我還是走過去,同他們握握手。然后我說,‘噢,順便說一句,為什么明天早上我們不可以一道進餐呢?人們在此訂約會,胡椒磨坊餐館就是這樣一個宏大的交際場合。”
在硅谷,對于每一個不同的微電子行業來說,總有那么一個特殊的組織,在這一行業的個人和公司之間形成非正式網絡的過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在微型計算機行業中,與費爾柴爾德公司與阿塔里公司舊部網絡相對應的是自制計算機俱樂部,這個獨一無二的組織首次會議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召開,地點是門羅帕克市一位微型計算機迷戈登·弗倫奇的汽車房內。在這個俱樂部成員們的推動之下,先后有二十二個微型計算機公司誕生了,其中的二十個公司運營至今,這些公司里有許多至今或一度是微型計算機行業里的一流公司,象阿普爾公司、克羅門科公司、北極星公司等。自制計算機俱樂部的計算機小伙子們有的在開展計算機軟件方面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其他有的人,如保羅·特雷爾和博伊德·威爾遜,則開辦了計算機零售商店;還有一些人象吉姆·沃倫,開辟了計算機展銷會。
在自制計算機俱樂部成立之初,它大約有五百名計算機愛好者作為它的固定成員,這些人大多是年輕人,而且大都是小伙子。所以起這樣一個名字,是因為它的一些創造人是用配套元件自己組裝計算機的。這個俱樂部的宗旨,是為了促進計算機愛好者們之間的信息交流。它的成員不交會費,沒什么儀式,也沒有個章程。
俱樂部開會的典型方式是,開初總有一個“制定議程階段”,那些有通知要發布,有東西要交易、出售或讓予的人站起來,做一番自我介紹。然后,會議便轉入“隨機接觸階段”,讓那些興趣相同的成員,例如因特爾公司“8080”型微處理機的愛好者們,分別組成一個個小組進行暢談。人們利用這種場合交換計算機的程序和線路設計,有的信息幾年之后將變成公司秘密。
自制計算機俱樂部的發起人是弗雷德,他和他的朋友們曾在硅谷的各處張貼布告,宣稱要“交換信息、交流思想、交談業務、協助項目設計等”。出乎他們所料,第一次會議就來了數百人,于是,不久他們就將會址從戈登·弗蘭克的汽車房遷到斯坦福大學的一個禮堂。當自制計算機俱樂部成員中的一些人開始籌辦一個個微型計算機公司時,在俱樂部組織的會議上,自由交流信息的活動便開始終止了。但當初的計算機小伙子中有些人至今仍然來參加自制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戈登·弗蘭克現在是一家名叫“廣場一號”的微型計算機咨詢公司的老板,他認為,自制計算機俱樂部仍然是微型計算機專家們非正式的信息網絡的中心。不管是否如此,該俱樂部確確實實締造了一個網絡。
硅谷的最為引人矚目的特點之一,就是員工的流動率之高到了令人驚異的程度。
高級微型儀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曾經說過:“在這里,所有的那些想調換工作的人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在清晨開車上班時,在那條原來也要路過的相同的馬路上,把車拐進另一車道就行了。”
保羅·赫斯是硅谷一家公司的經理,他說:“我做了許多雇傭和招聘方面的工作,因此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我閱讀過一百萬份履歷表。有一個家伙,居然在二十四個月中先后在十五家公司里干過活。這恐怕有點太過分了。然而,我也不會討厭那些在一家公司干上兩年后又到其他公司的人。”
員工的高度流動究竟是福還是禍,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看法。對受雇的一方來說,確保他能夠離開一家公司而受聘于使他增加薪水的另一家公司無異于提供了一種保險。每一次的工作調換意味著薪水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五,而且或許還能夠晉升職位。而公司當然會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跳槽”問題,失去有經驗的雇員是一個主要的問題,雇員的經常流動對公司內部的運營的連續性造成了困難。當某一設計項目的關鍵性工程師離去時,圍繞這個項目的大多數設計思想也隨之而去了。
工作的高流動率也許是受到公司本身的鼓勵,因為老板們總是鼓勵雇員去追求更好的職位。對于大多數人來講,鼓勵他們“跳槽”的普遍動機是金錢。由于缺乏技術人員,付更加高的報酬有時是吸引所需人才的唯一方法。在半導體行業里,設計工程師尤感缺乏。王安實驗室的艾伯特·貝爾·賽爾說:“職業籃球或職業壘球手的人數都要比搞集成電路設計的人多。”
“跳槽”還是沿著公司的階梯一步步向上攀登的一條道路。在硅谷,與其他地方不同,“跳槽”比呆在原來的公司能提供大得多的晉升機緣。伴隨著工作的調換,雇員能攀上一個責任更大的崗位,同時拿到更豐富的薪金。
從“跳槽”獲利的是那些尋覓人才的人,這種介紹人物色到一個工程師所得到的傭金相當于這個工程師新職位第一年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大概是六千——八千美元。
盡管經理召募公司和職業介紹所強調他們的信譽和正直,然而實際上卻并非總能夠兌現。一九八二年,在埃克林辦公室系統公司宣布關閉它的高級研究中心之后的一個小時之內,人才尋覓者們打來的電話如潮水般涌來。當被解雇的人員走到停在露天停車場上自己的汽車時,都發現一張本地一位人才尋覓者的名片,貼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由于缺少合格的和有經驗的人才,進一步增加了硅谷專業人員工作的高度流動。而使業務管理的一般方式也必須適應于短期雇傭。
在硅谷,工作高度流動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渴望從競爭中獲得技術信息。
一個工程師如果離開甲公司而到其他公司就職,他也許已經簽署過某種保密協定,保證在他離去后不泄露公司的秘密信息。然而,縱然這位雇員不能夠向乙公司的新同事們提供關于具體產品的信息,但是上述的保密協定卻并不妨礙他向他們提供圍繞這一新產品的頗有價值的信息。比如解決某個重要的微電子設計問題也許有二十種不同的方案,甲公司曾嘗試過其中的十種,但未獲得成功。關于不應采取何種方法的信息對乙公司來說可以是極其有價值的,在一個激烈競爭的行業之中以聘用一個專業研究與開發工作人員的形式來購買這樣的情報,是一種繞過其他公司的保密規定的戰略,而且,這樣做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對于甲公司來說,也有一項反戰略可以采用。這位雇員的離去,并不妨礙他在為與甲公司競爭的乙公司工作六個月或一年以后重新回到甲公司,一位在乙公司身居要職的工程師,在他的舊雇主看來,是更有價值了。他重新受甲公司雇用,很大成分是為了能夠了解對手的情況。實際上甲公司“批準”這位專業技術人員離職,可能就是為了以后重新雇用他。所以,在硅谷,“跳槽”實際上是一種拜占庭式的戰略與反戰略的把戲,換取技術情報是這些戰略的主要目的之一。
一個公司可以采取任何降低關鍵雇員去職的方法,起到減少公司秘密泄漏的作用。在公司之間,人員的流動率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工程師的流動率大約是百分之六,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大約只有百分之四,然而,許多其他硅谷公司卻達到百分之三十或者還更高。
對于那些流動率低的公司,唐·霍夫勒說:“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人是非常忠誠本公司的,從那里挖人很難。但是只是某種類型的人才喜歡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因為那是一種具有固定結構的存在方式。如果你是一個外向性格并且具有創業精神的人,呆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會感覺郁悶。我所認識的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多數人都想終生在這個公司里工作,沒有離開的念頭”。自然,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也因為保持如此之低的工作流動率而付出了代價,發給雇員的豐厚慷慨的薪俸占了公司利潤相當可觀的比重。這個公司的官員們早就決定,他們的公司不希望象典型的硅谷公司那樣終日忙于解聘與招雇工作。這種終生雇傭制所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報償,就是幾乎沒有什么公司的秘密泄露出去。
在高級技術行業中長期雇用是防止信息交流的一種方法。它的重要性為日本公司所證明。在日本,從事微電子工作的人員都享有終生雇用的待遇。因此,在日本,保密協定是不存在的,因為,工作流動率很低,沒有必要在雇主和雇員之間簽定這樣的協定。
限制工作流動及相應的技術信息方面的損失的另一種方法,是把從事研究與發展工作的關鍵工程技術人員置于被隔離的環境中。這可能意味著把他們安置在硅谷以外的什么地方。因特爾公司為了確保一項研制秘密,特地把設計組安置在俄勒岡波特蘭大的郊區某地。這樣隔離有效地防止了該項技術秘密過早地通過硅谷的小道消息網絡傳播開來。然而堪稱不幸,該公司的這種隔離戰略導致了事與愿違的結果。十八名在波特蘭大工廠工作的因特爾公司雇員辭職了,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新的公司。這個決裂行為對該公司的打擊是沉重的:這些身居要職的背叛者中有三位所負責的工作與因特爾公司全部銷售額的百分之二十和全部研究與發展預算中的百分之二十有關。
在硅谷,大多數發明并不去申請專利,以避免將他們的發明泄露給競爭對手。但也有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專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樹立自己的公司是技術領導人的形象。
一份專利在理論上說,是確保了對一種技術革新的壟斷,然而在硅谷,這樣看并不完全準確。在美國,專利是由聯邦政府頒布的給予發明者的一種權利,這種權利排除了任何其他人十七年內在美國境內制造或銷售該項發明。美國專利局一般需要兩年至五年的時間來審查專利申請書,以便確定該項發明是否具有新穎性和實用性。
在硅谷,大多數發明并不去申請專利,因為這樣做的話,就必須在專利批準之時將他們的發明泄露給競爭對手們。這就是為什么托馬斯·愛迪生將專利斥為“偷竊許可證”的原因所在。硅谷的經理們擔心,專利的泄露會鼓勵競爭者們去仿制他們的發明,也許還給予改頭換面,使得利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發明相當困難,或根本辦不到。專利權受侵犯的訴訟,既費錢又費時。對手也許還會繞過某一項專利來進行“發明”。往往可以采取各種方法以便搞成一個有效的對應產品。在一個高技術產業中,變化十分迅速,專利作為確保技術信息所有權的一種法律手段,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盡管如此,硅谷的一些企業仍擁有自己的專利。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出于公共關系方面的考慮,為了樹立自己的公司是技術領導人的形象。專利的這一作用,雖然不大可能對該行業的局內人產生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卻能給技術知識較少的投資者們以好感。在公司來訪者的接待室里,鑲上框子的專利一個個掛在墻上,給公司增添了誘人的裝飾。阿塔里公司的霍夫,一個人拿到了十四項專利,他說:“在半導體行業里,專利的實際用處微乎其微。發明層出不窮,你肯定會侵犯別人的專利權。如果這一行業里的每個人都認定要死守他們自己的專利,那么,唯一能掙錢的人就只有律師了。所以大家不這樣做。更為慣常的做法是,達成一項我不觸犯你,你也不觸犯我的協定。這種協定簽定之后,如果我卷宗里的專利書比你的多,那么你可能應付給我一小筆費用。”
代替取得專利權的商業秘密戰略,在完成技術開發之后和投入商業性生產之前,保守技術創新的秘密。基本上,公司說什么是商業秘密,什么就是商業秘密。與擁有創新的公司進行競爭的公司,可以通過所謂反求工程這種常用的方法來掌握對方的商業秘密,即購買那種產品,并且把它拆開來,研究它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有一種用以保護商業秘密免遭反求工程侵害的反戰略,即所謂“裝壇”:就是用一種辦法將創新產品包裹起來,使人很難去掉包裝而又不損壞創新的內容。在硅谷,一些半導體公司把它們自己的新產品“裝壇”,而對競爭者們的新的集成電路芯片卻使用反求工程。這兩種方法中任何一種從長期角度看都不是很成功。但是一個半導體公司,可以因此獲得幾周或數月的短期優勢。在一個競爭極為激烈,革新持續不斷的行業中,即使是短期優勢也可能是很重要的,而且反求工程的費用可能是值得的。
一九八二年中,兩家巨大的日本計算機公司,日立公司和三菱公司以及它們的十八位雇員,受控策劃竊取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秘密,其中包括該公司最新和最強大的計算機“IBM3081K”的設計工作手冊,聯邦調查局曾在圣克拉拉采取一種所謂“喂飼”行動,建立了一個假的咨詢公司——格林瑪公司,向日立和三菱提供了商業機器公司的一些秘密。一九八二年六月,當這兩家日本公司的干部到格林瑪公司來取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機密情報和計算機磁帶時,被當場抓獲。
不論人們如何評議聯邦調查局的“喂飼”行為,它說明,在硅谷,攫取工業情報活動的合法與非法的界限是很不明確的。日本人說,“這是人人皆為之事”,這是對的。國際商業機械公司每年都要花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巨款來保護公司的秘密,除非是感到了一種非常現實的威脅,否則,是沒有誰肯花費這么多錢以求免受工業間諜活動之害的。
硅谷的高技術產業有一種與傳統工業不同的緊迫感,因而硅谷人在以競賽的速度工作和生活,節奏相當快,家庭生活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傷害。
與硅谷任何一個人隨便聊聊天,就可以聽到加班加點的事兒。一位在硅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師弗蘭克·維勒介紹說:“我常常周末不休息,連續工作很長時間,最長一次連續干了五十九天,每天至少八小時,最多達十七小時。”硅谷人為什么要這樣做?一句話——競爭所迫。
硅谷的高技術產業有一種與傳統工業不同的緊迫感。能否提前推出新產品,打敗你的競爭對手,是決定生死存亡的問題。誰先沖向市場,誰就生存下來,因而硅谷人在以競賽速度工作和生活,節奏相當快。尼克·拉森形象地描繪說:“如果機器每分鐘是一百轉,我們每天早晨起來就把它定在一百二十轉。”然而,激烈地競爭,同行們的壓力,率先推出新產品的緊迫,給硅谷人帶來的是長時間的“突擊”。在這長時間的突擊中,做一名硅谷人不易,當一名硅谷的公司經理更難。
國民半導體公司副經理布蘭特,患了一種罕見的血液病,需二十四小時不停地輸液。這種病要住院治療,但他拒絕住院,他帶著輸液瓶出席會議,并把汽車作了某些改裝,使他可以邊開車邊輸液。他說:“如果我住六個星期院,我就要落伍了。”勝利技術公司的經理,憶述了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在過去的兩年里,我把三名副經理送進了醫院,四名高級職員中有三人因離婚而失去了家庭。緊張和忙碌使人陷入了一種夢境,當你醒來的時候,孩子們已長大了二、三歲。哎!如果當一年美國總統減壽十年的話,當一年公司經理會減壽五年。”
硅谷人已經習慣了緊緊張張地工作和快節奏的生活,如果真的閑下來,他們反而不暢快。西格奈蒂克斯公司的一位推銷代理人朱迪·惠勒說:“在周末,我沒有計劃做很多事,這使我煩得要死,我已經習慣了快節奏地生活,我喜歡快節奏,當節奏慢下來時,我真感到無法忍受。”
但是,快節奏給硅谷人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很大影響,家庭生活也為此受到了傷害,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家庭團聚的時間,工程師肯尼思介紹說:“當我在公司忙碌時,我妻子常常帶上孩子們和晚飯,開車到我辦公室來,把飯用微波爐熱一熱,這就是我們在一起吃晚飯的唯一辦法。”
有些觀察家這樣認為:硅谷的企業家是典型的高功厚利的追求者。他們為此付出了很高的個人生活代價。這些“工作狂”漠視與妻子、孩子、父母和朋友之間的人情關系。康妮的丈夫與前妻有兩個孩子,他與前妻離婚時女兒五歲,兒子才三歲,他們的離異,主要是因為他忘“她”的工作。
今日硅谷,離婚人數超過了結婚的人數。離婚率比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的離婚率還高,而加州的離婚率又比美國平均離婚率高20%。人們發現,在飛速發展著的硅谷,跟上快速工作的節奏,意味著沒有時間與親人相處。一位離了婚的工程師說:“在這種環境里,你要維持住婚姻,那得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因為工作牽扯你的精力太多了。”對那些以取得成功為動機的工程師來說,事業可以擠掉家庭,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硅谷人的婚姻,經常呈現出兩個階段的模式。開始,夫妻二人為達到共同的目標奮斗著,但是,為這種奮斗所付出的高昂代價變得越來越明顯:工作時間太長,夫妻團聚太少,生活節奏太快。時間就這樣年復一年的流逝,他們感到硅谷對生活的要求太苛刻,也許是妻子不再甘心在孤獨中度過自己的美好時光,也許是丈夫不再愿意受到家庭的拖累,于是他們分手了。
人們是否擔心,在硅谷容忍的氣氛中,男女私情會大泛濫。事實上,大多數刻意追求事業成功的人都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工作上,而不是花在異性身上。
一位工程師深有體會地說:“要干的工作太多了,使你根本沒時間花兩個小時與一位美人吃頓午飯,這里有的是漂亮的女人和各種機會,但工作起來感興趣的只是工作,而不是廝混。”
硅谷還有許許多多的“計算機怪人”,他們迷上了計算機,在計算機終端設備旁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他們酷愛計算機超過了酒吧和女人。一位妻子抱怨說:“這些迷上計算機的怪人,簡直是與計算機結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