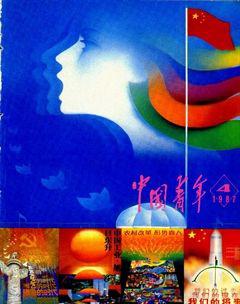讀后信筆
陳建功
讀了《故里人物三紀》,很有點兒興奮。新的表現手法固然可喜,傳統的“著數”亦不可輕弄。作者的確沒用什么“新著兒”。不是“意識流”。不是“超現實”。沒有“荒誕”。沒有“象征”。他用的“著數”非但不時髦,甚至可以說有點兒“老掉牙”。大概可以追溯到一千四五百年前吧?不信你去翻翻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周處斬蛟。劉伶病酒。孔文舉應對。王逸少坦腹……那里面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也都是用的這一“著兒”凸現的:以極簡省的筆墨,把最傳神的細節勾勒出來,仿佛一幅幅生動的速寫。劉仁前對他的“故里人物”的刻畫,亦不外如此。
當然,作為一個步入“新星系”的文學青年,他需要為文學提供新的東西,需要用他獨特的“著數”確定他在“新星系”的獨特軌道。可是,你得承認,他寫成現在這樣已屬難得,因為他一下手便寫到了被許多初學者忽視了的,可恰恰是小說藝術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在這三篇小說里,他寫了時代的發展,世事的變遷;寫了淳厚的民風掩蓋下的欺騙;寫了被漠視、被冷落了的人生的渴望。而這些帶有作者獨特的感情色彩的對生活的把握,無一不是通過具體人物的性格、遭遇暗示出來的。這就使得讀者首先從人物的性格、命運里,受到了感染,在被藝術魅力所吸引所征服的流程中,不知不覺地被帶入作者對生活總把握的情感境界里去了。一個初寫者,懂得了小說的魅力在于人物,再深刻、再動情的對世界的總體把握,也必須通過筆下人物來表述。這不是難能可貴的嗎?
看得出來,《故里人物》的作者,是從扎扎實實的人物積累開始他的小說創作的。從他這三篇作品的總名便可見一斑。他寫“祥大少”玩牌—衣衫不整的窘態和端坐牌桌時的莊嚴;他寫“譚駝子”抓魚—“柳下取呆子”的“熱心”和“自得”;他寫“二侉子”售貨—時而”洋火”“洋油”,時而“火柴”“火油”的謙恭和隨和。一看便可知絕非閉門杜撰,而是有著對生活中人物的觀察、積累為基礎的。這種觀察人物、積累人物的能力,是當一個好的小說家的“飯碗”。
這位作者的另一點可貴之處是,他開始意識到,要寫出“味兒”來了。比如作品中那“遠距離”的敘事態度,不是確實有了一種冷雋的觀照的味兒嗎?最典型的,是《祥大少》一篇前五個自然段的起首,一律以“祥大少”三個字當主語。而《譚駝子》一篇,前五個自然段照例以“譚駝子”三字冠之。《二侉子》一篇小有變化,但第二自然段則是一連串的“二侉子”為主語的單句。我想,這都不是隨意為之的。這里面滲透著作者對一種敘事調子的追求。不過,這種敘事調子怎樣才能更加獨樹一幟,以區別于汪曾祺先生的某些小說呢?大概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