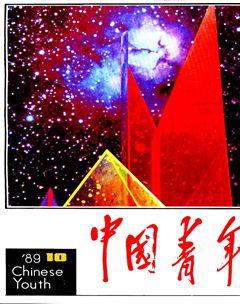童年的啟示
1989-08-24 05:50:14路遠(yuǎn)
中國青年
1989年10期
路遠(yuǎn)
雖然我沒有過多的情感體驗(yàn),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情感世界遠(yuǎn)比一般人的要豐富,我的內(nèi)心世界復(fù)雜紛繁卻從不善于表達(dá),憂郁和痛苦總是被抑制到心靈的最底層。
其實(shí)我知道我的性格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成份——謙卑和自傲,它們就是這樣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并主宰著我的一言一行,構(gòu)成了我命運(yùn)的獨(dú)特行程。我深知這一切完全來自于我的童年和少年——一種對(duì)痛苦的獨(dú)特感受以及大自然的豐厚饋贈(zèng)。
似乎是一個(gè)多雨的秋天,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里。實(shí)際上那是一鎰決定我們家庭命運(yùn)的大遷徙。那年我大約4歲或者5歲。我找到一根木棍,在鍋爐里將它燃著。我舉著燃著的木棍在院子里跑來跑去,不知什么時(shí)候?qū)⑸砩系男旅抟聼艘粋€(gè)洞。我正怕得要死,忽聽到繼父的呼喚。那次旅行是繼父將我、姐姐和母親接到他那兒去——草原上的一個(gè)水庫工地。在陌生的繼父面前我肯定嚇壞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并沒有受到訓(xùn)斥,繼父取出一包玉米面窩頭的碎渣子讓我吃。我無法形容我吃得多么香甜,那種咀嚼的吞咽的快感如此頑強(qiáng)地銘刻在我的腦海里,是夠我回味一輩子。
我的朋友說他對(duì)痛苦這個(gè)字眼;我恰恰相反,對(duì)痛苦及為敏感,外界任何微小的刺激都足以讓我的心尖震顫。我們?cè)谝粋€(gè)極為荒涼的水庫邊上安了家。我深深記信了那里陡峭的山巒、淙淙的河水、草灘上的小野花和那些可吃的野果兒—橄欖形的“地瓜”和野菊似的“酸塔”。……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