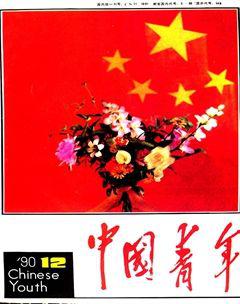不拘一格降人才
佘未人
1980年,在中國的教育史上也許值得重重提一筆。就在這一年,北京市率先開創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這是一個創造,盡管充滿了苦澀。
噩夢過去,百廢待興。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正張開雙臂,呼喚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奇缺,10年動亂中積累的考生成百萬計,無法都進入高校。
從中南海的決策者到每一個被“文革”耽誤的青年,都在從不同角度思考著同一個問題:完全按照常規辦高等教育顯然是不行了,怎么辦?
辦法總是有的,只要決策者得到人民的擁護。終于,1980年9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做出了《關于建立高等教育自學考核制度的決定》,在《北京日報》上全文刊登。
決策既出,青年拊掌。于是,成千上萬的求知者,繞過大學校園,另辟蹊徑,向知識的高峰進軍。
追回青春
只有4名工作人員的北京市自學考試辦公室掛牌辦公了。盡管他們對工作量做了充分估計,報名人數還是超出了預料。短短幾天內,6000多人報了60個專業!
來報名的都是什么人?讓我們結識幾位吧。
單明樟是一個郵遞員,曾在內蒙兵團插過5年隊。他渴望自己擁有豐富的心靈,總是利用投遞之前的空隙,讀讀就要送走的報刊。他的領導說,算了,送你的信吧。你學了又怎么樣?老“右”們不都是些有學問的人嗎?他笑了,他不贊成這種膽怯的人生態度,他不相信“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還會重來。
魏志勇這個小伙子,連初中都沒讀完。后來,他當了兵,當了文工團員,又轉業干電工。當他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震醒時,10年已經荒廢了。現在,他加入了自學者的行列。為了搶時間讀書,他不知放棄了多少假日。
盧兵曾就讀于北師大女附中,是一位優等生。她也因為那場浩劫失去了進大學的機會。1970年,她在北大荒意外地得到一本《英語九百句》,從此感到有了一絲精神的慰藉。她白天干活,晚上坐在炕沿輕聲朗讀,幻想著她置身在大學的課堂里。
走進自學考試辦公室的,正是這些渴求知識而又被耽誤的一代。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給了他們一個補課的機遇,他們怎么能不格外珍重?
莊嚴神圣的“國家級”考試
北京建立了一個由教育、計劃、財政、勞動人事部門負責人以及校考試委員、專業考試委員、課程考試委員共300多人組成的考試委員會。專家學者們來自北京的16所高等院校,可謂人才濟濟。
考試委員會主任白介夫說:“我們這個委員會逢會必講考試的質量。質量如果差勁,牌子就砸了。質量如果下來了,我就辭職。”
考試委員、著名英語教授許國璋是自學考試的熱忱支持者。他用自己的一部分稿費設立了英語專科考試的獎學金,獎給每年考試的前2名。他每年都要親自審查試題,一個標點也不放過。他說:“自學考試是新生事物,官僚主義比較少。我認為,英語專科的考試比‘托福扎實。世界上每年有幾十萬人考‘托福,美國不可能花那么多閱卷費,所以只能出選擇題,由計算機閱卷。我不知道‘托福的合格率,我們自學考試的合格率大概是20%。這20%的人,超過了大學本科二年級的中等水平。”
自學考試的命題,要求內容全面,重點突出。命題教授及工作人員實行嚴格的“入圍”制度,出題期間要“關禁閉”,直到課程開考后半小時,才能“恢復自由”。
清華大學教授李歐和何品,都有50多年的教齡了。他們為高等數學課一次命題100多道,讓青年教師清早三四點鐘就起來做。最后挑選出10多道試題,他們又親自動手,再做一遍。人大教授趙樹嫄,有時一天要做200多道題,累得頭昏眼花。
從1985年起,北京自學考試委員會建立了題庫。題庫中有210門課程的200000多道套題,就是押題老手,也只能是束手無策。
閱卷是由主考學校進行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和教師們一齊上陣,一份試卷的評分,前前后后要經過12遍核對。每份試卷上必須有7項簽名,一項也不能少。雖然考試辦公室規定不查分,但每次考試后都有要求查分的考生來信。考試辦公室曾將來信集中起來,拿著標準答案一份份核對,復查了2000多份試卷,無一差錯。
經過12道審核,7道簽名的試卷,對每一位考生都是一律平等的。
考生魏志勇說:“我們140多人考古代文學史,只有14人過關。我只差最后一門就可以拿畢業文憑了,可這次卻考了個59分,沮喪透了。我們認為考題太難,去找考試辦主任穆穎同志提抗議。老穆靜靜聽完,說:‘自學考試就得這樣考!”
當今社會上流行的“說情風”,“條子風”,自然也會刮來。經常有人拿了公函,拿了條子來要求查分,甚至改考卷。對此,自學考試辦公室一概拒之門外,不管你來頭多大。在工作人員心目中,自學考試是一座神圣的殿堂,不容玷污。
艱辛備嘗的自學者
侯勇以自學考試英語“狀元”的身份,被選送到北京外語學院本科三年學習,成績也是一路領先。如今,他留校擔任了聯合國譯員訓練班的教師。
青年農民陳坤來,以平均80分的優異成績,拿到了果樹專科的畢業證書。他家在密云的一個村莊,每天要騎兩小時的自行車去做臨時工。農忙時節,下了班還要幫父親干農活。他只能用晚上休息時間來自學。為了去做實驗和考試,他前后24次往返于北京和密云之間。幾年艱辛,他終于成為當地果樹種植的“小專家”。
郭爭平占了自學考試的幾個“一”。第一批參加考試,第一批專科畢業,第一批得到文學學士學位,課程考試全部是一次合格。人稱“六一居士”。他愛人趙國騰報考了英語專業。夫妻倆互幫互學,比翼齊飛。英語考試前夕,33歲的趙國騰偏偏因先兆性流產住院。她咬咬牙從醫院趕到考場。考場設在四樓,趙國騰一步兩歇,撐著扶手一點點往上挪動。爬到二樓,她精疲力竭,實在走不動了。考試辦公室破例讓她改在二樓應試,結果大汗淋漓的她,竟考了滿分。
1989年,郭爭平以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當外國人問他畢業于哪所大學,他自豪地說:“我是自學考試出身!”
上校飛行員趙京戰,曾經在18個月里通過了19門考試,3年里拿了3個文憑:黨政干部基礎科、中文專科、中文學士學位。同時,他又在本職工作中榮立二等功一次。
1987年7月,趙京戰被派往加拿大改裝具有80年代水平的“挑戰者”飛機。沒想到,他在自學考試中獲64分的英語派上了用場。座艙設備上標明的英文,他都能看懂,聽課也能懂一部分。于是,他發現了教員講授過的一張圖表上有錯誤,提出了修改意見。這張圖表,教員已用它對來自美國、加拿大、西德的幾期學員講過課,誰也沒發現有錯。教員對此非常感謝。加拿大空軍的卡爾將軍立即打電話給中國駐加武官,稱贊中國飛行員“創造性地學習”,并向趙京戰贈送了紀念牌。
對于自學考試,嘗到甜頭的趙京戰自有一套說法。他說:“在校學習好比吃正餐,咱這是吃零嘴;在校學習好比用大塊衣料裁衣裳,咱這是用小布條兒拼拼湊湊。各有各的路子,不是嗎?”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站在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高度,實行全方位開放,對傷殘人也是熱情地敞開大門。
劉小容3歲患小兒麻痹,僅讀完小學。雖然她行走不便,生活艱難,但她渴求知識的愿望并沒有泯滅。她在病床上捧起了英語課本,經過5年苦讀,報名參加了自學考試。她沒法去考場,考試辦公室的同志先后8次為她單設家庭考場,外語學院的教師還到她家為她舉行口試。這位身殘志堅的姑娘,8門課都是一次合格,獲得了英語基礎科畢業證書。
李偉洪是一位盲人,靠自己扎教材學習。妻子和熱心的同事為他念課本,他用錐子一針一針扎成盲文。幾年間,他一共扎了300多萬字的盲文教材,堆起來有幾人高。扎完了教材還要理解、記憶、背著去豐臺區聽輔導課。在考場上,監考人為他念試題,他用盲文扎下來,用盲文答好,再錄下音交卷。就這樣,他以常人難以理喻的毅力,4年時間獲得了兩個大專文憑。現任北京盲文印刷廠廠長的李偉洪說,是自學考試為他闖出了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
十年樹人,功在國家
我國獨特的自學考試制度,已漸漸引起了國際教育界的注意。日本千葉國際大學的教授稱贊說,中國的自學考試制度很好,歡迎自學的畢業生來國際大學就讀。加拿大康克迪亞大學校長丹尼爾,是搞遠距離教學的專家,兩次盛情邀請自學考試委員會的專家去進行學術交流。
楊珍原是工人,自學考試獲得學位之后,調到了《人民中國》雜志當編輯。他沒有“忘本”,上任后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了一次“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同窗懇談會”,并為此寫了文章。文章在日文版《人民中國》雜志上發表之后,一個月間,雜志收到了幾百封日本讀者來信,稱贊和探詢中國的自學考試制度。
北京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畢業典禮,可以算得上是中國規格最高的畢業典禮了。它曾經在中南海懷仁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許多名牌大學的畢業典禮還沒有此份殊榮。
李鵬同志在1986年第5屆自學考試畢業典禮上說:“實踐證明,社會助學、國家考試這種自學成才的辦法,是一條成功的經驗,要給予充分的肯定,長期辦下去。”
自學考試制度之所以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得到青年的歡迎和國際友人的稱道,是因為它為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為無數無緣進入大學的有志青年提供了讓社會再次挑選的機會。從創立至今的10年間,僅北京地區就有16000人通過自學考試獲得了大專或本科文憑。可以想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會有更多的求學者,通過艱辛的自學之路,尋求知識,尋找更豐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