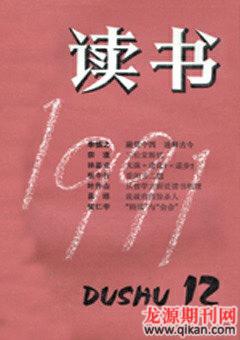“死而上學”的沉思
東 雪
死是一個斯芬克司之謎。自從有了人類,關于死的恐懼、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種方式的處理,便成為人類心,靈、民俗和文化的經久不衰的課題。關于死亡的哲學思考,近出《死亡哲學》的作者段德智杜撰了一個名詞,叫做“死而上學”。這個名詞造得妙不可言。一般“死亡學”中包含的大量的具體文化門類、具體科學所研討的諸如喪葬祭祀方式、死刑、死亡稅、核污染及死亡過程理論等等有關死亡的形而下的問題,不構成死亡哲學的對象。“在死亡哲學里,我們討論的是死亡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亦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與可避免性)、死亡的終極性與非終極性(亦即靈魂的可毀滅性與不可毀滅性)、人生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亦即死而不亡或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的個體性與群體性、死亡的必然性與人生的自由(如‘向死而在與‘向死的自由)、生死的排拒與融會,諸如此類有關死亡的形而上學的問題。”(第4頁)毋寧說,死亡哲學是死亡學之內核或最高層面。
叔本華曾經說過:“由于對死亡的認識所帶來的反省,致使人類獲得形而上學的見解,并由此得到一種慰藉……所有的宗教和哲學體系,主要即為針對這種目的而發,以幫助人們培養反省的理性,作為對死亡觀念的解毒劑。各種宗教和哲學達到這種目的的程度,雖然千差萬別互有不同,然而,它們的確遠較其他方面更能給予人平靜地面對死亡的力量。”這就把宗教和哲學由對死的反思上升到本體意識,最終給人以安心立命的終極依據的目的和功能表達了出來。
《死亡哲學》的作者指出,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死亡哲學有著我們不能窮盡的豐富意涵。概略地說,至少有兩個基本層面,第一是人生觀的或價值觀的層面,第二是世界觀的或本體論的層面。
從前一層意涵來說,死亡哲學是人生哲學或生命哲學的深化或拓展。其所以如此,按作者的觀點,首先是因為只有具有死亡意識的人才有可能獲得人生的整體觀念和有限觀念,從而克服世人難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緊迫感,有一種魯迅式的萬事“要趕快做”的“想頭”,從而“雙倍地享受”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緊張熱烈”(蒙太涅語);其次,“所謂死亡的意義或價值問題,說透了就是一個賦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無限)的意義或價值問題,因而歸根到底是一個人生的意義或價值問題。”(第5頁)這一層意涵當然不難理解。塞涅卡講“一個人沒有死的意志就沒有生的意志”。這也就是說,生只有通過死才能獲得它的意義和價值,換言之:“未知死,焉知生”。這與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恰恰構成對立互補的兩極。
作者強調指出,人生觀或價值觀的意義尚只是死亡哲學的表層意涵,與它相互區別而又相互貫通的更為深邃又更為基本的意義層面是世界觀的和本體論的意涵。因為只有通過對死亡問題的哲學思考,只有倚重死亡意識或者消解死亡意識,才能達到本體的洞觀、天人的契合。正視死亡,看重并借助死亡,樹立正確的死亡意識,是我們達到哲學意識、達到哲學本體境界的必要工具和階梯。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柏拉圖講“哲學是死亡的練習”;叔本華講“死亡是哲學靈感的守護神”;雅斯貝爾斯講“從事哲學即是學習死亡;從事哲學即是飛向上帝;從事哲學即是認識作為實有的存在(大全)。”作者認為,死亡意識的哲學功能,正在于它是我們超越對事物的個體認識、達到對事物的普遍認識、達到萬物生滅流轉、“一切皆一”(赫拉克利特)認識的一條捷徑,是把握世界和人生之全體和真相的充分條件。《易傳》講“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是一個極高明的見解。不過中國死亡哲學與西方略有不同,它是在“重生”“尊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背景下正視死亡,因而強調惟有超越、消解死亡,然后才能達到人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境界。《莊子·大宗師》:“外天下……外物……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王陽明《傳習錄》:若于“生死念頭”“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按莊生之論,只有遺世獨立,飄然遠引,超然物(利害、毀譽、榮辱、是非)外,才能進而“外生”(無慮于生死),“見獨”(體悟絕對的道),進入不知“悅生”“惡死”,“不死不生”,無古今、成毀、將迎的“攖寧”狀態,即萬物齊一的本體境界。按陽明之論,一個人的聲色利欲已難脫落殆盡,而“從生身命根上來”的生死念頭,則更不易“見破”“透過”,然不超越死亡意識,遑論見得貫通著的宇宙生命、人類生命和個體生命之統一的本體(“仁”體)?
似乎西哲西圣是從正面建構死亡意識的階梯、橋梁,以達致形上本體;而東哲東圣則從負面拆毀死亡意識的階梯、橋梁,以當下體悟本體。這是從死的角度說的。如果從生的角度來說,則西方是從生命意識的自我否定出發,通過建構死亡意識的曲折周章來接近形上世界;而東方是從生生不息的“一體之仁”之自我肯定出發,就在生命與生活的當下,直接地進入本體境界。這恐怕與西方哲學主流派的主謂結構、二分模式、理性主義與知識論的進路和中國哲學主流派的“整體一動態”結構、機體模型、生命體驗與道德學的進路之區別有關。然而正所謂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同歸殊途,一致百慮。
沒有死亡意識,就沒有生命意識。人類全新的死亡觀,誕生于文藝復興時期。蒙太涅針對基督教為了神而犧牲人的罪惡主張,痛心地指出:“我們最無人性的弊病就是鄙視人的存在”,從而把“研究我自己”規定為哲學的根本課題。人不再是自己命運的奴隸,而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籌劃者,人生也不再意味著忍耐、受苦、消極無為,而是可以依照自己的設計過得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正是面對死亡,省視了生命的個體性和有限性,才賦予生命以內在的價值!由“借死反觀生”到“以生界說死”,人類的生死觀發生了質變。殉道者布魯諾雖遭八年囚禁,面對羅馬廣場的熊熊烈火,仍然從容鎮定,厲聲高喊:“你們宣讀判決可能比我聽到這判決時更加膽顫心驚!”
爾后,在近代哲學家那里,人及其理性則成了死亡問題思考的唯一尺度和準繩。斯賓諾莎斷言:“自由人的智慧不是默思死而是默思生”。而所謂自由的人,乃是“純依理性的指導而生活的人”,由于他的自由和智慧,由于他依理性認識到必然性,他才能擺脫死亡恐懼情緒的支配而直接地要求善。當然,一般地說,近代思想家是以割裂、二分的思想模式看待生死關系的。拉美特利的下述十分機智頗為俏皮的話,典型不過地表達了近代西方人追求現世的凡人的幸福的生死觀:“我的生死計劃如下:畢生直到最后一息都是一個耽于聲色口腹之樂的伊壁鳩魯主義者;但是到了瀕臨死亡的瞬間,則成為一個堅定的禁欲主義者。”啟蒙主義健將、百科全書派首領狄德羅的話,字字擲地作金石之響:“如不能向惡毒的敵人正當復仇,我死不瞑目;如不豎立一座豐碑,我死不瞑目;……如不在世上留下時間無法消滅的若干痕跡,我死不瞑目!”
這種生死態度,當然是壯懷激越,令人神旺的!但是,真正深邃的所謂死亡意識,不僅僅是理性的,尤其是辯證的。惟其如此,才能升華為生命意識。黑格爾的精神辯證法,生與死矛盾運動的觀念,尤其是對事物內在的自我否定的頌揚,克服了近代生死二元對峙的局限性,是真正打開死亡之謎的鑰匙。既然死亡是一種內在的矛盾運動的結果,是事物通過自我否定獲得新生的契機,那有什么理由害怕、又怎么可能躲避呢?作者引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有關言論并解釋說:“如果精神害怕死亡,它就沒有勇氣直面自己的應當被否定的方面”。“所謂承擔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敢于去否定自己應當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經受怎樣的風險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辭。面所謂‘在死亡中得以自存,就是要在不停頓的自我否定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超越自身又不斷地回歸自身,不斷地實現自我和認識自我。”(第203頁)可見,死亡在黑格爾那里是一種揚棄,是精神的肯定與否定的統一、取消與保存的統一、分裂與和解的統一。而這一點,正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看重。以這樣的死亡觀去觀照天、地、人、我,還有什么牽掛粘滯而不能達觀自如呢?行文至此,眼前所浮現的是青年郭沫若描繪的鳳凰在火中涅
在西方死亡哲學中,自由原則和個體性原則是死亡意識向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轉化的樞紐。那么,這兩項原則是如何產生的呢?在理論上應如何定位呢?精心沉思,死亡的另一個更為本質的意涵,是在個體、群體與美的關聯,和自由意志與普遍必然性的關聯中展示出來的。原始死亡觀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超個體靈魂不死的信念。這實質上是一種由原始社會公有制中生發出來的集體不死的信念。超個體的靈魂主要通過氏族或部落首領體現出來,并隨著首領的代謝承傳下來,成為集體的“守護神”。原始公社的解體、私有制的出現,使得不死的超個體靈魂原子化或個體化了,從此由集體的靈魂不死信仰過渡到個體靈魂不死信仰。作者認為,原始死亡觀的崩解與人的死亡的發現的先決條件就是“人的個體化”。在荷馬史詩里,個體靈魂的二重性(有死的靈魂即認識能力與不死的靈魂即生命原則)得以確立。人的死亡的發現內蘊著兩個層面,一是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一是死亡的終極性。這就啟發了肉靈(身心)關系或精神與自然界的關系和死亡與人生的關系等問題的思考,也就呼喚了哲學的產生。直到亞里士多德,才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如何使我們的有死亡的生命具有不朽意義這個死亡哲學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奠定了理性主義的死亡哲學的基礎。作者認為,“亞里士多德注重從人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入手,從個人同群體和類的關聯來考察待死態度問題,提出借道德和勇氣戰勝死亡的問題,這同蘇格拉底著重從個人的人格和形象出發來考察待死態度相比,顯然要高出一籌。”(第81頁)
這是什么意思呢?人的個體化是人的死亡的發現的前提,然而人畢竟是社會的人,人是普遍的自我與個體的自我的統一。任何正常的人都知道,界定“自由”離不開普遍必然性,界定“個體”離不開群體和類。所以康德提出了自由人自己選擇去死這樣一個死亡哲學的重大命題,強調了“意志自律”,同時又要求人們把死亡方式的選擇自覺地建立在超乎個體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準則的基礎上。黑格爾進一步指出,“死亡的根據是個體性轉化為普遍性的必然性。”這是因為,自然或肉體生命作為類的一個個體原本就潛在地具有普遍性(類的特征)。精神或理念突破自然生命的局限,使自身從片面的直接性和個體性中解放出來,達到自身的普遍性,達到現實的個體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然而,自然生命達到這一步的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死亡。死亡是對肉體生命的“個別的純粹的個別性”的克服,因而也就是對事物世界和功利世界的否定。唯有死亡我們才能超越“意識”而達到“自我意識”,超越功利世界而進入道德世界。“在黑格爾看來,一個人要達到獨立的自我意識,非有死亡意識不可,非有點拚命精神不可。因為所謂獨立的自我意識,其本質必然是一種自為的存在,是一種自由的意識,一種不束縛于任何特定的存在的意識,然而它又必須是通過另一個意識而存在的意識。這樣作為這種精神現象的對立的雙方,必然處于一種互相拼命的狀態,即它們自己和彼此間都通過生死的斗爭來證明它們的存在。”(第207頁)正是從獨立和自由的自我意識的立場出發,黑格爾對人格作了頗具特色的界說:“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可以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的真理性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以待死態度區別了主人意識和奴隸意識。主奴意識之間的辯證緊張正是構成歷史運動的基礎的東西。總之,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死亡不僅是精神超越意識達到自我意識的重要契機,不僅是精神從主觀精神達到客觀精神、達到道德世界、成為倫理實體的重要契機,而且也是精神超越有限制的倫理實體達到更為普遍的“世界精神”乃至“絕對精神”(狹義的)的重要契機。通過死亡,達到人與上帝的同一,即人的個體性與人的普遍性的同一。
自由原則和個體性原則是死亡意識內蘊的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敞開或升華的極其重要的關節點。在這些方面,西方哲學史上的有關爭論給予我們許多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值得認真地記取。本書作者的許多細致的、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相信能對青年人正確地建樹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的生死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以有益的幫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列專章系統地、歷史地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亡哲學,并結合國際共運史上的許多英勇戰士的生死業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地指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生死觀才是過去時代死亡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和歷史總結,是當今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偉大成就。正如哲學史家陳修齋和蕭
“存順歿寧”,“生寄死歸”,中國傳統哲學自有一套特殊的生死智慧。本書盡管在不少地方論及中國的死亡哲學,但畢竟未及深究。我們期待著作者在本書的姊妹篇《死亡與文化》、《中國死亡哲學》中再行展開。此外,由于本書架構的限制,死亡哲學中的許多研究專題,例如死亡與愛情、自殺理論等,雖在評述各代表人物死亡哲學思想時均有涉及,但沒有集中深入地分類探討。從屈原到三毛,自殺的該有多少?那維護尊嚴、抗議無道的,如老舍、翦伯贊、傅雷先生等,以死來成就完滿人格,實現人生價值,悲憤蒼涼,然都能理解;而那種由于文化價值系統失序、轉換引起心理失衡而導致自殺的,如梁漱溟的乃父巨川先生和學界巨擘王靜安先生等,則頗不易揣度;還有諸多作家、詩人,包括不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則另屬一類;還有我國農村曾發生過的幾位青年姑娘相約投河而死;還有七十年代末美國的“人民圣殿”宗教組織的九百多人集體大自殺。如此等等,都是死亡哲學不能不研究的問題。本書甚至沒有為加繆列專節,評者頗覺悵悵。
文德爾班說:“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與自殺對應的另一面,如太史公含垢忍辱,身殘處穢,就腐刑而無慍色,終而完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至于文天祥、譚嗣同、李大釗、張志新等,臨難毋茍免,鐵肩擔道義,未敢昧大義而輕生,未敢昧大義而懼死,更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梁!
(《死亡哲學》,段德智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精〕9.25元,〔平〕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