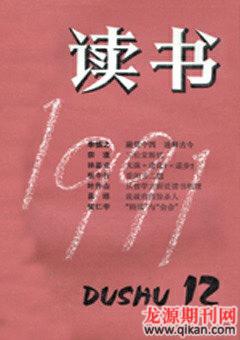“持續”與“匯合”
黃仁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陸版序
這本《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包括的內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點則表彰中國歷史有它的特色,前后連貫,通過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階段,各篇雖大致以人物傳記之體裁為主,所紀事之影響遠逾當時人之人身經驗,積累之則與我們今日之立場仍然有關。
自明朝至現今的一段,原擬定也照同樣體裁敘述,出版者還盼望我出一本《赫遜河畔再談中國歷史》。只因歷史的進展成螺旋式,愈至后端積累的分量愈重,內容也更復雜,其內容不容易保持文藝副刊的風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幾種工作,不容易擺脫。所幸已有《萬歷十五年》,《放寬歷史的視界》,英文本Chian:AMacro-history(中文本題為《中國的大歷史》,可望于年內出版)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已編排完畢,即將出版,英文本也在編撰中),都由作者執筆。讀者不難從此中看出,上述前后連貫的特性并未因元朝而中斷,也因明清而持續迄于今日。而且在二十世紀末季,中國的歷史也確切的與西洋文化匯合。
對大陸的讀者講則因上述書刊尚待問世,刻下有將所謂“持續”及“匯合”兩點扼要作梗概的報告之必要。
中國雖然在歷史上產生過九個統一全國的大朝代(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個到二十個的小朝代,為研究檢討的方便起見,我們仍可稱秦漢為“第一帝國”,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第一帝國的政體還帶貴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國則大規模的和有系統的科舉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將經濟重心由華北的旱田地帶逐漸轉移到華南的水田地帶。在第一第二帝國之間有過三個半世紀以上的分裂局面(晉朝之統一沒有實質)。若將第二帝國與第三帝國比較,則可以看出第二帝國“外向”,帶“競爭性”,與明清之“內向”及“非競爭性”的豁然不同。在財政與稅收的方面看來,其性格之差異尤為明顯。第二帝國帶擴張性,第三帝國則帶收
朱元璋創建明朝,他的種種措施在中國近代史上講實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如紡織業、冶金、鑄幣、水運等)為主體造成行政之張本,結果節節失敗,卻沒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帶服務性質的事業(民法、商法,保險業及銀行等)沒有展開,私人財產權缺乏固定性,無從在數目字上管理。他只憑己見認為凡是提倡擴大經濟范圍的說法即是“與民爭利”和“聚
明朝的財政與賦稅以較落后的部門(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為基礎。三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時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時又全面恢復,而以人身服役為原則,即各級衙門所用文具紙張,桌椅板凳,軍隊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補修理均無預算之經費或供應之承辦者,而系無費由各地里甲征集而來。朱元璋更利用“胡維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獄去打擊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一三九七年戶部報告,尚有七百畝田產以上者,全國凡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其名單也進呈“御覽”。如此造成全國皆以小自耕農為主的龐大之扁平體,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揮,雖有短期間之平等,而缺乏經濟上之組織與結構。
唐宋時之轉運使在各地區間活動,手中有大量物資周轉,明朝放棄此種辦法。朱元璋的財政體系成熟之后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的短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以接受二三十個縣的接濟;一個縣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機構交納財物。戶部不再成為一個執行機關,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會計衙門,只能核銷小數目此來彼往的供應,無從籌牟全局的重新分配,本此情形之下,服務性質的事業也永遠無法展開。大凡現代化之前,民間的經濟組織有賴與政府官衙交往開始。意大利的銀行家即因代教皇輸納各地的十一捐而發韌,日本的“藏元”和“兩替”也系承差于幕府及各大名,才開始出頭露面。中國明清間的商人始終無此機緣。
過去有些歷史家以為明后季行一條鞭法,朱元璋的財政稅收體系,即已改進。殊不知財政與稅收為承納于一個國家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間之法制性的連系,牽涉到官制與兵制,以及鄉村里甲和城市街坊間的結構,也與法庭判案的能力與社會風尚全都有關。明清的制度,既然如此之特殊,如果一經更革,則以上各種因素全要更革。一條鞭法只是各地會計制度局部間的修正,與全面更革的范圍相去至遠。五十年前梁方仲研究一條鞭法,其結論則是行一條鞭法后明代的財政稅收仍是“洪武型”。我們也可以更大膽的指出雖有明清之交替,康熙時將丁額永久的固定,雍正時的火耗歸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稅收開始出現,剿辦太平天國期間開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之財政仍與第三帝國全始終。我們只要從鴉片戰爭時支持揚威將軍奕經的軍費,和甲午中日戰爭前供應北洋艦隊的經費即可看出:清代承明之舊,只有零星支付局部需要的能力,而無全面經濟動員打破局面之可能性。所以從長時期遠距離的角度看來,明清之體制為一元。
什么是洪武型的財政?簡言之為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經濟為始終,憑零星雜碎之收入拼湊而成,當中因素都容易脫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產,忽視供應行銷間可能的技術上之增進。可是說到這里,我們也要附帶申明:這種觀點只因我們在六百年后體驗到,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國家不能適應于外界新潮流之創痛,才能產生。在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決策時,一般人士未嘗不以之為得計。一個大陸性格的國家動員時注重數量而不注重質量,企圖長期保持各地區間之平衡,不計較對外折沖時一時一地的禍福得失,都有它特殊之邏輯。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為全國的標準,并不完全是缺乏頭腦,明朝即為中國惟一之朝代其用兵由南至北而統一全國,而且因為其資源零星擱置,各地的總督巡撫無從跋扈割據而尾大不掉。有明一代除了有幾位王室人物和農民造反外,并無文武官員擁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像嘉靖朝的張經和崇禎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紙文書的逮捕,隨意處決,為以前所未有。而承著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之外,清朝又繼續如此的紀錄達二百六十七年。除了所謂“后三藩”,系明降將曾舉兵反之外再無一個重臣背叛朝廷,這樣的紀錄為西方之所無,在中國也僅有。因為其整個社會重文輕武,國家不待軍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會價值(social value),所產生的社會秩序,以“尊卑,男女,長幼”作綱領,有替代法律之功效。雖說今日我們已不能欣賞此作風,也知道其標榜不盡符合事實,卻無法否定其為地緣政治下之產物。本書已一再提及中國反映著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讀詩書之士人統治大量農民,無法應付變叛(variables),所以才強調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這些特點都因明清帝國而發展到盡端,直到鴉片戰爭才徹底暴露這樣的體制不能在現代社會里存在。
一提到現代社會,則當中端倪紛紜,可以發生無限的爭執,我個人也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也根據著居留在英國、日本、美國和旅行其他各地的經驗,則發現先進國家完成現代化之程序,當中無不有一個從以農業作基礎的管制方式進而采取以商業為主體的管制方式。其先決條件,對外能自主,對內鏟除社會上各種障礙,使全部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然后這個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在數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歸金融及財政操縱,政府在編制預算,管理貨幣,厘定稅則,頒發津貼,保障私人財產權利時即已普遍的執行其任務,而用不著張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萬能”的原則,零星雜碎地去權衡各人道德,再厘定其與社會“風化”之影響。只是農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系為單元;商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系為多元。這體制上之改變,絕非輕而易舉,通常有類于脫胎換骨。大凡近世紀各國的革命和獨立運動,流血不止,通常與這種改變有關。一待某一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種數字,尚可以隨時商酌,大體上以技術上的要求作主,不必籠統的以意識形態為依歸了。
說到這里,我更要提醒讀者:中國過去百多年來的動亂,并不是所謂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軍人專橫,政客搗亂,人民流離。清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七年,本來也是“氣數將盡”,這也就是說專制政體全賴人治。當初皇帝如康、雍、乾日理萬機,還能稱允文允武,以后之君主實為典章制度之囚人,況且宮闈間的糾紛與黑幕愈多。及至慈禧太后主廢立,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之一代不如一代,已難能維系人心,遑論及忠臣烈士之“死社稷”,是以本來即有覆亡的征象。再則參入這“換朝代”的機緣中又有了一個“改造帝國”之必要。明清兩朝合并為五百四十三年,也和第一帝國之四百四十一年及第二帝國之六百九十八年(內有五代十國之分裂局面五十四年)大致上等量齊觀。這第三帝國既有收
所以中國的長期革命,費時必多,為患必烈。法國“老虎總理”克里曼梭曾說革命總是一個大整體,一個大方塊。亦即一經發動,玉石俱焚的公算極高,很難照應到各人各事內在的公平。康梁百日維新失敗后,譚嗣同自愿犧牲,即是已經看穿長期流血之無可避免。
但對中國事情,當時只有極少的人能看到全局之高低縱深,大多數人士只能隨著內外壓力,一步逼一步,逐漸覺悟到大規模改革之無可避免。迄至辛亥革命之后,肇造民國,猶且不能解決問題,才有五四運動之展開,知識階級覺悟到改革必從本身著手,及于文化和教育。
我曾在《萬歷十五年》再版(一九八六)之跋,稱為“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寫出:國民黨專政期間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共產黨則因借著土地改革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今領導人集團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之間敷設法制性之聯系。這樣的程序,也和所有產業革命先進的國家之所經歷符合。其最后的目的則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中國能做到這地步,中國歷史即已與西洋文化確切的結合。大凡管制人類群眾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勸,由神父牧師及政治指導員主持之。二是武力強之就范,受軍隊巡警法庭的操縱。三是策動各個人之私利觀(我們也可以強調其為開明之私利觀〔en-Iightened self-interest〕),于是各個人赴利避害之間,即已間接的趨向于集體的目標。以上也帶相對性格。迄今也沒有一個國家,只采用一種方法,即能將其他兩種方法完全擯棄。
最后我希望與本書讀者共同保持一點檢討中國歷史的心得,此即當中的結構龐大,氣勢磅礴,很多驟看來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長時期遠視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來卻仍合理。中國既已在二十世紀幾乎亙全世紀的盡瘁于革命,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作殊死戰八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紀錄,在人類史上也是僅見。土地改革規模之大,行動之徹底,亦超過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時間的平等,而在給新體制一個合理的出發點。現在進入建設時期,應該能克服困難,使國家資本有民間經濟作第二和第三線的支持,在新世紀里成為一種穩定全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們希望如此,我們衷心希望如此。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紐約州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將由三聯書店在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