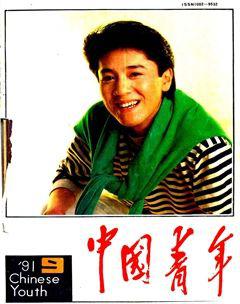職業價值的新生代
樓靜波 段躍
處在一個空前變易的年代,處在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舞臺中,青年人幾乎來不及去反思前輩灌輸給他們的種種觀念,更來不及去構造他們自己的價值體系。迫切等待和迎接著他們的是現實的生活課題,他們的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跟隨著瞬息萬變的社會局勢和隨時得來的新知識、新觀念而矛盾錯雜地、彎彎曲曲地向前發展著或倒退著。
在這個過程中,相當一部分青年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生活必須根據下一步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來考慮,而不是預先規定的遙遠的終極目標。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當代青年的職業價值判斷中可以獲得更為清晰的印象。筆者將借助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青年價值取向”課題組的調查資料進一步加以描述。
在他們心目中,腦體價值并非倒掛著,但價值的起點卻沖出了傳統的范圍。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學而優則仕”在中國已流傳了上千年。這種用“治人”與“仕”來體現知識與腦力勞動最高價值的法則早已潛移默化為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一部分。盡管近代以來,這種價值觀經歷過多次文化運動的批判,但在缺乏相應社會變革的情況下,單靠人的信仰意志是無法使之發生根本動搖的。
新中國的成立,使新一代的青年獲得了一個比父輩更為幸運的機會:在他們價值觀形成期的前后較為廣泛地認識、感受了現代文明,而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則在更大程度上,從一開始便沐浴在改革開放的陽光之下。在青年們所感受到的現實中,“知識就是力量”不僅代表了時代的先進思想,而且顯示出越來越巨大的精神和物質成果,這種來自于社會變革與信仰意志的雙重力量更為深刻地動搖了傳統的價值觀念,知識與腦力勞動的價值沖出“治人”與“仕”的范圍,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不斷地擴展著、延伸著。
盡管改革的步伐還來不及充分滿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要求:盡管現實中仍嚴重存在著腦體倒掛現象,很多人還在抱怨“造原子彈者不如賣茶葉蛋者”;盡管不少青年人為了生計不得不丟棄本以為神圣的職業換取基本生活的滿足,但是我們仍會看到青年對知識與腦力勞動的崇尚并沒有減弱。1988年和1990年兩次全國性調查的結果是:青年對企業家、科研工作、大學教師、醫生等以腦力勞動為特色的職業評價,除中小學教師外,全部高于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對腦力勞動的崇尚帶有鮮明的功利色彩。或者說,支撐著青年們的并不是一個偉大的、古老的信條,而是腦力勞動在民族和個人發展中所顯示的實際效果。我們在調查中獲得了這樣一組數字:同是腦力勞動、青年對中小學教師的職業評價只排在16種職業的第11位,居合資企業之后。問及原由,大多數青年回答,中小學教師收入低、待遇差、工作辛苦。而1990年的另一項調查中當問到“你認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障礙是什么”時,又有80%以上的青年把基礎教育薄弱列在了前幾位。從現象上看,青年們的回答似乎充滿了矛盾,但當我們繼續將兩年的數據加以比較后,又會發現:青年對企業家的評價在兩年的調查中均居16種職業之首。為什么同是腦力勞動,同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卻在青年的選擇中拉開如此的距離呢?一位青年女教師的述說似乎更準確地揭示了這個謎:“我的職業是神圣的,但我的生活卻是艱辛的;我不愿在白日里做一個神圣的夢,更不愿在夜晚中為我生活的貧乏與勞累而哭泣。”另一位青年在評價電視劇《渴望》時曾發出過一個疑問:“劉慧芳用愛溫暖了小芳的心,但真正使小芳站起來的卻是王亞茹的手術刀,究竟是哪種力量使小芳走向了新的生活?”
從這里我們也許找到了青年職業價值判斷的一個特點:站在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青年首先選擇兩者的兼而有之;但當這一愿望難于在現實中兌現時,他們又會把側重點放在自身利益方面。
他們看重了個體戶,不僅為了賺錢,更羨慕那里所擁有的機會。幾乎所有人都會對10年前的情景記憶猶新,1979年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其中個體戶的興起更引起世人的矚目,它在沉悶的社會屏幕上劃了一個令人振奮的信號。然而,當個體戶做為一種職業的選擇項目擺在了每個具體人面前時,它給人們留下的卻是一聲不得已而為之的嘆息。
當時幾乎沒有多少家長心甘情愿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擺地攤、開飯館,也沒有多少青年樂意將自己一生的事業拴在個體勞動者的執照上。如果沒有龐大的待業大軍,如果我們的國營企業有望將他們容納,發展個體經濟的政策很難吸引住當時的青年。1983年前的多項調查表明,青年個體戶的最大呼聲是:“提高社會地位,贏得更多的尊重。”而能夠在國營或集體企業就業的青年,對于滿街叫賣的個體戶從來就是不屑一顧的,顯然,他們比個體戶擁有著更優越的地位和更穩定的生活保障。
10年過去了,不知不覺中我們對個體戶的印象似乎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只是坑蒙拐騙者的代名詞,他們當中涌進了不少高層次的青年,他們帶給了我們越來越豐富的精神與物質享受……社會已離不開個體戶,青年也悄悄地羨慕上個體戶,甚至當他們有時在國營單位工作得不順心時還會這樣說一句:“再解決不了,咱也去干個體戶!”
這種印象與我們調查的結果幾乎是一致的:在1988年的調查中青年對不同所有制的職業評價呈現了以下趨勢:
個體專業戶>合資企業工人>國營企業工人>集體所有制企業工人。而1990年的調查對個體戶的評價雖低于國營企業,卻仍高于集體企業。
誠然,評價與行動之間經常存在著距離。事實上,近幾年仍有不少個體青年在經過了幾年的苦心經營后,忽然間變賣產業、交回執照,重新返回國營企業。而國營企業中卻有一部分青年,一只腳踏著國營企業的大船,另一只腳踩著個體戶的小舟,在可進可退之中尋求著自身的滿足。客觀地看青年對個體戶的態度是:在理智上評價高,在行為上則若即若離。
經過分析,我們找到了進一步解釋上述現象的數據。當問到對職業的所有制評價的主要依據時,相當一部分青年認為,個體勞動比國營企業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在評價16種職業時,同是腦力勞動,黨政機關干部被排在了第8位,其絕對數遠低于對個體戶的評價。當我們在一次座談會上詢問其中原由時,一些青年說:“黨政機關最令我們不滿的是,不但收入少,而且不自由。”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到兩方面的提示:一方面在日益活躍的經濟生活中,青年人獲得了更廣泛的選擇機會,他們對勞動的自主性、創造性和實效性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國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崗位的有限性又難于在短期內滿足青年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現實與需求的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對個體戶的態度恰恰是這一矛盾的體現。
在他們的選擇中,社會聲望和身份越來越成為一個古典的夢,他們更感興趣的是高額收入和高度輕松。
調查向我們顯示了兩個出乎意料的結果。
一向把“社會聲望”做為擇業重要標準的青年人,如今卻將之棄于一旁了。1988年的調查中,城鎮青年只有2.1%把社會聲譽放在擇業因素的第1位,1990年的調查中,社會聲望在擇業的11種因素中則被排在了倒數第2位。青年在考慮現實、具體的擇業標準時,個人成就和收入遠比社會聲望更重要。
與此相關,另一項結果也很有趣,農村青年在擇業時并不著眼于“改變農民身份”。農村青年對務農的評價是不高的,把認為“務農較好”和“很好”的相加起來也只有10.6%,居10種可供選擇職業的末位。但擇業時把改變農民身份做為首要因素來考慮的則寥寥無幾。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改革開放使相當一部分青年在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實現了農民身份的轉變,另一方面也說明對自身發展的實際滿足比社會聲望和身份更能吸引青年。
調查還顯示出這樣一種傾向,相當一部分青年把很大的興趣放在了職業的“輕松、自由”和“高額收入”方面。面對一個個迫切需要解決的日常實際問題,曾經被人們所看重的社會的聲譽與身份,在青年眼中越來越成為一個古典的夢,這個夢依然具有美好之處,但現實也許是更美好的。
青年的職業價值取向是青年價值觀中一個極不穩定的部分,我們很難由此而做更多的結論,我們的最大收獲就是從中尋到了青年所共有的一個價值判斷原則:這就是實用的現實主義方法。這種原則不僅向我們解釋了當前青年中的許多現象,而且也預示出,當青年們眼前的問題得到解決后,他們是否又想為自己的生活找出新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將遠遠地高于他們在成功地解決了日常實際問題時所體驗到的那種成就感呢?對此,我們應當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和更恰當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