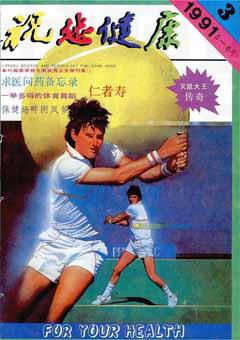仁者壽
孫觀懋
一九九0年的十二月六日,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我見到了當代著名作家、九十高齡的冰心老人。
這是一個溫暖的冬日,冰心老人的家里更是一番春意盎然,玻璃窗外的陽臺上,一片怡人的綠色。我們進屋時,老人正端坐在書案前,神清氣朗地在閱讀一本雜志。書案緊靠著窗戶,案上堆滿了書。午后的一抹陽光照在老人和藹慈祥的臉上,讓人感到分外親切,老人的身后有兩架書櫥,我特別注意到,櫥里有兩幀小像,一幀是她的老伴吳文藻先生,另一幀是巴金先生。
老人見到我們很高興,拿出紀念冊來讓我們簽了名,并說,到她這兒來的人很多。她因為腿跌傷后不方便,已有十年不參加社會活動了。但是,從她最近幾年發表的文章以及和我們談話的內容來看,老人對外面的情況十分了解,豈止了解,而是洞若觀火。
有人說冰心老人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這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從五四運動到四五運動,從廿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她用筆寫出了人民的血和淚、壓迫和反抗、痛苦和歡樂。她謳歌祖國的大好河山,抒發對中華民族的無比深情。當我們的國家進入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后,她已八十高齡,可她卻說,她的生命從八十歲開始,真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八十歲以后,她不斷的有新作品問世,有小說,有散文,有評介,更多警世的文章。以至有人把這稱作“冰心現象”。冰心老人瘦小的身體卻蘊含著如此頑強蓬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這倒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生命現象。
當我問到老人有何養生之道時,老人笑了笑,她說:“我都不能動了,還有什么養生之道好講。”
我說:“我剛才看您讀書寫字都不戴眼鏡,還經常有作品問世,我的年歲是您的一半,可沒有您這樣好的身體。”
她說:“要說養生之道,我可沒別的,什么事都不要擱在心上,這就是了。你想想,一個人把什么事都擱在心上,他還能活得下去嗎?”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后來轉入了別的話題。冰心老人沒有再談養生之道,沒有談她的飲食起居,沒有談她吃什么補藥,更談不上打太極拳、練氣功什么的,我當然不便追問,我覺得“什么事都不要擱在心上”,有這句話就夠了。這雖是一句明白不過的話,但做到它卻并不容易。現在的人,這“事”就來得多,而又是“事不如意常八九”,“不如意”、“不順心”的事又不少。不擱在心上,你就得超脫一點,得豁達大度、得甘于淡泊、得做到世事通明、人情練達方可。這就不容易了。常有人嘆息活得很累,倒不光是體力上的勞累,而是心理上的負擔太重,擱在心上的事太多。
曹操說,“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講的不也是這個道理嗎?
冰心老人的生命之樹常綠,還因為她用的是愛泉的水去澆灌。
我從小就愛讀她的《寄小讀者》,珍藏著一本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的藍綢面精裝本。這次帶到北京請她簽名,她欣然為我簽下了“觀懋小友囑簽名留念”,“小友”兩字讓我激動不已。我有一本初版《繁星》,文革時被抄沒了。我喜歡冰心那一系列“為人生”的問題小說,喜歡她的清麗、雋永的散文。而這些作品,一首首、一篇篇,無不是充滿著愛。
“母親啊,天上的風雨來了,鳥兒躲到她的巢里;心中的風雨來了,我只躲到你的懷里。”
“這時心下光明橙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里,看不分明了。”
“生命之燈燃著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著了。”
“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
這就是冰心老人的愛心。
一個充滿了愛心的人當然也就不會把別的什么事都擱在心上了。
九十年的人生歷程,冰心老人始終不渝地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的人民、愛母親,愛兒童、愛廣火的青年,她愛得真摯、愛得深沉,她有一顆偉大的愛心,人們也回報對她的熱愛。
愛使人高尚,使人充實;愛使生命之樹常綠,使人永葆青春。
孔子曰:“仁者愛人”,“仁者壽”。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