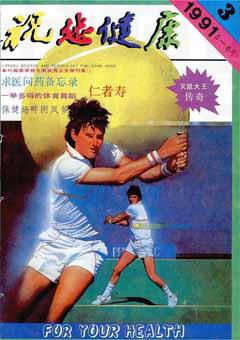養生與獻身
俞友德
人們說:“健康不是一切,但沒有健康就沒有一切。”有許多年事已高的學者、專家仍然在默默地工作著,他們那種可謂兼程而進的精神十分感人。但試想,如果他們沒有健康的身體,又怎能在各自的園地里繼續耕耘、播種呢?毫無疑問,這是和他們平日注意養生、堅持鍛煉分不開的。據說著名書法家費新我每天都要打幾次太極拳,顯然,養生為獻身于事業作了可靠的保證。
事物往往是雙向的,養生為了獻身,獻身也有利于養生。
老年人更成熟、更老練,認識到這個優勢,就會感到有許多事需要去做;有了這個欲望,也就有了精神支柱。年已古稀的姚雪垠同志,為了實現他宏偉的創作計劃,為后人留下豐厚的文學遺產,正以“老夫聊作少年狂”的豪邁氣概,每天清晨3點就起床揮毫寫作,這樣充沛的精力,除了他堅持體育鍛煉外,就是來自于崇高的追求。我國著名女作家謝冰心,年屆90仍筆耕不輟,自然也是基于有崇高的追求精神。宋代歐陽修說過:“優勞可以興國,豫逸可以亡身。”“宴安鳩毒”是人所共知的。執著的追求不僅是事業取得成就不可缺少的素質,也是人們保持旺盛精力的一根堅強的精神支柱。
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的關系從來就密切相關。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同志往往有空虛感,若能根據自己的情況,繼續為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那就不會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嘆息了。因為“黃昏”心理可以加速生理老化,是不利于健康的,是不可取的。曹操說得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種昂揚積極的心態值得我們效尤。
也許有的同志在選擇干什么時有一定困難,其實可干的事多得很,它們有的或許是“微不足道”,但只要做得出色,同樣可以在自己身后留下一座權勢和金錢所不能建造的豐碑。何況在我們把情感傾注在自己所選定的工作上時,會感到生活的充實,客觀上也會自然地排除種種可能導致苦惱的俗事糾纏,這也大大有利于養生。我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內經》上就有“聚精會神乃養生之大法”的精辟論斷。
總之,養生是為了獻身,獻身也有利于養生,懂得了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就懂得了科學的養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