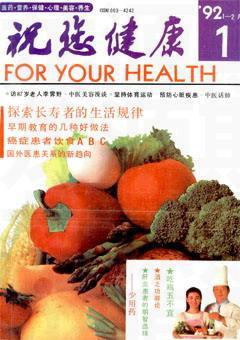國外醫患關系的新趨向等
夏青珞等
所謂醫療的現代化,就是說營養不良和傳染病等病癥已大致克服,醫療的課題已轉移到癌癥、老年病、遺傳性和先天性疾病等更加精微的領域。也就是說·從對急性病的研究過渡到了對慢性病的探討。
僅以美國而言,70年代在醫療領域投入大量的研究經費,于是出現了一些新型尖端醫療技術。例如腦死亡、器官移植、人造器官、體外受精、遺傳病的篩檢、胎兒診斷與治療、基因治療技術等,都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邁入實用階段的。
隨著尖端醫療技術的應用。與人類生死攸關的醫學知識也大幅度增加,醫學研究的領域已擴展到生與死的邊緣。人們甚至可以用人為的方式操縱生命。這使醫學觀和倫理觀陷入了兩難局面。因而人們需要一仲新的醫學倫理觀來代替已經難以自圓其說的舊理論。當然,說由尖端醫療技術引發了倫理問題也不盡然。與其說尖端醫療技術引發了新的倫理問題,不如說醫療現代化促進了醫療思潮的改變。
就醫患關系來看,過去以至現在,在大多數國家中是由醫生決定治療方針的,而患者只是執行者。如果把治療方針的決定權交給患者,患者便可自行設計和選擇治療的內容。這種情形如果再往前發展一步。患者就將成為“訂購者”,醫生則成為受理的一方。這一改革是醫患關系的一種新的組合,是醫療思潮上的一大革新。
根據這種新的思考模式,身為“訂購者”的患者可以從自己的生活信條和宗教信仰出發,選擇與設計合適的醫療方案。這樣,在醫療活動中將加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這些觀念往往突破了傳統醫學倫理觀范圍。因此,隨著醫療結構的改變,必須有一套學問來應付新的倫理性問題。它的目的是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上的人類行為進行系統性的探討與研究。
在70年代前期,歐美發達國家的醫學研究急速擴展,醫學理論與觀念出現了混亂的局面。各種議論紛紜一時,腦死亡觀念的確定、器官移植的手續問題、人體實驗、人工流產和胎兒手術的應用等棘手問題接踵而來。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這些問題大多都已獲得解決。特別是在患者自主權方面有7很大的突破。開始,提倡這種新認識的人。只是要使醫生承認自己對患者負有說明病情的義務。然而后來卻逐漸發展為患者有權從醫生那里知道關于自己的一切病情,并參與治療決策。經過冗長繁雜的爭論,患者終于作為可以自行決定命運的現代人,登上醫療活動的舞臺。由于患者權利的確立。一些新的問題又被提出,例如:病入膏盲的病人是否可以決定切斷維持生命的一切“管道”,或決定讓醫生幫助自己結束生命。進而與生命相關的其它問題也相繼提出,如受精卵冷凍保存、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代理母親等。
由此可見,尖端技術運用于醫學診斷與治療的過程,不僅可以促進醫療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引起醫療秩序的變革。因此,在重視引進和運用新的醫療儀器和技術的同時,也應適當地調節人們的醫療觀念。這樣才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中醫看病也需病家開口
薛耀東
有人認為,中醫看病“勿須病家開口,便知百病根底”。因此看病時不主動敘述病史和病情變化,只待醫生摸脈下藥。這實在是種誤解。
切脈固然是中醫診察疾病的一種方法。醫生可以通過脈象來了解人體的陰陽盛衰,辨別證候的表里、寒熱、虛實。然而,人體是復雜的,疾病也是多變的。有時脈象提供的信息就很含糊。如弦脈,肝病可見,各種疼痛、痰飲、瘧疾亦可見。另外,臨床上還可遇到與疾病本質不相符合的假脈。故欲正確診斷疾病,便不能惟以切脈為能事。《內經》曰:“診病不問其始……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現代著名中醫學家蒲輔周也反對將切脈神秘化。
其實,中醫診病除了切脈外,還需要進行望診、聞診和問診。通過望診,醫生可以了解病人的精神狀態和舌象、體表變化。通過聞診,醫生可以了解病人語言、呼吸、咳嗽等聲音變化,了解病人排泄物、分泌物的氣味。而問診的內容就更加豐富了。有歌訣日:“一問寒熱二問汗,三問頭身四問便,五問飲食六問胸,七聾八渴俱當辨,九問舊病十問因,再兼服藥參機變,婦人尤必問經期,遲速閉崩皆可見,再添片語告兒科,天花麻疹全占驗”。既然醫生需要問診,病家自然也就要開口,將自己何處苦楚、何因所致、何日開始、晝夜孰甚、寒熱孰多、喜惡何物、曾服何藥、曾經何地等病情病史告知醫生。只有這樣,才能加強醫患雙方的交流,以便順利地完成各項醫療活動,而不致于誤診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