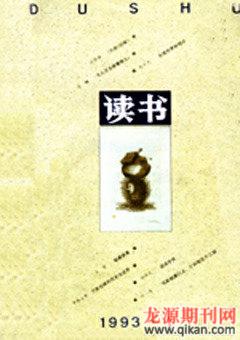萬里長城的歷史與迷思
羅厚立 葛佳淵
以前常從普及讀物里看到:人類所有的建筑物中,只有長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觀察到。可是前年出版的林
關于西潮東漸,過去西方漢學界對近世中國史的著作,常遵循一種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模式。其特點之一就是無論對西潮沖擊是褒是貶,都忽略中國自身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文化思想的內在發展。六十年代后,美國學術界逐漸左傾。在此大潮中的不少美國漢學家們,往往因西方過去侵略中國而產生一種負疚感,所以倡導一種要“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研究取向。柯文(PaulCohen)教授以此為題著有專書,前幾年已由中華書局出了很不錯的譯本。這個新的研究取向當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可是讀了柯文一書仍不免覺得有些“隔膜”。蓋柯文一書主要是對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國漢學界主流進行批判的反思,而從中國的視角觀之,其所批評的一些主要觀點不僅不錯,實際上可以說還認識發展得不夠。
對于這些問題本文不能一一涉及,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柯文批評了費正清學派關于西潮入侵以前中國只發生“在傳統范圍內的變化”的觀點。雖然柯文正確指出了費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國的不變即缺乏西方那種“根本轉變”的一面,但柯文在批評的同時將這一觀點本身亦視為不妥而擯棄,則不免矯枉過正了。實際上,費正清諸人或許是無意識地觸及到了儒家或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的一個根本要點,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實際上,在傳統范圍內變即溫故而知新,正是兩千年來中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若從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釋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國時,士人總是“回向原典”去尋找變的思想資源。到西潮大盛后,才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后立的所謂“超越進步觀”,與傳統徹底決裂。費正清等若沿此取向研究,本可證明西潮的沖擊對中國的影響實超出一般的認知。柯文等若依照這一真正中國式的“在傳統范圍中變”的取向,本來也可見到費正清等所不曾見之處。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處恐怕多年也是秉承超越進步觀的,所以將前一輩破得太厲害,無意中將其好處也破掉了。
林
林著變而后大的一個特點即在其熔古代近現代為一爐。美國的漢學,古代和近代幾乎是兩個不同的學派。前者相對更重史實,后者則偏重詮釋。古代史學者通常更多或更易于接受一些中國的觀念和認識方式,近代史學者則更多以西方的觀念模式來認識中國。這當然只是言其大處,古代史學者中自不乏以希臘羅馬中世紀模式套中國者,近十多年許多近現代史學者也日漸主張應以中國為中心,更有人明言應學習古代史的學風。但直至今日,兩造在學風上的差異仍十分明顯。例如柯文就曾指出費正清等編著的《東亞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風格上有時自相矛盾,就是雙方學風相異的顯例。林
林著能“變而后大”,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林氏突破常規的取向。林氏對人們視之為當然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觀念均不輕易接受,而是批判地印證。的確,這是一部對西方流行的“中國世界觀”概念進行挑戰的力作。依以前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國的歷史發展是一個邊界清楚和文化內凝的連續進程,即以長城為屏障分夷夏,華夏族在關內基本不受打擾地自在發展。而中國的對外關系,亦在文化決定論的夷夏觀的影響下維持連續和穩定。林氏以為這些觀念或多或少都有問題。而其根本性的挑戰,則在于破除傳統的文化決定論。林氏指出,中國幾千年發展中的變與不變、勝敗長短并非全由文化決定,而常是特定時代的具體政治風云或政策爭論的結果。具體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來,不僅給中原政權造成軍事政治困擾,同時更觸及到中國的名份認定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換言之,“中國”首先是一種文明呢?還是一個國家?是國家,則種族和地域的界定均甚要緊。是文明,則不必以種族地域分夷夏。如是則以修筑城墻來隔斷某些民族和地域,從根本上是與中國文化中的天下(Cosmopolitan)傾向背道而馳的。這樣一個名份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漸成道義問題,感情成分甚重,而且從未被確切地回答過。
實際上,從先秦起就有筑墻拒北方游牧民族之舉,歷代筑墻者亦不少見。但長城在軍事上從一開始就并未起到屏障作用。今日所見的長城,主要是明代修筑的,就不曾能阻擋滿人南下。清初幾位皇帝的“御制”詩中,常有挖苦長城無用的句子。長城既無作用,各朝代仍須自己重新界定其北疆,界定時也并無一條固定的界線為依據。所以中國北疆的走向歷代始終不定,有時廣袤而開放,北向甚遠。由于包括各族住民,其時對中國概念(Chinese-ness)的界定即趨天下的傾向,文化也并不內凝;有時則窄而關閉,疆域約僅包括農耕的漢族或更小,此時對中國概念的界定則采民族的傾向,夷夏之分遂清。故長城的修筑與否,并非僅在文化決定論的夷夏觀影響之下。各朝或修或不修。即使在修筑長城的那些朝代,比如林
林氏認為,某些舉措之所以不能被采用,常常也并非依其本身的功效利弊而定,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帝王與士大夫之間的權力之爭。這樣的爭奪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即宮府之爭,一般又稱為“道”與“勢”之爭或道統與治統之爭。其由來既久,而且從無制度上的根本解決。一般而言,帝王將中國視為朝代的,將政治視為血統的。而士大夫則將中國視為文化的,將政治視為道德的。這部分是因為晚周“禮崩樂壞”之后,貴族式微。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以教育的尊貴來代替血統的尊貴,最后完善成科舉制度。故特別增強了士人強調文化教育重要性的傾向。更重要的是,士人與帝王之爭,在某種程度上不啻是口與手之爭。士人要爭取的理想境界是君子動口不動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給“中國”一個獨立于朝代之外的客觀文化界定,強調道義為政治的基礎。由于強調文化區分,其中國概念是民族取向的。但是口終斗不過手。中國歷代思想意識活躍皆在亂世,幾乎已成常態,便是口斗不過手的明證。故帝王強大時,以其個人力量和血統為統治依據,對中國概念的界定則是天下取向的,對外族問題也更容易靈活處置。不過口雖斗不過手,手也終不能征服口,實際上也離不開口。結果是雙方又斗爭又協作兩者并存。林氏以為這種對中國概念的文化界定和朝代界定的并存,恐怕正是中國得以長久持續統一的一個重要因素。
蓋士人強調道義為政治之基礎的好處即在于其可在帝王強大時借道義為依據批評帝王,而在帝王太弱時又可借道義為凝聚社會的基礎。但文化界定的寬嚴失度頗易造成政策沖突無法解決。以邊界為例,在帝王看,其所控制的便是領土。從文化看,就有必要采用一種具有超越約束力的夷夏區分。結果是對外政策實際上處于政治內爭的影響之下。官僚間的政爭和政策之爭,通常也被道德化。而道德判斷一引入政爭,妥協即不可能。蓋爭斗的雙方必不斷提高政爭的價碼,以在“道義”上壓倒對方。故在對外政策上要接受“化外”民族為平等或與其妥協,實在難上加難。于是貶和平為出賣,以高不可攀的理想為實用措施的對立面,通常都能使重實效的政策失去立足點。故林
不僅如此,長城在中國歷史上也絕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從漢代起,長城在中國的上層和民間文化中,都是與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關聯的負面象征。從賈誼的《過秦論》,到漢樂府詩以及民間的孟姜女傳說,無不如此。明代筑城,為趨避此惡名,乃呼為邊墻。直到八十年代中,明長城下的農民仍稱此長城為“老邊”。也是在明代,長城漸為歐人游記所提及。初尚平實,所說長城的長度不過幾百英里。到明長城完工后,歐人記述的長城尺度日漲,并漸附會為早年的秦長城,更增加其神秘性和吸引力。到十八世紀,西方許多關于中國的“迷思”在歐洲形成,長城亦然。其中啟蒙主義大師伏爾泰居功甚偉,英人則首推那位不向乾隆皇帝磕頭的特使馬爾戛尼。從這時起,長城漸被捧為人類奇跡。到十九世紀,近海濱一帶老龍頭嘉峪關一帶的明長城,已成旅華洋客常去的“秦長城”勝地了。
通俗文化聲勢一大,也要影響精英文化。約在此時,西人的歷史理論中也漸將長城引入,多少或與西方傳說中的亞歷山大墻附會,關于長城使匈奴不再南下,遂北向而使羅馬覆滅的說法漸成通論。到十九世紀末,現在流行的關于長城的觀念已完全樹立。并開始引起想象。唯一能從太空看到的人類創造物的說法即源于此時,到二十世紀初已廣為西人所接受,在各種讀物中常可見到。
隨著西學東漸,這些有關長城觀念又回到中國的懷抱。一九一八年,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盡采西人成說,視長城為中國最偉大的工程,并授孔子贊管仲意表揚長城說:“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秦漢之時代矣。”孫氏雖授西說,實抓住了當時中國的需要。蓋民國雖然代清,因傳統帝國崩潰而在中國文化中心造成的空白卻未被填補。對中國這樣一個依靠統一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秩序來維系凝聚力的國家,將長城轉化為一個正面象征,正適應了這一需要。長城形象在中國的時運就此逆轉。
但這轉變是緩慢而不完全的。新文化運動中人便不似孫中山這樣積極地看待長城。魯迅曾一言以蔽之:所謂長城,
其實,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現在不過是一種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或者還要保存它。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魯迅所見的“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分明都非褒意,其中自有言外不盡之深意,但其表達的新文化運動諸人對長城的負面看法是明顯的。實際上,如果說長城在軍事上從未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其“將人們包圍”的功用恐怕也沒有新文化運動諸人想象的那么厲害。
林
而傳統的文化中國與民族中國的概念界說仍是不清晰的。中國既已成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員,自必采西洋近代民族國家的界說。但在思想上,文化中國仍有生命力。美國的杜維明教授便正在提倡一種“文化中國”說。不過杜氏的“文化中國”在疆界上是天下取向的,在種族上恰是民族取向的,這與歷史上的文化中國已大不相同。林
ArthurWaldron,TheGreatWallofChina:FromHistorytoMyth,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