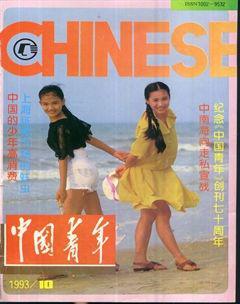官場中的“哥們兒情結”
侯松峰
我常覺奇怪的是,一些身負重任的官員,身心深處竟也縈繞著一股股剪不斷的“哥們兒情結”。其情切切,絕不亞于江湖者流。
一日,我去某大機關辦事,見要拜會的那位正在打電話,我便立在一邊耐心等候。不意,他竟笑容可掏地向對方冒出這么句掏心窩子的話:“咱們哥們誰和誰呀,這點事,沒說的!”
還有一次,某大企業舉辦了一個青年干部培訓班,班上那些前程遠大的生力軍們,竟也敘起了年齒,排上了座次:張三大哥,李四二哥,王五三哥……就這么依年齡大小排將下去,而且還訂立了哥們兒協定:日后誰先被提升,就要請弟兄們撮一頓。據說,后來還真就做到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如此這般。局外人如我等,恐怕也就只能作如是想:任何一種語言現象都無不和一種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如今的人整天所思所想都是各自左右圓通、名利兼得的大事情,有的,將“世路難行錢作馬,愁城欲破酒為軍”視為“處世真言”;有的,動員起七大姑八大姨,將拉關系走后門當作發達捷徑……所以官場中的“哥們兒情結”剪之不斷、揮之不去,實在也是有理有據的。試想,當今商品經濟大潮風起云涌,官而為商,已是尋常之事。如果不在為官時多認些哥哥兄弟,怎能保證自己將來在商海中一舉成功?因而,“茍富貴勿相忘”的信誓旦旦,許愿升遷或發達之時一定會“拉兄弟一把”,當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人說,渴望友情,乃人之常情。當官的也是人,大事小情彼此幫忙,理所當然。“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是人際關系友善的準則嘛!這么說當然不錯,但遺憾的是,“哥們兒情結”卻常常鬧到和黨紀國法水火不容的地步,“如之奈何”?
《黨風月報》曾載有《“囚星”奇聞》一文,披露的是,某縣工商局長因貪污受賄1.4萬元被依法逮捕。可在監獄的半年時間里,他竟出監54次,在看守所值班室向外掛電話162次,并有46人77次前來探望(這些人當然都是平日里迎來送往、有求必應的哥們兒),稱其為“囚星”,也算得上名副其實了。某日,該“囚星”讓前來探監的哥們兒捎出一張便條,命其轉給縣藥械公司黨支部書記王密(王系“囚星”受賄2000元的證人)。便條上寫道:“王老兄你好,在88年查處羊毛案件時,你到我家去過兩三趟,交給我1000元錢,我都沒要,你在(再)好好想想。”不久,這個王哥們兒就為其大搞翻案,真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這則事實確鑿的報道很能讓人看出些“哥們兒情結”的妙用和“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大家都握有一定權力的情況下,一句“哥們兒”,就可以頓時縮短彼此的心理距離。再佐以互施“滴水之恩”,共圖“涌泉相報”,或謀權,或取利,于是,各自的一畝三分田里便不間斷地呈現出一派其樂融融的豐收景象——皆大歡喜。
然而,黨紀呢?國法呢?損公肥私,是要受到懲處和制裁的,這一點,常人都明白。也許“哥們兒”們委實是心無旁務、顧及不了其他了?
竊以為,既已為官,首先就該“三省吾身”,所思所想俱應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準則;若整天只為個人私利,深陷于哥們兒情結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蠅營狗茍,干些為黨紀國法所不容的監守自盜的勾當,難免有朝一日淪為兔子尾巴長不了的“囚星”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