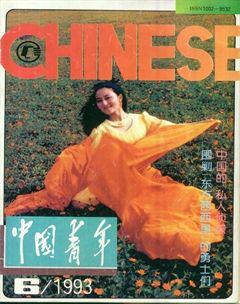譯制導演是干什么的
王文和
歷來,電影觀眾大都熟悉電影演員,對于影迷來說,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出一大串影星的名字,甚至可以津津樂道影星們的脾氣秉性等等。本來嘛,演員畢竟是直接接觸觀眾的。
隨著大眾電影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們已不再停留于此。現在,他們不僅熟悉《芙蓉鎮》中的姜文、劉曉慶,而且熟悉影片的導演謝晉;不僅熟悉《過年》中的趙麗蓉、丁嘉莉和李寶田,而且熟悉影片的導演黃健中;不僅熟悉《邊走邊唱》中的許晴,而且熟悉導演陳凱歌;不僅熟悉鞏俐,而且熟悉《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片的導演張藝謀……
然而,對于外國譯制片,人們可以說出很多自己熟悉和喜愛的配音演員,卻還很少有人熟悉,甚至很少有人了解譯制導演,不知譯制導演是干什么的。
在人們的常識里,一提到譯制片,首先想到的是配音,一提配音,首先想到的是對口型,卻怎么也想不起有譯制導演的什么事,大概不過是位盯著配音演員對準口型的人。不錯,在配音的過程中,譯制導演確實自始至終守在錄音棚里,兩耳傾聽,雙眼圓睜,目不轉睛地盯著畫面,注意配音演員的說話是否與畫面人物的開口、閉口和中間的停頓相吻合。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因為作為一個比較熟練的配音演員,都能順利達到這一點,譯制導演對此也無需花費多少氣力。在配音現場,譯制導演的精力更多地還在于把握配音演員對劇中人物性格、情緒的恰如其分的表現。這種把握也并非止于配音現場對配音演員的誘導和啟發。其實,在此之前,譯制導演已經做了大量的創作準備,可以說,這種準備并不比拍攝原片的導演輕松多少。首先,譯制導演在接受譯制劇本后,要對照原片反復研究,力求準確理解和把握影片中各種人物的性格和內心世界,作好充分的案頭工作。比如要像影片導演寫分鏡頭劇本一樣,也要寫出配音分鏡頭,有的細到給每個人物的語言標好停頓或換氣的氣口。其次,譯制導演要依據配音演員聲音的音色、音高、音域和聲音的靈活性、可塑性,比照原劇中人物語言個性特色,進行慎之又慎的選擇。配音演員確定后,譯制導演要帶領他們,連同錄音師一起反復觀片,認真分析劇本,進行大量多次的排演,最后才是配音實錄。
雖然,播放時,是配音演員的聲者直接訴諸觀眾的聽覺,但是配得好不好是不能僅僅歸功或怪罪于配音演員的,在相當程度上,是與譯制導演的才華高低相聯系的。因為只有譯制導演才有權對配者、配樂的藝術效果做最后裁決。例如,美國電影《巴頓將軍》有這樣一場戲:巴頓將軍正在床上休息,忽然有人進屋向他報告敵軍已經進攻,巴頓將軍起身詢問,譯過來的片子把巴頓的問話說得很急促驚響。再看原片,巴頓的這兩句話卻說得輕描淡寫。顯然前者表現出一種驚惶,后者表現出一種沉著,兩相徑庭,不言而喻,譯制片違背了原片的含義。與其說這是配音演員理解的失誤,倒毋寧說是譯制導演把握的疏忽,使得巴頓將軍失去了被譽為“軍神”的那種大將風度。
應該說,是譯制導演引導、啟發配音演員從原片演員的表演中尋找出人物的心理活動,體驗到人物的精神世界,然后用準確的語言,藝術地再現片中人物的神韻色彩,而不是照本宣科機械地依靠聲調高低和節奏快慢的簡單模仿來完成。毫無疑問,這是譯制導演與配音演員共同完成的一種藝術創作。有人說譯制片不是創作,理由就是譯制片要忠于原片,所謂配音對白不過是原片對白的拷貝。
這是一種誤解。忠于原片,顯然不僅僅表現在人物的對白上。確切地說譯制導演不僅是聽覺、對口型和對白技巧的行家,還應該是一個技術高明的錄音師,他還要將配音演員的對白,與原片的環境音、背景音動效等進行有機的混錄,遺憾的是我們的觀眾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物對白上,而忽視了對其他音響的感受,就是有些譯制導演在這方面也顯示出功力與修養的不足,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表現工廠噪聲損害工人健康的外國片,女主人公和同事在車間談話,環境聲原來是突出的,可這里卻被壓得低低的,人物談話被推到最前面,使對白清楚可聞。女主人公轉身問其身邊的母親,而母親因機器嗓聲早已雙耳失聰,根本沒有聽見。譯制片做如此處理,顯然又背離了原片的含義。譯制導演在最后的聲音合成上,不加分析堅持了只圖讓人們聽清對白的陳腐觀念。其實,此時人物的那些不關痛癢的寒喧之語有什么非聽不可的必要呢!倘若此時將環境嗓聲提高,豈不正吻合影片的主題?豈不是最準確的藝術表達?
美國影片《愛情的故事》對愛情的音樂主題使用別具一格。它既不出現在情節的關鍵處,也不出現在情緒的高潮處。就是在女主人公臨終前,甚至死去時音樂都沒大作,而是將大量疊畫不斷刺激視覺。直到男主人公回到影片開頭他所坐的那個溜冰場的看臺上時,音樂才如山洪宣泄,盡情抒發,給人留下無窮的回味。譯制導演倘若忽視這種獨特的藝術處理,而隨意按照國內影片的俗套,電閃雷鳴,海潮奔涌,音樂狂起,就會將一部藝術經典糟蹋得不成樣子。好在這部片子譯制導演把握得很有分寸感,大膽地再現了這種獨特的藝術,使觀眾獲得耳目一新的感受。故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譯制導演的水平決定了譯制片的譯制水平。
從1948年起譯制原蘇聯影片《普通一兵》到現在,我國譯制外國片已有了40多年的歷史,其中不乏優秀之作,不乏優秀的譯制導演。袁乃晨、陳敘一、胡慶漢、時漢威、林白、莊焰、李景超、伍經緯、孫渝烽、肖南、陳汝斌、衛禹平、蘇秀、畢克、楊成純、喬榛、曹雷等等,譯制導演層出不窮。其中很多人既是導演,又是優秀的配音演員。
隨著電影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譯制導演必將全面提高整體聽覺藝術的表現力,觀眾也將不再僅僅滿足配音演員的精彩對白。他們必將對譯制片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也就更加寄希望于我們的譯制導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