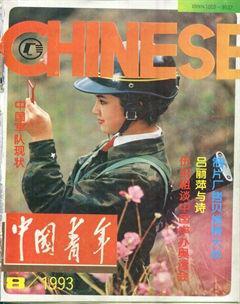單人旅行
劉湛秋
少年的一雙稚氣的眼睛,永遠在窗外,在某個遙遠的地方。
是的,托著腮,想什么呢?
在書本中尋找幻想,在幻想中尋找自己。
外面的世界會怎樣呢?一種想離開原地的感覺總是在攫著你。
這時候,旅行開始散發出特別的誘惑。哪怕是一次短暫的郊游,一次隨意的遠足,也能使心靈多少有些新的寄托。
少年的我最憧憬的事莫過于旅行了。如果說大多數人情竇初開想的是異性,而我當時卻更傾情于旅游。
離開熟悉的房子、街道,離開親密的人和門前的一棵老桑樹,進入另一些大路或小路,穿行于不熟悉的景色之中,與一些陌生的人擦肩而過或同車對坐相視,總是那么美好。這種異地的新鮮感使我眼睛明亮,呼吸暢快而又急促,整個身心像一塊干干的海綿,吮吸著環境的水份。
當然,旅行遠不是少年的專利,只是少年更容易為好奇心所驅使罷了。也許,隨著年歲的增長,旅行會因你的成熟而帶來更多的愉快。
眼下,在西方世界,老年人的旅行更成為一種時尚。君不見北京旅游團的大巴士中坐的大多數是老年人嗎?在金色的時光,更有充裕的閑暇來觀覽他大半生未見過或想再見的地域,或者只是作為一種休息方式,頤養天年,排遣最后的人生。
唉,離開旅行,人生會是多么的乏味啊!
人不是一棵樹,人不能永遠呆在一個地方。
無論什么方式的旅行,無論長短時間的旅行,都是美麗的。
對我來說,更習慣或者更喜歡的是單人旅行。
你悄悄地收拾好行裝,你趕赴火車站,你默默地排在隊伍中,你不必擔心會把誰丟掉,除了丟掉你自己。
在車廂里,你可以默默地看書,或看窗外永遠也看不完的風景。你忽然想說幾句話了,恰巧,對坐的旅伴也投來友善的目光,于是你們互相都贈與新鮮。真的,不知道對方姓名的交談是最愜意的。怎么開始,怎么結束,都無所謂。
你獨身在異地漫步,你愿意多停留一會,沒有誰不高興,你想匆匆趕路,也沒有等待別人趕上來的義務。你喜歡買書,那么你去逛書店,你想喝啤酒,那就隨意找個小飯館去喝吧!
你清醒地知道,你是在單人旅行。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一個人去完成。甚至你去上一次廁所,也要考慮如何處置你的手提包或別的什么物件。
只有單人旅行時,你的思維才是你自己的,你的五官才是不受干擾的全方位開放,你才能吸收外界傳來的所有信息。否則,那電波就是模糊的,時斷時續的。
我有這樣的經驗,如果作為詩人或其他旅行團什么的,全程接待,那么,每個城市都是模糊的,因為那不是你自己走,而是別人抱著走,背著走,你像一個嬰孩那樣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你被安排著觀賞一個個景點,你的生活也全包了。以至你以后如果單人再來這個城市,你依然一無所知,不知道該怎么坐車。你來過,好像又沒來過。很倒霉,失去了新鮮感,卻依然陌生。
從旅行的本意來考察,單人旅行才能回歸到那種個人和外界的膠著狀態。你和某個農村或城市的關系,你和大自然的關系,能最直接的交流,沒有任何的中介。這樣,一切都經過你頭腦的篩選和儲存。顯然,這種記憶會深刻、連續而富有立體感。
美國影片《鴿子號》講一個青年單人環球旅行的故事,這個青年人中途認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而且墮入愛河。幾次他想讓這姑娘上船共同作環球旅行,但是這樣他就毀了原來的協議。最終,他只能不情愿地選擇了單人旅行。我想,撇開這一層的毅力、勇氣、冒險精神不談,如果他和這姑娘在一條船上旅行,那么,他的記憶中留下更多的恐怕是愛情,而不是大海的風暴,逼人的陽光以及變幻的日夜了。
是不是呢?正如“蜜月旅行”,重要的肯定是卿卿我我的“蜜月”,而“旅行”只是某種背景音樂吧!
真正有幾次認真的單人旅行,對學習人生、了解人生像鹽對身體一樣不可缺少。我想,高爾基的《俄羅斯浪游》、艾蕪的“滇緬漂泊”決定了他們的文學生涯。當然,不是從事文學的青年也一樣需要單人旅行的經歷。這是學習生活的學校,是訓練自己獨立能力的課堂。在單人旅行中,你原有的弱點會暴露無遺,你會發現,你的生活能力有多么薄弱。
可惜的是,由于社會的習俗及安全的原因,男青年單人旅行很容易,而女孩子一個人就不那么方便了,雖然也不是絕對的。不過,走不了就不走吧,有一點美麗的遺憾也是很好嘛!
人的一生雖然短暫,卻也相對地漫長。對許多人來說,各種旅行機會也很多,商業旅行,公務旅行,會議旅行,部門的休假旅行,結伙或不結伙的,等等。旅行也變得越來越快捷簡便,不是“千里江陵一日還”,而是“萬里江山一日游”了。有的人幾乎已疲于旅行了:一上飛機火車就睡,一下飛機火車就匆匆辦事,完全是易地辦公,而不是旅游。
唉,如果我們到過成百上千個地方,卻又沒有一次進入旅行的真諦,多多少少是有些愧對人生了。
我很慶幸我一直保有敢于單人旅行喜歡浪游的性情。在我看來,外面的世界也許無奈,外面的世界卻永遠可愛。就在幾年前,我還想騎自行車作幾個城市的單人旅行呢!也曾被好心的人勸阻過,其實因為沒找到空閑也沒有實現。但這個愿望也許在我身體尚好的時候會嘗試一下的。
少年時就立志浪跡天涯。我不需要旅伴,不需要導游,不需要全程的陪同。去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因為我活在這世界上,我總要尋找我和世界更多的交匯點。正如我在一首詩中所寫:
永遠在旅途中
不追求任何的目的
這就是我終生的目的
“該出發了!”——好像這是我命中的門鈴,又輕輕地響了幾下。
于是,我離開了原來的屋子。
1993年5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