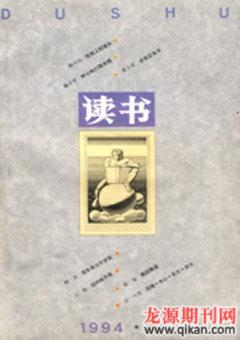智慧的痛苦
蘇東斌
近十多年來,每次踏進史家胡同去拜訪于光遠先生,幾乎總是要首先傾聽他滔滔不絕地講演著自己最近又在研究著什么,對馬克思的什么提法有什么新的認識等等。諸如,“社會共產主義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對稱”,“社會的社會主義是共產的社會主義更高階段”……這其間,又幾乎使你插不上話,逼得你又不得不跟著他一起去追尋與體味。常常是在差不多上了這樣一堂課后,才能再來問你到達的目的與要求。面對這位年近八十老人的這種風格,使你不得不承認,如他自己印制的圖章中借用來的一句話所描繪的那樣“是一位死不改悔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看得出,他的精神有時充滿了痛苦,但那是一種智慧的痛苦。這一方面來自他本人對嶄新學術領域探索的艱難過程,另一方面又來自學術與政治或其它的爭鳴和抗進。
讀他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首先反映的當然也就是他在理論風云中的苦難歷程。近十年來,他發起了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對按勞分配的研究,對生產力經濟學的創立、對個人所有制的肯定、對市場經濟主體論的確認……足以證明他正是以經濟學大家的姿態,面對一個“大視野”去創造一些“大概念”。
以“社會所有制”這一概念為例。在社會主義社會,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到底應當建立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
光遠先生認為,“社會共產主義”的基本含義是:這種共產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其所有制的基本性質是“社會所有制”。在這種共產主義社會中,實行社會主義原則。顯然,光遠先生是把“社會共產主義”當做一種社會制度,一個歷史階段來研究了,于是,“社會所有制”也構成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
我以為,在這里,他抓住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三個論點:
第一、反復考證“社會所有制”概念的來源。
他查閱了《資本論》、《反杜林論》的德文原本、英譯本、俄譯本,清楚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公有制和社會所有制這兩個詞在使用時是有嚴格區分的。凡是在講“一般”,在講原始社會的所有制時,在講共產主義社會是古代原始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時,都用“公有制”來說明,而在講生產社會化了的私有制后的共產主義社會時,都用“社會所有制”來說明。我國在翻譯他們的著作時,對這兩個詞都譯成“公有制”,并未加以區別,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本人則是嚴格加以區別的。
第二、特別強調“社會所有制”概念的特點。
因為馬克思的結論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也就是承認個人對財產有了所有權。
第三、高度重視“社會所有制”概念的形式。
因為馬克思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浸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企業。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一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近百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股份制度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典型企業制度形式了。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勞動者已經不再是“無產者”了,而是本來意義上的“有產者”、“資產者”了,否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人地位就被架空,也無法說明誰是社會財產的真正主人,社會主義革命也就失去了勝利的標志了,所以,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正是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勞者有其股”。
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并未沿著這一理論思路走下去。
第一、重建在社會所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應由三部分組成:其一是屬于整個社會占有,而每個公民都等量平均所有的公共財產,如公園、公路等社會財產。其二是屬于共同體中每個成員不等量的財產,如股份公司中張三股份和李四股份。其三是游離于社會所有制之外的私人所有,如我們常說的私有經濟制度。顯然馬克思沒有提及第三種狀態的個人所有制,甚至認為它是完全應該被消滅的對象。
第二、在未來社會流通中,既然承認了個人所有制,那么交換的內容就不僅有勞動量,而且還會有資本量。但由于在第一種狀態下的財產關系是等量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交換的計算了。顯然馬克思忽略了第二種形態的個人所有制也需要進行資本交換的計算了。
第三、馬克思忽視了個人所有權實現的部分內容。他認為這種個人所有權僅僅在第一種狀態下才有實現的方式,即一方面可以通過社會公共福利按需分配,另一方面主要則可以通過按勞分配去實現。從而否定了第二種、第三種財產狀態也需要實現其所有權,即還要實行按資分配的必要性。
第四、只要進行勞動產品的交換、又要承認不同的個人所有權存在,就必然要把交換的內容還原于抽象勞動——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價值——價格。這就是說,在社會所有制的表層關系下仍然是一種最終歸屬個人的個人所有制,那么個人所有權的實現,即收益權和買賣權,也就順理成章還要發生商品貨幣關系。馬克思在這里的失誤不僅在于它忽略了個人所有制實現的另外兩項內容,而且也否認了商品貨幣關系仍然是實現個人所有制的唯一形式。
當然,在這時,光遠先生總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苛求于作為科學家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第一,早在一八九一年,根據當時股份公司的發展情況,恩格斯就說,資本主義的私人生產“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例外了”。我理解,就是私有經濟即使在那時已經不占統治地位,不是典型形式了,更何況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就更不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了;第二,馬克思為了避免陷入空想,總是對未來只做“一般”的預測,不做細節說明,既然私有經濟不占主要地位,也就可以抽象不計了。那么,他又是如何研究社會所有制的運行規則呢?他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上有一個三個發展階段的認識過程。首先是“排斥論”,其次是“結合論”,最后是“主體論”,認為兩者不再是兩種東西相并列,社會主義經濟的有計劃發展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計劃發展,市場經濟就是有計劃發展的主體。在此他斷言,股份制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所有制形式。
自然,這里就發生了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市場經濟到底需不需要有一個經濟基礎問題?
顯然,計劃經濟體制的實現是建立在經濟國有化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對待國有企業,各級政府才有權下達指令性指標。
市場經濟要求由市場價格來配置資源,而價格不過是不同所有權的交換條件。所以,商品交換,一定要發生不同的所有制關系之間,就是說,“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就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如果,只靠采取市場經濟的運行方法、種種手段,如使用稅率、利率、價格等進行經濟調節,那么,最多只不過是模擬市場經濟,不可能真正進入市場運行。
無論是從歷史上還是從邏輯上看,都證明了馬克思創始人關于同一所有制下不可能有商品經濟結論的正確性,在同一所有制內部不需要進行等價交換。因為: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第一種形態的全民等量所有的社會財產不需要進行交換價值的計算。而一旦發生交換世界上國有企業大體都虧損就是一個明證。人們在家庭內部為什么吃飯不要錢?就是因為都同屬于一個所有者,不需要核算與交換,只需要按需分配、需要吃多少就吃多少。馬克思的商品、貨幣、市場關系就是只能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礎上的。
第二,私有制(指第三種狀態的個人財產),與現代市場經濟在總體上也不能完全結合,雖然它有一定的適應性,但畢竟要產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而會引起社會動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這也是他論證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原因之一。所以國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結論并不能導致經濟完全私有化過程歷史趨勢。連資本主義在當代都把私有經濟看成一種例外,那么社會主義就更不會去發展全部私有化方向了。
第三,應當注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一句話,即如果資產階級不對他的全部經濟關系、社會關系進行根本的革命性改造,那么他一天也維持不下去了。到底是什么使資本主義的喪鐘尚未敲響,使資本主義制度從總體來講不僅沒有滅亡,而且還有巨大發展呢?就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明顯標志就是股份制取代了純粹的私有制。從而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弱化與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從這個意義講,是股份制挽救了古典資本主義。
第四,只有第二種財產狀態才能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典型形式。股份經濟是一種非私有經濟、是合作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共有制經濟,是社會所有制的主要具體形式。正是這種形式要求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確保了社會所有制中個人所有權的實現,所以才能進入市場,才是真正的商品經濟。面對中國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近三分之二虧損的狀況,只有采取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公司制,才會在產權與經營兩個機制而不是一個機制上得到根本性的改革。由于股份制能夠把財產的公有制的理想形式——社會所有制與商品生產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相結合起來,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股份制肯定會挽救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
兩種社會制度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趨同形勢更加說明股份制是人類社會化大生產,是經濟現代化的產物。
這里的結論是:必須塑造起市場經濟的基礎與主體,即建立等價交換、自負盈虧的企業來。國有經濟只能“國負盈虧”,所謂“國有民營”,無論是租賃制,還是承包制,都解決不了資產虧損這個問題,“國有民營”決不是中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只有改革國有制本身,把它變成混合經濟才行。如果把國有制分解為條條塊塊再加上不同的國有企業組成的百分之百的國家股的股份制也不行,因為只有“分散而明確”的所有權才能建立起自負盈虧的約束,只有當所有者(股東)與經營者(經理)兩種身份有不同的經濟目標時(一個追求資本升值,一個追求收入增加)不再同時是國家雇員時,才能形成相互監督約束機制。
總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中,只搞經營機制,運行機制不行,必須同時搞產權機制,所有制關系的改革。
那么,對于那種不占統治地位,不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形式的第三種個人所有制狀態,即被稱為“一種例外”的私有經濟存在的根據到底又是什么呢?本書作者特別重視毛澤東的一段話,即一九五六年初講的,只要社會有需要,可以開私營大廠,華僑投資一百年不沒收,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些資本主義。
那么,私有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什么呢?我們認為只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需求去探索。首先,如果我們承認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社會發展最基本動力,如果我們承認對生活資料的占有是這種利益實現的標志,那么就應當承認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正是獲得生活資料的手段之一。可以斷言,人類社會第一人權就是經濟生存發展權,而第一經濟權就是財產權,第一財產權又是投資權。所以,從主觀上講,發展私有經濟是個人的經濟需要,因為人類社會都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所以完全消滅了私有經濟,也就消滅了人類本身。其次,由于社會需求的豐富性、變化性,私有經濟、小規模經濟,只要銷售社會化,也就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全世界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一家小廠的商品甚至可以打入全世界就是一個明證。社會化大生產流通過程和經濟國有化沒有必然聯系。所以,從客觀上講,發展私有經濟也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要求。
至于倫理學上講的“剝削”,只能理解為“超經濟掠奪”,而不應是“資本收益”,否則為什么人們在接收儲蓄利息,股份分紅時絲毫沒有剝削別人的感覺呢!“勞動價值論”是講價值的創造必須通過勞動,而不能否定“價值共創說”本身,如果投資沒有收益,誰還去積累呢?
當然純粹私有經濟是與社會化大生產有深刻矛盾的,其一是資本規模狹小,其二是經營素質局限。所以它不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我們以為,這里有一個三部曲。一九八四年,“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確立,標志著承認商品等價交換關系,從而承認了除按勞分配以外的按資分配,這樣就在實際上否定了只有按勞分配一種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征的說法;一九九二年小平的南巡講話,在實際上又否定了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的說法;一九九三年,中國的改革家們所倡導的對國有制改革,就在實際上否定了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唯一基礎特征的說法,因為不僅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公有制與國有制,而且幾乎國有經濟沒有幾家辦得盈利。國有經濟遲早要退出商品競爭領域而走向非盈利的公益事業。
我們引申出這些理論問題,是為了說明:僅從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所有制”這一概念艱辛探索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改革的拓荒者是怎樣在馬克思所開辟的土地上向前耕耘。我們確信,這既是生命的記錄,又是終極關懷。在這里,既有智慧痛苦折磨,又有智慧結晶的歡悅。這當然也足以反映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命運。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于光遠著,人民出版社版,卷一3.85元,卷二4.25元,卷三6.25元,卷四8.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