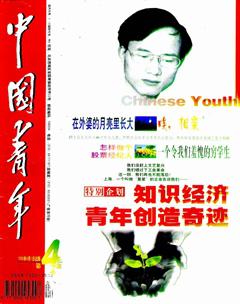愛情無定式
可可
那一年,我22歲,大學畢業后進了民航,這是一份不少人羨慕的好職業。然而,一年前父親的突然去世引發的失眠癥因了陌生的環境更加肆虐地折磨我,在5月的雨季來臨時,我已虛弱得不堪一擊。皓及時察覺了我灑脫快樂的外表下泛濫的憂郁,人前人后很自然地關心著我。他是我的上司,并且已婚,我為他的真誠感動,放心地做了他的小妹。
在接下來的某個秋涼如水的月夜,皓陪我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我的眼淚忍不住碎在晃動的杯中。皓握了我的手,輕嘆一聲:“什么時候你才會快樂起來?”霎時我的淚洶涌而出,打濕了原本朗朗的夜。皓默默地擁著我坐了一夜。那一晚,我22歲的生命第二次體驗到刻骨銘心的絕望。第一次是驚悉父親病逝的時候,這一次,我今生最渴望的依靠卻不屬于我,絕望隨著我的淚水不絕地流淌在漆黑的夜里。
為了對付長長的無助的夜里蝕骨的相思,我學會了抽煙,常常縮在沙發中一根接一根地燃著,明明滅滅的煙頭將我的心烙得千瘡百孔。不可饒恕的是,皓和我最終都丟盔棄甲做了感情的俘虜。朋友們都說我越來越漂亮,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在加速消耗。我沒有勇氣去判斷這份感情的是非,也不想以破壞一個家庭來成全自己最初的錯誤,于是很多次想遠走高飛,可是又怕母親受不住再一次的打擊。皓也明顯地消瘦下來,我觸摸得到他受煎熬的靈魂的痛楚。
再一個夏天來臨時,從鏡中憔悴的面容上我驚覺,愛情實在太嬌貴,這朵沒有明天,見不得陽光的愛之花注定會枯萎的。又一晚,我把自己關在房里,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把所有的淚都流光了之后,我感到一種虛脫的疲憊。愛情是什么?是一把鈍鈍的刀,千刀萬剮之后才有錐心的疼痛?抑或是一柄帶毒的利箭,穿身而過時已注定無藥可救?
盡管每晚都需要安眠藥來伴我入睡,但人前的我必須是健康而快樂的。下班后常常與一大幫同事狂熱地去跳的士高,逛一天的馬路,泡啤酒屋。皮是我的鐵哥們兒,高大英俊,且善解人意,是極好的玩伴。夜深時,常常是他送完女朋友再送我回家。有天皮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與女朋友吹了,我只覺得他是個貪玩的大男孩,便像老姐姐似地送了他一大堆愛情箴言。皮不置可否地笑笑。
夏末的一個黃昏,與皮和幾個朋友去俱樂部游完泳之后又去喝啤酒,可能是累了,我覺得有些醉。皮牽了我的手找出租車送我回家。一時間,那些冰凍的記憶悄悄地復蘇,我的心痛了又痛。皮侍候我在沙發上躺下之后,卻依舊蹲在地上,他靜靜地看著我,收斂了往日的調侃與張揚,澀澀地說:“嫁給我好嗎?我們忘記彼此的過去,重新開始,好不好?好不好?”我驚愕之下,酒也醒了,難看地笑著:“不要開這種玩笑。”皮卻搖搖頭,他突然哭得像個孩子一樣,一邊哭一邊說:“我不想乘人之危,但因我的怯懦,我曾錯過你,這一次,我不想再錯過。”皮說,他在暗中關注了我兩年,知道我所有的故事,他問過自己好幾遍,羅列了許多不應愛我的理由,卻發現無法說服自己。皮抬著一張淚水縱橫的臉,極認真地:“我會是一個很好的丈夫,給我,給你自己一個機會,好嗎?”我從未見過如此愛哭的男孩,無法狠心地拒絕他的請求。
我與皮舉行了婚禮。過了沒多久,我的失眠癥不治而愈,我發現我愛上了皮,并開始努力學做一個好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