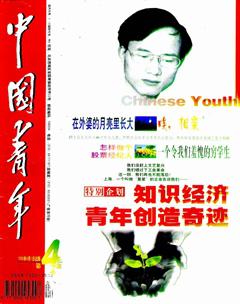今天,我們還能“消化”保爾嗎?
趙彩婧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南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yè)——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正面是戈多,反面是科諾克!”
“當啷”—是正面。就職于北京某部委機關的23歲的沈蔚就這樣決定了當晚的安排—去看話劇《等待戈多》。
這個春天北京的演出市場實在太熱鬧,以至鄭蔚要拋硬幣決定取舍。但同期上演的另一部話劇《保爾·柯察金》卻被她沒怎么猶豫就冷落一旁了。“哦,聽說有這個戲。保爾,是不是離我們太遠了?硬邦邦的‘主旋律嗎?”
抱有這種看法的年輕人肯定不少。所以盡管自去年9月就有媒體開始關注《保爾》的排演,今年2月以來,傳媒又給予熱烈的報道,其廣告每天都在主辦單位之一的北京音樂臺滾動播出著,可上演后票房卻仍不理想。
這印證了演出前樂評人王曉峰的疑慮:“在一個‘心太軟流行的年代里,有多少人會去看《保爾·柯察金》?又有多少人會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挑戰(zhàn),這是一個懸念。”
而大家最初、共同的疑惑恐怕是:是誰、為什么在90年代末的今天,將一部70年前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重新搬上舞臺?
“我希望靈魂就像我的帽子,離我不遠”
“五六個,二十八九歲,中央戲劇學院87級的,學編劇學舞美的,其中3個還是一個宿舍的……一個人背著帆布包,一個人眉毛上別個‘別針,一個人戴著大眼鏡,眼鏡腿上纏著白線,一個人瘦骨伶仃剃著平頭,還有一個穿著草綠T恤干干凈凈不像搞藝術的。”
這是去年9月1日下午,北京酒吧街一次聚會上,《三聯(lián)生活周刊》記者眼中、筆下的幾個“看起來很時尚,滿不在乎的大小伙子”—彭濤、蔡尚君、刁奕男、劉奮斗和柳菁,是他們“在弄一個劇:《保爾·柯察金》”。
還要補充進去的是張楊,29歲,這個劇的獨立制作人。這之前他是活躍的歌手經(jīng)紀人(那英、侯牧人、零點樂隊),經(jīng)常做的是流行音樂的演出制作。
張楚,搖滾樂手,擔任《保爾》的音樂統(tǒng)籌。
一群最“時尚”“前衛(wèi)”的年輕人和一個“老土”的“紅彤彤”的題材,是如何勾連在一起的?僅僅是世紀末懷舊風潮中又一例“舊報新讀”嗎?
導演蔡尚君否認了這種猜測:“我們做這個戲首先要拒絕的就是低廉的懷舊和哀傷的挽歌。我們所關注的是那段不可磨滅歷史中一個獨特個體生命的閃爍之光。我們要借助它重新勘察我們的今天,但我們要的效果不是今昔對比,而是整合,對靈魂和肉身整合的一種探求。保爾的形象已經(jīng)超出了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它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種生存與生命意義的積極范例,呈現(xiàn)了一種作為人的高尚尊嚴。”
不過,他們萌生創(chuàng)作《保爾》的念頭倒是緣于一次“懷舊”的閑聊。1995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蔡尚君和幾個朋友聊起小時候的事:玩過的游戲,看過的小人書和電影。偶然地想到了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想到了保爾。
他說:“當時特興奮,保爾的故事里有革命、有愛情、有傷殘、有自我意志的搏斗和年輕人的成長過程,那冰冷、血熱兩種東西的交融,包括極富形式感的火車、鐵路都特來勁兒,特別激動人心。”
更重要的是,保爾的再次“出現(xiàn)”打開了一面久違的窗子。“畢業(yè)后的幾年,我覺得自己生活得沒態(tài)度、沒魂兒,行尸走肉似的。總是帶著一種自戀、叛逆的心態(tài),對社會難以適應。前衛(wèi)、先鋒成了一種姿勢。無聊、沒勁、沉悶,總之,生活得不健康。我們想念保爾。盡管我們已不可能像保爾那樣生活了,排這個戲之前之后我可能也不會有鮮明的變化,但我們需要保爾給自己和大家提個醒兒:曾經(jīng)有人那么認真地生活過。至少我希望我的靈魂像我的帽子,離我不遠。”
制作人張楊的情形與之相似,是在“年近三十,青春將逝,少年時渴望的稱謂—成熟指日可得的時候”,悲傷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青春是沒有顏色的!“想想自懂事起的這20年來,恣意地將看到、聽到、知道的、不知道的各種顏色涂抹在自己原本雪白的青春上,并狂妄地反傳統(tǒng)、激進、時尚、前衛(wèi)……而事到如今,卻因為無法找到在未來生活道路上支撐自己的生命信念而心虛、乏力!”是在“整理青春遺物的時候,偶然發(fā)現(xiàn)了保爾,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什么,我需要保爾,在我的心里!”
小學一年級的夏天,刁奕男認識了保爾。從此這個小說、電影、小人書中的形象成了他童年生活最鮮明的記憶之一,他也曾無數(shù)次地幻想過自己就是保爾·柯察金。正如蔡尚君所說:“保爾在我們成長的經(jīng)歷中被我們所熟知,以特有的方式和我們親近。”于是,偶然跳進話題中的保爾,就這樣成了他們的青春參照和激情投人的創(chuàng)作目標。
《保爾》是怎樣“煉”成的?
于凱的名字列在節(jié)目單上12名演員的最后一個。名字后面只跟了一句“飾歌隊之一,北京工業(yè)大學機械系學生”,沒提任何演藝經(jīng)歷。盡管北京高校中有十幾個學生劇社,但多半只是小打小鬧,上得了“大臺面”的不多,何況一問之下,這個20歲的大二學生不但沒受過任何演藝訓練,甚至沒正兒八經(jīng)地看過一場話劇演出!他是怎么“混進革命隊伍”里的? “從我哥那兒知道有人在排這個戲,我特別想?yún)⒓?就跟他們聯(lián)系,去見了面,談了我對保爾的看法和保爾對我的影響。導演說‘在臺上會有你一個位置的,這樣就進來了。剛來的時候我什么都不懂,還問人家‘要不要戴假發(fā)?這成了一個‘著名笑話。”
蔡尚君談到初次見到這個小伙子的情形:“他性格其實偏內向,對話劇也完全是門外漢,但氣兒特沖,質感很純,像我們當年那種,讓你覺得親切。就像是一塊生肉向你拽過來。這正是我們需要的,對職業(yè)演員也是個刺激。
“我們這個戲拼的就是真誠,就是這股氣兒。自己都不堅信,不純凈,那就完蛋了。我們對演員講,別把排這個戲只是當成個演出任務,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這個組有點兒像小宗教團體似的。”
剛開始蔡尚君最擔心的就是如何調動起演員這股氣兒,甚至想過組織大家去蹦級、跳傘,以體味那種生死瞬間的控制和掙扎。因為演員們幾年來有了很大變化,生活安定了,有的走入電視劇很長時間沒上舞臺了,進入這個戲要做很大調整。
作為“圈外人”的于凱除了要完成從普通人向演員的身心調整和相關訓練外,不得不作大調整的是他以往對演員的成見:以前他覺得這個圈子生活環(huán)境偏優(yōu)越,自由度更大一些,演員們生活態(tài)度浮躁、散漫、責任感差……在《保爾》劇組呆了兩個月,他不再以偏概全,反而能列出一長串“好人好事”:“好多演員為演這個劇把片酬很高的影視劇都推掉了,在這個組,從來沒聽誰談錢,大伙不是沖錢來的(為進首都劇場,他們曾主動要求放棄酬金,并自愿湊錢支付場租—筆者注)。
“這個戲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結晶,每個人都在努力,他們對角色特別鉆,有時候為了幾分鐘的戲要‘磨上一天。
“專家、媒體都看過了,大家還是該怎么演就怎么演。觀眾特別少的時候依然那么賣力。演冬妮亞的夏力心都演了十幾場了,每次演到保爾和冬妮亞分別,總要流淚。有次布景用的大木頭砸到了演麗達的楊青身上,她一動都沒動,挺著……”
為演保爾,胡軍推掉了一部電影,兩部電視劇。“你傻啊你,現(xiàn)在演保爾,誰看?得損失多少錢?”有朋友這么說他。 “我自己也不是沒猶豫過。很快得買房了,經(jīng)濟壓力撲面而來。可我真是特別想演保爾,覺得不能錯過。這不是讓我大紅大紫的機會,我也不是想從保爾身上得到什么東西,而是更確定自己原本有這些東西—個人奮斗、精神常在,即便被社會洪流卷得無可奈何,還是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生活熱情。我自己本身也有,但在社會上磨練的幾年中,慢慢忘卻了。排這個戲,我可以在內心里再揭示一下。
去年底一提出方案,我就很興奮。跟打火機點煙似的,“啪”一下,沖動和激情燃起來了。不過,說不清是不是也有點兒盲目。保爾所處的年代、歷史背景跟現(xiàn)今差別太大了,我們看了小說的全本,還有蘇聯(lián)拍的電影,結果一開始先掉在框框里了,滿腦子都是小說、電影里皮衣服、卷發(fā)、拄拐、很帥的那個保爾,使勁靠保爾。后來明白必須完全扔掉這根深蒂固的印象,想我是保爾的話會怎樣,讓保爾靠我,慢慢有點眉目了。現(xiàn)在舞臺上的保爾,我自己的成分很多,要占到2/3。”
給予你們今天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你們一直贊賞的東西
誰來贊助《保爾·柯察金》?
1997年11月8日,北京《生活時報》以此為題刊出了一篇占了一個整版的文章。招來的社會反響雷聲一樣熱烈,實質性的回應卻不過是幾滴雨點兒—沒什么人愿意為這個劇投資,理由是一致的,不看好它的市場前景。
1998年2月8日,《保爾》開始在北京兒童劇場上演,最多可容納800多人的場內經(jīng)常只坐著二三百觀眾,最少的時候只賣出去100多張票。
戲不好嗎?
來自專家和媒體的反饋大部分都是肯定的:戲是好戲。一位業(yè)內人士認為該劇票房失利是因為“吃虧”在它是“主旋律”題材—許多人以為又是那種生硬、空洞、教化人的作品,不買賬;該劇的實驗戲劇特征對一些習慣于看故事看情節(jié)的觀眾不討好。
需要留意的是《等待戈多》和《科諾克或醫(yī)學的勝利》也不能用“好看”來說,離觀眾也“不近”,票房卻好得多。有人說啦,前者是著名的前衛(wèi)戲劇,后者是明星演名劇,而且是姜文扔下12年后重“拾”話劇,自然有一定的號召力。
其實換一種思路操作,《保爾》的票房收獲可能會大不一樣。它不是沒有“賣點”。
蔡尚君和刁奕男最初拿著劇本四處找人投資的時候,并不是沒人肯出錢。但對方提出的條件是換一個“更有經(jīng)驗的”導演來導,有的則要求另外寫一個劇本,設法請“要人”接見劇組,走宣傳口徑的路數(shù)。
冒著大風險的是張楊。1997年4月,他的索洛演藝顧問有限公司成立,本來打算做流行音樂,就是因為和這群朋友在這個戲上的投合,因為自己的保爾情結和多年的話劇情緒,決定制作這個劇。
起初他以為這個事能感動自己也能感動別人,渴望在資本上更有勢力的人與自己合作,結果慘遭失敗。那篇整版文章也沒引來志同道合者融資進來。最后他決定靠自已,把公司現(xiàn)有的能提出來的錢做前期投資,又向父母借了一些錢維持正常的排練和制作。他說也想過會虧,但沒想到票房會這么慘。
那么是不是如一家報紙“刻薄”地指出的,這些年輕人是在自說自話?保爾之于現(xiàn)今的我們意義在哪兒?
胡軍:“現(xiàn)在社會這么復雜,周圍的參照物太多了,我們往往會把自己最本能、個體的東西丟掉。保爾帶給我們的感悟是:人得真正相信和肯定自已,感到自己與眾不同的存在,確立真正的自信心,這是我們這輩年輕人最該注重的。”
于凱:“大家目標太多,生活得沒有果斷性,人對自己不夠真誠,缺乏一種核心的精神素質。我現(xiàn)在才多大,我只有思維,就是沒熱情,不振作。平時哥們兒聊天,說要做這做那,說說而已,第二天忘得干干凈凈。所以去年《心太軟》才那么流行啊,勸你‘該放就放,怪你‘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多‘貼心貼意?《保爾》不想教化誰,但它是有益的。保爾的精神能生發(fā)好多東西,純潔向上、青春血性還有對生命信念的承擔和堅持。”
張瑞平(觀眾,某私立學校小學老師):“現(xiàn)在的學生挫折感太強,我們的教育常常是本末倒置的:要小學生愛祖國,成年人卻還得囑咐他自行車要放好。人對自身的精神培養(yǎng)特別少。可生命就是這樣,得有一種東西支撐著你。”
采訪張楊那天,場內只有100多觀眾。他接了一個朋友的電話,籌措急需的10萬元,這之前他已投進去了幾十萬,后面演一場賠一場,他說估計得賠50萬。而且很可能因為沒錢被迫取消原定3月1日—5日在首都劇院的幾場演出(后險些被言中,幸虧在媒體的關注下,中國航天公共廣告有限公司不計得失趕來“搶救”,首都劇場免了數(shù)萬元的裝臺費,才使《保爾》得以進權威的話劇舞臺)。
這的確是一次“不市場”的演出。
但它卻是一次直面內心處境的真誠嘗試。
那天我坐在后臺,演員的衣服散放在椅子上,戲在前臺演著,跺腳奔跑聲和臺詞音樂清晰可聞。因為看過前一場,所以我能聽出演員們是在全情投入,毫不敷衍。
忽然覺得糾纏于戲內,討論它內容形式的優(yōu)劣成敗和觀眾的欣賞惰性都不是最重要的。在這樣一個大家都“該放就放”,遇到路障就茫然無措、拐彎或是中途退場的今天,戲外這群年輕人提醒你反觀自身的努力是有益的,不是簡單的虧還是不虧。從前臺傳來的是清越的年輕的聲音:
……
風:我相信土地永遠呼吸于是有風,你們的心跳即使平靜也將隨風鼓動永不停息
雨:我相信天空永遠多情于是有雨,你們的眼睛即使蒼老也會被濺濕而清澈明亮
風:歡迎你們這些黑暗中的眼睛和心跳
雨:請記住這里震驚和沉默也許比眼淚更值得信賴
風:給予你們今天最需要的東西
雨:而不是你們一直贊賞的東西
風:靈魂已經(jīng)結滿了老繭
雨:那就去皮修剪
風:一個人有什么樣的開始雨:就會有什么樣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