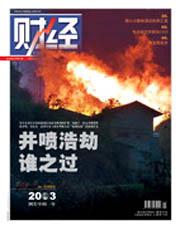三株治什么
李 甬
是藥不是藥——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偉哥和三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偉哥由一個60人的研究小組數年得之,考慮到輝瑞公司1997年研發投入達19億美元這一事實,其中為媒體所津津樂道的“運氣”不妨看作一個終究會不期而遇的助產婆。三株的誕生過程則“運氣”到無從解釋,吳炳新說,它是“一夢所得”。
然后,輝瑞公司一直致力于告訴公眾:偉哥不過是藥之一種,它的有效率不是100%,它有負作用,有禁忌癥,它需要在醫生的指導下使用。三株公司則一直致力把“有病治病,沒病保健”的口號寫在宣傳單上、鐵路橋上、農屋的墻壁上。事實上,它并不是藥,甚至它作為保健品的科技含量也是可推敲的——指出這一點的韓成剛家里的窗玻璃被三株員工砸破了。
三株和偉哥都不是孤立的故事。偉哥之后,輝瑞公司又在興致勃勃地談論另一種具有突破意義的新藥“2號舵手”;而在“三株”神話破滅前后,中國保健品業曾目睹了“飛龍”折翼,“巨人”傾覆,“太陽神”光輝不再……
由是,我們期望著中國的企業家們,特別是醫藥和保健品行業的企業家們,能從兩類不同的故事中,領悟產品和科學對于企業的真正含義。
塑料大棚進風了
就像三株“長”起來的速度一樣,三株倒下去的速度也是讓人吃驚的。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三株市場表現大滑坡”的傳聞開始抬頭,至1998年春天業已演變成“三株已申請破產”。
三株的窘境此后通過不同的途徑被曝光。
1998年7月,三株公司副總裁張薔對前往采訪的某記者透露:“1998年4月下旬開始,銷售急劇下滑,直至下滑到月銷售額不足1000萬元。4月至7月的4個月間全部虧損。”目前生產三株口服液的兩個工廠已全面停產,6000多名工人放假回家,只拿生活費。張薔說,三株口服液庫存積壓達2400多萬瓶。
吳炳新則干脆發出了“急需政府拉一把”的呼吁,他說:“三株現在寅吃卯糧,每月僅工資支出就達數千萬元。我們對現狀已無能為力。”
這就是不久前還在“爭做中國第一納稅人”的吳炳新?這就是數年來被形容為“神話”的三株?現在媒介對它有了新的比喻──“作為保健品行業龍頭老大的三株集團好像一個塑料大棚”,一進風就被凍得奄奄一息。
“風起于青萍之末”
按三株人自己的看法,寒風來自一場人命官司。1998年3月31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消費者陳伯順喝了三株口服液后導致死亡,三株公司須向死者家屬賠償29.8萬元。此后10多個省市的20余家報紙相繼報道或轉載:8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條老漢。
“這場官司給三株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張薔說。1998年4月間三株口服液的市場價下調近10元,但銷售曲線依然急轉直下。吳炳新不久病倒,20多天站不起來,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
三株人還記得一個叫韓成剛的山西人,這個榆次市癱瘓病研究所的普通科技人員被視為三株危機的始作俑者。1997年7月23日,韓成剛在山西日報上發表題為“推薦商品應對消費者負責”的文章,對“××口服液”的廣告宣傳提出質疑:“誰能保證消費者在18個月的有效期內服用時有活菌呢?每毫升含活菌量不少于2億個呢?還有,××口服液是否為野菌株、是否有耐藥因子等等關系消費者生命的國家級鑒定報告誰能出示呢?”此前韓成剛小范圍送發的文章點了三株的名,題目是“三株口服液是否偽劣商品?”
1997年下半年,三株口服液在山西省的銷售額為1560萬元,而1996年同期這一數字為5350萬元。在全國范圍內,三株口服液也漸露頹勢,1997年總銷售額為70億元,而1996年這一數字為80億元。
但是單單把韓成剛、陳伯順列為三株神話的終結者則顯然并不準確。事實上,韓成剛的科學武器主要來源于國家衛生部主辦的不同時期的健康報。
1995年10月26日,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研究員郭興華、賈士芳在該報上聯合撰文“活菌制劑令人喜,耐藥因子讓人憂”,文章說:“目前市場上所用的活菌制劑(或生態制劑),基本上都是野生菌株,絕大多數沒有用分子生物學方法檢查是否有耐藥因子,以致耐藥因子很可能在菌群中擴散……一旦服用者生病,抗生素將無法治療。”
1996年2月28日該報刊登記者魏蘭新采寫的報道“話說雙歧桿菌口服液”,報道說:“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前不久隨機從各大商場、藥店購得目前市場廣告多、知名度高的4種活菌口服液產品樣品,經檢測發現,……有的產品一個活菌都找不到。”
1997年5月1日該報刊登記者劉虹撰寫的報道“你吃的是活菌制劑嗎?”,稱“口服液標明活菌制劑有效期一年是不科學的”,因為“細菌在液體培養基中存活時間很短,一般一周內50%至80%的細菌會死亡,雙歧桿菌耐氧耐酸能力差,死得更多。”
這些批評中都沒有出現具體品牌。這使它們看起來像科普文章。只有極少數人留意到了它們,并決定慎買活菌制劑包括三株口服液。
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事實上,在口口相傳的層面,對三株口服液這一產品本身的非議在其成名之后沒幾天就已經露頭,在其迅速大紅大紫的日子里,這種聲音也像漣漪一樣,在另一些人群中一圈圈放大。
“高科技產品”還是“低水平重復”
那個一度隨處可見的標有“三株口服液”字樣的小瓶子里到底裝著什么東西?
三株公司的說法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那是“集保健與治療為一身,中國首創、世界領先的高科技產品”。在很多地方,它更被描述成“有病找三株”。
但是專家們卻另有說法。中國保健科技學會學術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評價三株口服液“技術含量低”,跟中國的絕大多數保健產品一樣屬“低水平重復”。他說:“不能說這個產品沒有功能,沒有存在價值,但是宣傳要適度,要以基礎研究為依托。它剛開始說它的三個菌株是活菌,但大家都知道,活菌一個月之后就差不多減到沒有了。后來它又說活菌的代謝產物是有效的,但代謝產物是什么,它又說不清楚。”
事實上,改善胃腸道功能的確不是非活菌不可,但是“三株口服液的基礎研究比較弱,其功能因子是什么,(結)構(功)效關系如何,(數)量(功)效關系如何,一直說不清楚”,所以對于認真的韓成剛們,它的說服力一直是有限的。
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完成的一份檢定報告對三株口服液則更為不利。在這份檢定號為SJIS970667的檢定報告中,這一國家衛生部直屬的最高技術權威機構對送檢的三株口服液作出了“不合格產品”的結論。
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是受湖南省法律部門的委托進行檢定的。在陳伯順家人狀告三株口服液人身損害賠償一案中,法官認為,檢定三株口服液與其廣告承諾是否相符是審理的關鍵所在。檢定對象除了陳伯順老人喝剩的兩瓶,還包括三株公司提供的同批號的產品。另外,檢定所的專家還在市場上購買了數瓶同類產品作檢定參照。
檢定報告稱:“未檢出雙歧桿菌等活菌;豚鼠過敏試驗陽性;小鼠安全毒性試驗陽性并經病理檢查,心、肺、肝、脾、腎和胸腺均有病理改變。”
有媒體評論道,檢定所為湖南省法律部門所作的檢定報告,已經撼動了三株口服液“立業的根本”。
到底該治什么病
三株栽了,栽在三株口服液上。三株要治病,首先要從產品本身(還包括產品生產規范和產品宣傳規范)著眼。但是另一些人不這么看。1998年8月份出版的一份雜志用了近20頁的篇幅報道困境中的三株,它的基本結論是三株在快速成長中“管理體系跟不上”,因此“輕輕一擊導致大廈震顫”。
有消息說,吳氏父子對這則報道是滿意的。如果是滿意于其轉移公眾注意力(對三株口服液)的公關效果也就罷了,如果是滿意于其結論,那就不由人不對三株重新站起來的前景感到憂慮。
三株一度“比國企更像國企”,管理體系自然是“跟不上”的。有人形容它患上了“恐龍癥”——機構臃腫,部門林立,等級森嚴,程序復雜,對市場信號反應遲鈍。原來不足200人的集團公司機關一下子增至2000人,子公司依葫蘆畫瓢。
但比起企業不甚理想的管理狀況,應當承認三株產品失去信譽對企業影響更大。韓成剛事件、陳伯順事件的反應均是明證。事實上,自去年開始,三株內部就在管理方面大動手術,吳炳新稱之為“刮骨療毒”,但因為三株口服液名聲不再,三株頹勢也依然如昨。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三株口服液是吳炳新“創造發明”的。這位中國保健品業的傳奇人物既沒有從醫的經歷,也沒有學醫的經歷,“創造發明”的過程被他自己描述為“一夢所得”。一批專家學者緊接著為三株口服液抹上第二層傳奇色彩,中國微生態學會主任康白教授稱之為“黑匣子”,意謂進去的東西清楚,出來的東西清楚,中間怎么變的不清楚。這位教授現任三株集團下屬一家科研所所長之職。
但是三株口服液在療效宣傳上可就不這么含糊了。1997年12月30日健康報載文披露道:“南寧市三株營銷公司擅自印刷各種小報、廣告傳單,當街散發或上門投遞,且把三株口服液吹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讓人感到似乎有了三株口服液百病皆除,再也用不著醫生、醫院了……”今年3月,廈門三株營銷公司因“違法廣告”被判賠償。4月,秦皇島三株營銷公司又因“虛假廣告”被迫公開致歉。
三株對產品研發的熱情與對產品促銷的熱情一直都是不可比的。三株口服液之后,三株再也沒有拿出過成大氣候的新產品,但廣告永遠都是大手筆。一位銷售經理回憶道,1997年某月三株的銷售收入只有1.2億元,廣告費卻拋出了1.4億元。
在三株的發展史上,吳炳新“農村包圍城市”的決策被認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像有媒體所說的,這一決策的效應也可以描述為──三株是“在消費者判斷力相對較低和信息來源相對較少的農村市場取得了廣泛成功”。遺憾的是,這兩個特點并不是能無限利用的。
產品!產品!
三株并不是第一個一朝即倒的保健品巨人。這幾年保健品業“飛龍”折翼,“巨人”(腦黃金)變成了矮子,“太陽神”光輝不再,“今日集團”的生命核能也成了昨夜星辰……一個個明星各領風騷兩三年,高高升起,又迅速落下,拋物線式的發展軌跡好像成了保健品企業的宿命。
1998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98國際天然保健及護膚產品博覽會向人們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美國森特瑞公司20年了,天來公司30年了,它們看起來還是那么生機勃勃。有介紹說,天來公司的研究所擁有200名博士。
不知道吳炳新聽沒聽說過這個,更不知道吳炳新聽沒聽說過沈陽飛龍老總姜偉的反思。1997年,這位保健品業的前老大在閉門2年之后,歷數了自身的“20大失誤”。他著重指出,飛龍的發跡是押寶于市場促銷,一舉成功。這種偶然性的成功漸漸成為自己的一種思維定式,種下了他日傾覆的禍根。
姜偉回憶了1994年他在香港準備飛龍上市的經歷。香港方面的律師問他:你每年的研發投入是多少?他答:2000多萬。人家又問:這么點投入,如何在未來5年內支撐起20個億銷售額?他不知如何作答。在準備上市期間,人家總共提出2870個問題,姜偉一多半答不上來。最后,對方告知飛龍上市存在四大隱患,第一條即是沒有硬碰硬的高科技產品。
經濟學家鐘朋榮曾經諷刺過主要不在產品上而在廣告上傾注心血的企業家們。他說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中國有13億人,從每個人口袋里掏一塊錢,就是13億之多。“他們主要不是制造產品,而是在制造概念,這種‘概念經濟是極不正常的。”
好在“概念經濟”并不能長久。太陽神是中國第一個導入CI的企業,但它衰落了,因為產品科技含量不高;馬俊仁寫下來的“生命核能”配方熱鬧了那么長時間,但它無聲無息了,因為不過是“8種常用中草藥”(《馬家軍調查》)。市場在短期內,尤其在不成熟的時候,可能會制造和接納幻象,但長期內卻是一塊實打實的試金石。
企業是需要老老實實做的。它的命運的基石是產品,是科學。由于行業的特性,在中國市場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保健品業相應地制造了最多最跌宕的悲喜劇,當三株這聲勢最大的一出劇畫上分號之際,但愿保健品和其它行業的企業家們能夠意識到這個最基本的道理──這是消費者的福祉所在,也是中國企業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