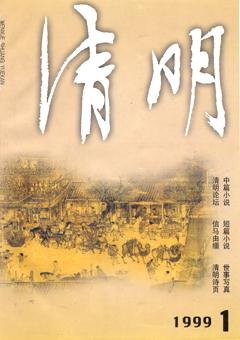黃麂
鄭時培
殷世清是早上開門時發現那頭黃麂的。
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殷世清打開厚重的杉木大門,看見一頭黃麂半臥半蹲在嶄新的屋檐下。殷世清打開大門的剎那間,一眼就看到那頭土黃色的黃麂。黃麂膽怯、驚慌、哀求的眼睛望著突然出現的殷世清,沒有一點逃跑的意思。那是個雪天。地上的雪已經厚厚地積了一層,天上的雪還在成片成片往下蓋。在一片白茫茫的背景下,黃麂那土黃色的毛顯得十分耀眼。
殷世清對這頭莫名其妙出現在眼簾的黃麂一下子還反應不過來,他拿著那條一人高粗重的門閂,呆呆地看著這頭小牛一樣的東西。黃麂掙扎了一下想站起來。這時候殷世清才如夢方醒,魁梧的身體一下子激動起來,舉起巨大的門閂向它撲去。
黃麂驚叫一聲,用盡平生力氣猛地一躥,最后還是無力地摔倒在雪地里。殷世清笑了,笑得舒心,也很得意。走過去將那黃麂一把抱到懷里,死死地不再松手。這一瞬,殷世清感覺到懷里的黃麂好像連掙扎一下的力氣也沒有了,聲音沙啞的凄慘地叫了一聲“哞——”。
這一叫讓殷世清心里一愣,忽然生出一種奇怪的想法,好像這頭黃麂是專門來找他似的,要不然怎么單單臥在這里?殷世清再看時,慢慢地從黃麂眼里品出一種非常熟悉的東西。他把它抱到了灶間的柴草堆上,點燃灶頭燒水做早飯。而在這以前,殷世清已經有些時候不做早飯了。
灶頭里的柴火燃起來,啪啪的響,艷紅而溫暖的火舌跑出灶口,照亮了昏暗的灶間。那頭黃麂動了動,一張生動的臉仰起來,望著灶頭里的火。殷世清仔細地看著它,覺得有這樣一頭野獸在一起也是挺有意思的。他知道黃麂被凍壞了也餓壞了,不斷往灶頭里添柴草。火越來越旺,溫暖著他們。殷世清的手禁不住就去撫摸黃麂身上那有點濕的長長的毛,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門外的雪還在下著,遠處的山莊已經讓雪幕隔得遠遠的不見蹤跡,山路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這樣的天氣不會有人來的。殷世清想,這頭黃麂少說也能賣上幾百塊,養它幾天,待近年關時再去賣了。有了這筆錢,也好去城里看看自己的媳婦和孩子。他找來一段麻繩,將黃麂抱過來,在它脖子上做了一個繩套,小心地拴在灶頭邊的柱子上,很滿意地在一邊看了好久,像看著一個久別的親人似的。
一個人的日子是寂寞的,殷世清已經好幾年一個人默默守著這幢空房了。他原先并不寂寞,有妻子后來有孩子,一家過得很清貧卻也開心。有了原先這份不寂寞和開心,后來殷世清的日子就顯得十分寂寞。只要沒有下雨刮風下雪或其他不良的天氣征兆時,殷世清一天到晚都伺弄著山地。他不讓自己空下來,一空下來他就會想起自己的婆娘,想起豐腴的女人乳房、肥臀和光滑的肌膚以及女人的種種好處。
殷世清的老婆師親妮本來是十分漂亮的村姑,現在是更加漂亮的城里人。她去城里先是給別人做保姆,以后自己做生意。開初,師親妮弄回來很多的錢,他把那些錢攢起來蓋了這幢村里數一數二的房子,買了很多實用的家什。可是有一天殷世清忽然發現這日子什么地方不對了,師親妮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和他做那事時的神態動作都十分敷衍。她偶爾從城里回來也只住一二天。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做這做那的,卻聽由殷世清服侍她。夜里殷世清幫著她脫衣服,要脫光時,她便不肯,說城里都穿睡衣的,只讓解掉扣子。殷世清要和她親熱一下,師親妮的身子平躺著一動不動,還沒進入角色就在下面一個勁催快好了沒有快好了沒有,催得他大多時候連師親妮的身子里面也沒有進去就匆匆地弄在了外面。
師親妮不管這些,推開殷世清扣好扣子和他商量孩子的事。商量次數多了,殷世清想讓孩子出去也好,就答應了。師親妮很高興,第二天早上允諾說,我會好好報答你的。當天夜里,師親妮像以前一樣脫光了衣裳,把殷世清服侍得很好,他好像自己整個人都進了師親妮的身子一樣。后來殷世清累了,師親妮問他還要不要,不要的話就不再給你了。殷世清滿足中笑笑,頭一歪睡去。早上醒來,師親妮和孩子已經走了,再也沒回來,兩年沒有消息。城里很遠,殷世清這才發覺居然沒留過老婆的地址,他只能遙望城里,一遍一遍地想念她們。
現在,有了這頭黃麂,殷世清心里漸漸升起了一種向往。平時他沒有覺察到這種向往竟會這樣的強烈。
這幾年黃麂已經不多見了,滿山的東西,只要稍稍值錢一點的,都讓人給砍了變成錢。這里沒有更多的出產,像黃麂這樣的動物一定很金貴。殷世清想,今年地里的收成不好,春天雨水太多,夏天雨水又太少,山地經不起折騰,一澇一旱,把那種好收成就弄沒了。殷世清很想師親妮寄點錢回來,家里連買鹽的錢也沒有了,他不知道對她是應該盼望還是絕望。現在殷世清對著通紅的灶火,一手向灶里添柴草一手撫摸著黃麂柔順的毛想,年底應該把師親妮母子倆接回來過年,以后再也不讓他倆去城里了,在一起過平平淡淡的日子比什么都好。
鍋里的水開了,殷世清拍拍黃麂的頭,去弄了一點苞米來,連于透了的苞米棒一起下到鍋里去煮。這頭黃麂肯定是餓壞了。要是現在家里還有一個人替他照看黃麂,他還可以到后山的窖里去弄一些番薯來。可是這么大的雪,沒人來串門。就是雪不大也沒幾個人來。來做什么呢?殷世清不會抽煙不會打牌不會麻將甚至不會象棋,到他家里來有什么意思啊?他也從不串門,串門同樣是沒有意思的。很多時候,殷世清就望著燈光打發時光,時間久了殷世清的心也細了,看什么都很深入,別人沒時間想的事他老早就想透了。殷世清希望師親妮賺夠了錢就會回來,天天在等著那個熟悉不過的人兒。本來,他會一直這樣等下去,這頭黃麂的突然出現,使殷世清改變了以往的想法。
鍋里的苞米飄出了誘人的香味。殷世清揭開鍋蓋撈出一只,自己先吃了幾口,想把苞米啃掉用棒子喂黃麂。沒吃掉幾粒,見那黃麂癡癡望著他手里的苞米,殷世清看看豐滿的苞米粒子有點舍不下,畢竟今年的東西太金貴了。他又咬了幾口,看那黃麂一動不動地盯著苞米,不忍心再吃下去,將它放到黃麂的嘴邊。黃麂試著咬了一小口,接下就大口大口地咬。他望著黃麂的樣子,很愜意。在殷世清的印象里面,黃麂是吃草葉子的。他不知道為什么這黃麂連老了的苞米棒子也要啃。金黃燦爛的苞米在火光的映襯下,顯出很有精神,很有力量。
殷世清看著它,想象著和師親妮團聚的好時光。離過年沒幾天了,到時把它送到村頭的獵戶殷老二家換回錢,便可以和師親妮團聚了。
那頭黃麂終究沒有被賣掉。殷世清待它體力稍稍恢復了一點的時候忽然發現這是一頭母麂,身上似已懷了孕。他拿不下主意,喊了隔壁的馮雨花來給他看著黃麂,自己去找來前幾年曾在公社獸醫站做過實習獸醫的殷木根,終于肯定這頭母麂真是懷了孕的。殷世清當下呆了呆,和師親妮團聚的想法就讓母麂肚子里的胎兒給擠沒了。他想,無論如何也要等這頭母麂下完崽以后才好把它拿出去賣。有了小麂,再繁殖一大堆小小麂,養雞養
豬一樣的,再不用愁沒有錢,再不用讓師親妮去那老遠的城里掙錢,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生活多好。
然而,很快黃麂的飼料成了頭疼的問題。殷世清沒養豬,師親妮進城后就不養了。秋收時地里的番薯藤都給了馮雨花家,地里的菜只夠自己吃。他只好把備下的冬糧拿出來和黃麂平分著吃。黃麂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來,他的糧甕一天一天空下去。這時候,殷世清想起了隔壁的馮雨花。
馮雨花家里養著兩頭豬,秋上備下了很多番薯藤。早聽馮雨花說過,今冬豬飼料是用不完的,何不向她借點呢?何況秋上曾把那么多的番薯藤給了馮雨花家。其實,殷世清現在完全可以不再養這頭黃麂的,村上人都知道殷世清家里跑來了一頭母麂,帶了胎兒的,很多人都愿意出一個大價錢把它弄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殷世清不肯答應。他要靠它去找回自己失去的東西,怎么肯輕易答應呢?除去馮雨花,沒人知道他會有這樣一個古怪的心思。村里人只知道師親妮在外頭攢大錢。
俟天上不再落雪,殷世清就去馮雨花家借飼料。山區里的屋不像城里的樓房,說是隔壁其實有二十多米距離。馮雨花正悠閑地坐在一缽炭火邊烤火,豐滿潤白的臉讓火烤得緋紅,顯得十分健康。殷世清第一次仔細地注意了這張臉,驚奇的發現除了師親妮外村子里竟還有如此動人的婦人。馮雨花見殷世清盯著她看,大方地笑說:“今天有空過來?有事吧?”
殷世清就把借番薯藤的意思說了,怕她不肯,補充說:“明年我地里的番薯藤全都給你們家,行不?”
馮雨花笑了。她笑時很好看,眼睛一瞟一瞟的,肩上一塊粉紅色的補丁像是要被她抖動的身子綻開。殷世清就看著那塊補丁,聽著馮雨花笑。
笑夠了,馮雨花說:“這番薯藤本來就是你的,現在我只不過把它還給你。坐一會兒吧,等下我幫你一起拿過去。”
殷世清不好意思地說:“不坐了,那東西還等著吃。”
“好吧,那我們走。”馮雨花就去灶間抱了一大抱曬干了的番薯藤,緊隨著殷世清出門。
雪積得很厚。馮雨花抱著這么一大抱番薯藤走路就顯得十分吃力。開始殷世清沒在意,顧著自己走。當聽見馮雨花粗重的呼吸時,才感到了一點什么,忙回過頭去幫她。馮雨花把頭歪了歪,說自己能行,不肯讓他插手。殷世清已經抱住番薯藤的手不好再收回來,倆人拖拉著一起把番薯藤弄進了殷世清家的灶頭間,坐在長條形的木凳上喘氣。
那頭黃麂看了看他倆,又看看身邊的番薯藤,開始選一些較嫩的葉子吃。馮雨花哈了哈凍僵了的手,扯一條番薯藤去喂黃麂,說:“你們家真冷。引點火吧,看我都快凍成冰人啦!”
殷世清這才想起去生火。一會兒,一縷煙爬出灶膛,在灶間里彌漫開來。馮雨花一把將殷世清手中的柴草奪下來說:“怎么弄的,師親妮沒有教過你啊!男人真的沒出息。我來。”
灶膛里的火很快亮起來。殷世清沒想到馮雨花做起這些事情來會這樣的爽快老練。她是去年才到村子里來的,是村支書殷木桶的麻臉兒子殷上樹花了三千塊錢從外面買回來的。開始幾個月,馮雨花不肯做任何事,見著機會就跑。每次都讓人給追回來。最后一次,馮雨花又跑出去了。村里人已經找得絕望了,她卻自己回到村里。她不會劃船,而要出這個村必須自己會劃船,渡過一條幾十米寬的江。那天晚上她在江邊坐了很久很久,終于自己又回來了。以后馮雨花再沒有跑過。安份地呆在村子里,學會了所有的生活。對這一切殷世清是不太清楚的。他只偶爾聽人說馮雨花不肯讓殷上樹碰她,所以一直沒有懷上孩子。殷世清想不通,這樣一個女人為什么不讓別人碰她呢?想想,就笑出聲來。
馮雨花一轉頭,看見殷世清在她背后一個勁地笑,有點莫名其妙,說:“你笑什么,沒吃過鹽呵?”
殷世清說:“不是。我不是笑你。”
馮雨花說:“那你笑什么?”
殷世清亂說:“我笑你這補丁。”
馮雨花看著肩頭上那塊緋紅色的補丁,坐回到凳子上。灶膛里的火越來越旺,火苗把昏暗的灶間映得亮堂起來,馮雨花那雙修長豐腴的手在自己的腿上機械地搓著。殷世清一下子不知道說點什么好,看看已是快做晚飯的時光,朝馮雨花笑笑,去廂房里取米做飯。
廂房和灶間隔著幾步路,殷世清走得很慢。進門的時候,他差一點撞在門框上。他呆了呆,忽然想起和師親妮結婚的那天晚上也這么差一點撞在門框上,是師親妮拉了一下才沒有撞上去。那時,殷世清一下子感覺到了女人的好處。這種好處一直到今天還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師親妮是他唯一的親人。這村子里拐彎磨角的親戚對于殷世清來說都是沒有什么痛癢的關系。這時,殷世清又想起師親妮在家時的情景,想起師親妮溫暖柔嫩的小手和她那雙小手弄出來的生活情趣,忘了還應該把米從甕里弄出來拿到灶間里去。
馮雨花在灶間里等了很久,還沒有見殷世清把米拿來。灶頭里的火旺旺的,鐵鍋里的水蒸汽咕咕咕向外冒。身邊的黃麂慢騰騰地嚼面前的那一小堆番薯藤。馮雨花等得不耐煩了,往灶頭里添了一把柴草,站起來去找殷世清。她走動的腳步很輕,到他的背后時,殷世清也沒有察覺。
“想老婆了?”馮雨花輕聲說。
殷世清一驚,不好意思地拿一個搪瓷杯到甕里去舀米。他彎倒身子的時候看見馮雨花的一只小手很像師親妮,心里產生一種久違的沖動,很想去握一握那雙被凍紅的小手。這種想法只一瞬便消失了,師親妮現在會在什么地方呢?
馮雨花見殷世清不響,又笑著說:“怎么,還不好意思呀。我來時就不見師親妮了,她一定很漂亮吧?會做很多好吃的?”
這幾年來,一直沒有人跟殷世清講這種話。他不知怎樣回答,便拿米去灶間。殷世清一轉身,正和她打了個照面,馮雨花奪過他手里的搪瓷杯說:“今天我來給你燒一頓飯。”
殷世清忙奪杯子說:“上樹知道了不好,還是我自己來吧。”
馮雨花推了他一把,邊走邊說:“管他呢,你又不是別人,說起來還是親戚,難得的。”
倆人就一前一后回到灶間里。殷世清看著馮雨花淘米,心里升起一股很濃的感激之情。米下鍋后,馮雨花甩干手上的水坐到灶頭前的凳子上烤手。殷世清也想過去烤一會兒手腳,看看她占住了灶頭口,便站在原地瞄著鍋里咕咕往上冒的蒸汽發呆。
一會兒,馮雨花像是看出了殷世清的心思,挪了挪屁股說:“你也來烤烤吧。燒飯還是燒粥啊?”
殷世清看了看她說:“隨便吧,什么都行的。”
馮雨花哈哈哈地笑起來,說:“你這個人怎么回事,想老婆想瘋了吧?哎,師親妮在時為你做什么吃呀?”
殷世清搓了搓手,在嘴邊呵了一會兒才說:“想她干什么?我是想兒子哩。”
馮雨花拍拍身邊的凳子說“都這樣說呢。其實孩子有什么好想的呀?還不是你們男人的一個借口。不想師親妮?哼。過來坐吧,冷呢。”
殷世清看看灶頭口涌出的鮮艷的火焰,感到腳上的那雙舊解放鞋越發抵不住寒氣,
腳心的一股子冷氣直往胸口上躥。他磨蹭著走過去,在馮雨花身邊坐下來。一坐下來他就后悔。在那團火紅色的火焰熏烤下,她身上散發出一股很濃很濃的女人味,弄得殷世清很不自在,倆人都好像感覺到了什么,不再說話,偶爾瞟瞟對方。
鍋子里的米開始散出一種誘人的芳香,殷世清感到漸漸的暖和起來。馮雨花突然側頭問:“殷世清,你這么幾年來沒有碰過其他女人?”
殷世清沒想到她會問這樣的問題,猛丁不知怎樣回答。馮雨花還那樣直愣愣地看著他。這時候那頭黃麂“哞——”地叫了一聲。殷世清恍然記起今天還沒有給黃麂加墊一層干草,連忙要起身去柴房弄草。馮雨花一把拉住他說:“問你話呢,怎么不回答?”
“沒……沒有……我要去弄點草來給黃麂墊上哩,它那草濕了,夜里冷。你看,它向我討哩。”殷世清掙脫她的手,顧自去弄草。
馮雨花感到好笑,這人真有意思,不像上樹那樣死皮賴臉的。待殷世清弄來草給黃麂墊上,馮雨花又往灶里添了一把草說:“我得回去了。喂,殷世清,這黃麂要是生頭公的就好了,以后養黃麂賣也是不錯的呀。過兩天我再給你送一點番薯藤過來,到時發了財可不要忘了我呀。”
殷世清送馮雨花到門口,望著她在雪地里一步一步遠去,她肩上那塊緋紅色的補丁一直很耀眼,像一團淡去的火焰讓殷世清的心里感受到曾經有過的那種溫暖。他這樣站在門口看著馮雨花消失在她自家的門里,直到一股飯焦味飄進他鼻孔時才突然想起師親妮走的前一天也是穿著這么一件緋紅色的衣裳。這是他看到師親妮身上最后的一種顏色。那是一個春天的夜晚,殷世清頭一次知道世上還有一種專門用來睡覺穿的、只用一條帶子扎起來不用結扣子的衣服。師親妮說那叫睡衣。
沒多久,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殷世清家平白無故地跑來一頭黃麂,這頭黃麂還帶了崽。老獵戶殷老二已經好幾年沒有獵到過黃麂,村里人都以為黃麂這東西已經在這一帶的山林里消失了。殷老二知道它的價值,賣得好這么頭野獸抵得上一頭肥豬。他立即去了殷世清家,看過黃麂后想出八百塊的價買下來,被殷世清拒絕。村子里的人都窮,殷世清家因為師親妮頭兩年在外面做工攢了一點錢,算是富戶。村里人都認為殷世清家有大堆的錢不肯借給別家,把錢當作命一樣,是很小氣的,沒想殷老二出價八百他也不肯將黃麂轉讓,可見這東西的價值。這頭黃麂就被村人傳得越來越神,傳到很遠的鄉政府也有人知道,專門來看了黃麂,對殷世清說鄉里也很想弄這么頭黃麂給縣民政局管救濟的人,好給鄉里弄點救濟款。殷世清也沒答應,說待黃麂產下后再說吧。鄉里的人不好強求,殷世清既沒違反計劃生育也不欠交稅款什么的,這事不好辦,只好打道回府。
這以后,沒人再打黃麂的主意,即便打了主意也沒有人愿意再去碰釘子。村上的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殷世清一個大男人家養著這么頭野獸做什么用,他家的師親妮不是在城里攢著大錢嗎,還養這東西做什么?
臨近過年,那頭黃麂終于產下一頭小崽。黃麂臨產的那天馮雨花正在殷世清家里幫忙燒飯。自從殷世清頭一次向她借番薯藤那天后,馮雨花就隔三差五地過來幫忙燒一餐飯洗一兩件衣服被子什么的,有時也幫著喂一喂黃麂,她和殷世清一起看著黃麂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
殷世清沒想到馮雨花會這么老練的替黃麂接生。那頭黃麂痛苦地呻吟著生下肚子里的小黃麂,再咬斷長長的臍帶,已無力去舔干那小東西身上濕漉漉的污血。馮雨花找來一塊薄薄的棉布覆在小黃麂身上,小心地將灶膛里的柴草灰一點一點的撒在棉布上。溫熱的柴草灰慢慢地把小黃麂身上的污血吸出來,她不斷地把濕了的柴草灰一點一點扒掉,再重新撒上干燥的柴草灰,直到撒上去的柴草灰吸不出什么了,又匆匆地跑回去拿了些紅糖來泡在米粥和番薯藤混合起來的飼料里面喂給黃麂吃。做這些事時,馮雨花眼里始終洋溢著一種很慈祥的東西。
自從馮雨花走進這個大門里來以后,殷世清就產生了一種很不安也很奇怪的心情。他變得不怎么想念師親妮了,馮雨花有那么一兩天不來,他的日子好像長得沒有了邊際。其實馮雨花來了,殷世清也不知道該和她說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他只是想馮雨花來,和她在一起呆一段時間,好像一日三餐,到時就會想起該做飯一樣。開初殷世清和她在一起還會想起殷上樹,后來就什么也不想了,好像本來就是這樣,他喜歡看馮雨花干活的樣子和于活時的那種神態。
殷老二知道這只黃麂已經下崽了,再次來殷世清家說,你有了小黃麂,這頭大的該賣了吧?殷世清又回絕了他。馮雨花在一邊打趣道:“這是殷世清的小老婆呢,他怎么舍得賣?老二,你還是自己去打吧,說不準你也有這么個福氣的。”
殷老二就笑,說:“你怎么啦,上樹又靠邊站了是不是?什么時候也像這頭黃麂一樣下個崽呵?上樹不行,我幫你怎么樣?哈哈哈。”
馮雨花罵:“你個該死的,上山讓老虎吃了才好。還不快回去看看你老婆的褲帶,說不定又讓誰給松了。”
殷老二又笑,指著馮雨花說:“沒事沒事,她那褲帶讓人松了就松了。我倒想看看你的褲帶是不是松了。”
馮雨花拉下臉來罵:“看你娘的去吧。死沒正經!”
殷世清在他們打情罵俏的時候回到灶頭邊看著那頭下完崽的黃麂出神。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留下這頭黃麂。母麂已經緩過氣來,在一點一點舔著小黃麂身上的細毛,偶爾很善良地抬起頭看一眼殷世清,像是有什么話要說一樣。
村子里看稀奇的鄉親都走了。馮雨花回到灶間說:“殷世清,現在黃麂生下崽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過了好久,殷世清回過頭來說:“這些日子真虧了你哩。把這小東西養大了再說吧,到春上總會好些的。”
馮雨花說:“師親妮什么時候回來?”
殷世清搖搖頭,坐回到長凳上重又默默地看著兩頭一大一小的黃麂。馮雨花朝他背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罵道:“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人家關心你呢。問你話怎么不回答,你老婆什么時候回來呀?”
殷世清仍然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她沒信來哩。”
馮雨花說:“她到底在城里干什么?怎么幾年都不回來?別被人騙去賣了。你兒子也沒消息?”
殷世清看了看她,低下頭,師親妮到底在城里做什么呢?他知道馮雨花就是被人騙到這里來賣給殷上樹的。師親妮會不會也被人騙到什么地方去賣了呢?連她在城里的地址也沒有,怎么辦呢?
馮雨花見殷世清不再理她,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回家去了。這些天來她對殷世清一點也吃不透,有時候感到離自己很近,有時候又感到和自己完全是在兩個世界。對于她,也許這是最后一個機會了。那頭黃麂的出現,讓馮雨花久違了的想法突然在心里一亮,看到殷世清朝自己走來,那一瞬間她暗暗責怪自己兩三年來怎么沒有看到近在咫尺的單身男子殷世清!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想殷世清的心里到底是在想著什么。
這個村子并不大,三四十戶人家散落在一個山坳里,一條小溪從村子里每戶人家的門前向遠處的江里奔去,幾千年幾萬年也沒有帶走這里的一點東西。這地方其實比馮雨花的老家還沒意思,她老家至少還算是一個鎮,而這里連電視圖像也收不到。她試探過村子里大多數男人,那些男人都很正統,都用眼睛緊緊地盯著她,生怕她再從這個村子里消失掉。要不是平白出現那頭黃麂,馮雨花真不會格外注意到村子里還有這么一個殷世清。一個殷世清給了她幾個閃閃發亮的希望。
殷世清可不知道馮雨花的心思,只覺得老是這樣受用她家的東西不是一個好辦法,心里老盼望著雪快點融掉,春天快些到來。殷世清望著那頭小小的黃麂,原打算年前去城里接師親妮母子倆的念頭慢慢沒了,一心想著這頭黃麂快快長大。長大了做什么呢?他沒有想過。
春天終于姍姍而來。有一天早上殷世清起得晚了一點,他一開門就驚喜地發現屋檐上長長的冰柱子開始滴水,遠處的林子也冒出枯灰的樹尖,馮雨花正在自家的門前一下一下掃著積雪,太陽升起老高老高。這時候,殷世清想起該給黃麂搭一個柵欄式的圈,也顧不上吃早飯,找出家什來在灶間里用柴棍粗粗地圈了一個一人多高的柵欄,把兩頭黃麂拉了進去。
做完這些,殷世清感到有點熱,也有點興奮。他很想把新做了一個圈的消息告訴什么人,就走出屋子朝馮雨花家那邊去。
馮雨花已經不再穿那件有塊緋紅色補丁的棉襖,懶懶地坐在屋檐下曬太陽。殷世清離馮雨花家門還有幾步路的時候聽到嘩嘩嘩一片搓麻將聲,知道殷上樹今天沒出去,一定是在家搓麻將。他望望在門口竹椅里打著盹兒的馮雨花,又轉身踅回自己家里。
殷世清前腳剛進門,就聽見灶間里傳來一陣陣異樣的響聲。他跑過去一看,那頭母麂正用力撞著新圍的柵欄,柵欄搖搖欲倒。殷世清奔過去拚命驅趕,那黃麂老實了一會兒又撞起來。殷世清拿了一條竹棒想打它幾下,馮雨花卻抱著一捆干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她看了殷世清一眼,把干草扔進圈子里細心鋪開,說:“有你這樣笨的人!它們沒有草墊還不凍死啊?”
那母麂見地上有了草,過去拱開來讓小麂站到草上面,然后才安靜地在干草上臥下來。殷世清看著黃麂安靜的樣子傻笑著。馮雨花站了一會兒,見殷世清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她一樣,說:“殷世清,好像我幫你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是不是啊?我告訴你,我可不是白給你做的。”
“噢,這樣呵。那些番薯藤我是要還給你的,今年秋上收成好的話,我再給你一些番薯好了。你要米也可以的,反正我多下來也沒什么用。”殷世清看著黃麂說。
“我不要你這些,我要……”馮雨花欲言又止。
殷世清這才回頭看著她說:“你要什么?只要我有的,我一定給你。”
馮雨花沒再說,伸過手來拉住殷世清的手。殷世清不知道她究竟要什么,只感到手上暖暖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暖和起來。他們站得很近,彼此感受得到對方的呼吸和心跳。馮雨花看著殷世清的眼睛。殷世清也看著她的眼睛,看著看著就情不自禁地把她的身子往身邊拉。馮雨花輕輕地靠了過去,把頭埋在他寬厚的懷里。
殷世清感覺到馮雨花很軟的身子和溫暖的手心,心里面似乎已經陌生了的那種沖動一下子占據了整個的心田。他的手沒有了分寸,撩開馮雨花的外衣就想插進去。她身上還穿了好幾件毛衣,這些毛衣把他野蠻的手擋在了身體的外面。殷世清的手只好在厚厚的毛衣外面亂哄哄地尋找著馮雨花豐腴的乳房,有好幾次差一點和她一起摔倒。無意之中,馮雨花靠上了一根柱子才使兩人站穩了腳。
很長時間,殷世清把馮雨花緊緊擁抱在懷里,那雙寬大的手一直慌亂地在她厚厚的毛衣外面徘徊。馮雨花有點累了,推開殷世清,仰起臉看著他說:“世清,我們到床上去吧。”
殷世清的手本來還不甘心地在馮雨花的懷里亂尋,聽她一說,像是觸到什么東西一樣驟然停了下來。
馮雨花迎住他的眼光,癡癡地等待。殷世清心里那種沖動在這一瞬間慢慢地冷卻下去。他似乎看到師親妮在什么地方正像馮雨花這樣癡癡地看著自己,不禁低下頭去,不敢再看馮雨花那對微醺的眼睛。
灶頭間里很靜很靜,只聽到黃麂劃動干草時“悉悉悉”的聲音。殷世清和馮雨花面對面的站著。很久,他才粗粗地喘了一口氣,不知所措的茫然地跺一下腳。馮雨花也似乎清醒了許多,匆匆理好自己被扯開的衣扣跑出大門。
過了好久,殷世清也沒有搞清楚自己究竟為什么會這樣,總覺得這樣對不住師親妮,心里很是懊惱。他不知道為什么馮雨花也會有那種意思,竟然會主動說去床上。不過,殷世清這回終于知道了她也是有這種意思的,他懊惱的同時又細細回味剛才撫摸馮雨花身體時的動作,那種沖動又被喚起,手不自禁地伸向自己的下身,一會兒便感覺到全身一陣愉快的痙孿,不由得呻吟起來……
晚上殷世清烤了兩只番薯隨便吃了,沒洗臉也沒洗腳就躺進被窩里想一些過去的事情。
師親妮的出走完全是因為那個該死的殷老二。那年師親妮養了一群鵝。師親妮手巧心靈,干什么是什么,從來不落人后。那群鵝在她的料理下很快長成,白白的羽毛,胖嘟嘟的形態,很是招人喜愛。只是,村子里沒人買得起這些鵝,就是買得起也不會買,自家養的都愁沒有出路呢。本來,家家養這東西也沒指望賣什么錢,反正鵝是自家孵的,滿山里的草也不要本錢,養幾只逢年過節宰了吃,吃不下讓它們自己早出晚歸,花不了多少心思。那年大家也實在養得太多,殷老二獵了幾頭獸到城里去賣,說是在城里有很多店收購白鵝,價錢和野貨差不多。
村里人頭一次聽說城里也有人要買鵝吃,沒多少人相信殷老二說的話,都當作一個笑話在傳。可師親妮就信了,專門找他問了價格、收購的地點,和殷老二約好下次一起到城里走一遭。殷世清百般勸阻也沒有用,師親妮從城里回來就和殷世清商量,她要到收鵝點的那家飯店里做工,說是每月有好幾百塊錢,還包吃包住。殷世清有點心動,在村里苦苦干上一年還攢不下幾百塊錢,到城里一個月就能掙那樣多錢,要不了一年便可以把房子拆掉重造幢氣派點的瓦房,真有這樣的事?師親妮就這樣走出了小小的村子,走出了殷世清犀亮的目光。
殷世清想不下去了,把被頭拉了拉,讓整個人都埋進被頭里面,還是覺得冷。已經是春天啦,為什么還這樣怕冷?被子有點潮,還有一股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蓋在鼻上真的有點受不住。殷世清記不起有多長時間沒有曬過被子,更不要說洗了。
睡在被頭里的殷世清第一回被這種氣味折磨得徹夜難眠,想象著有師親妮的日子,想象著他和兒子說故事的那些有星星月亮的晚上,想到最后不免想起馮雨花那雙溫暖的小手和肩上那塊緋紅色的補丁,到天亮時才迷迷糊糊地睡著。
春天的日子總是那么快走出人們的視野。殷世清還沉浸在春天的氣氛里,夏天已悄悄地來到山坳里了,豐盛的草葉讓那兩頭黃
麂茁壯成長。殷世清沒日沒夜的在地里、山上料理莊稼采集黃麂的飼料,再沒有空去馮雨花家了。事實上,殷世清已經沒有必要再去找馮雨花,滿山滿地都是黃麂能吃的飼料,根本不用他再花什么心思。那兩頭黃麂經過幾個月的馴養,已經習慣家里的一切,有時殷世清把它們從圈里放出來,讓它們在寬大的灶間里自由走動,甚至有一次他忘了關上大門,黃麂也沒有逃走。
殷世清在春夏之交的時候把自己所有的山地都種下了清一色的番薯秧,將兩頭黃麂一個冬春踩下的欄糞全部壓在地里。望著那一畦畦整齊的番薯秧,殷世清常想,要是那兩頭黃麂是一公一母就好了,過幾年他可以擁有一大群黃麂,可以賣很多錢,那么師親妮就不用到城里去攢錢。可惜兩頭都是母的。
有了兩頭黃麂以后,殷世清比往常要忙得多,空閑下來也多半在想與黃麂有關的事情。夜闌人靜時,他偶爾也想起馮雨花以及和她度過的那一短暫浪漫時光,想到情急處,免不了自己安慰一下。奇怪得很,每次一這樣,殷世清馬上便想起師親妮,到天亮才能入睡。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這樣,眼前老是恍動著馮雨花肩上的那塊緋紅色補丁,有幾次甚至很后悔的想那次真該和馮雨花到床上去的。平日里路上碰到她,他都禁不住瞟幾眼她越來越清晰的體型。有一次殷世清看著馮雨花豐腴的臀部隨著步子很有韻味的抖動,心里竟升起了某種騷動。
殷世清的心里十分矛盾,他既很想像年前那段時候一樣再和馮雨花無拘無束的在一起,又怕碰到她。在他的印象里,馮雨花似乎也在忌諱著什么,兩人偶爾碰面只是笑笑,再沒有說話。對于殷世清來說,說不說話都是一樣。隨著季節的變化,馮雨花一件一件脫掉衣裳,把那天殷世清雙手沒有探求到的內容慢慢推到了他的眼前,強烈地刺激著他。殷世清越來越有些分不清楚師親妮和馮雨花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那是端午節過后一個大風雨的早晨。殷世清被一聲響雷從夢里驚醒。醒前他夢見自己身邊躺著一個赤裸的女人,他正很沖動地摸著這個女人豐潤的乳房,剛想把她抱到懷里面做那事時一聲很響的雷聲在床頭邊的窗外響起。聽著嘩嘩嘩的檐水在窗外很響的往下落,殷世清努力回憶夢中的女人,像是師親妮,又好像是馮雨花,只記得那女人手里拿著一塊緋紅色的手絹蓋在兩腿之間。他幾次要掀掉那塊緋紅色的手絹,卻怎么也沒有掀動。殷世清不明白,看似那么輕盈的手絹怎么會比滿擔的濕谷還沉重?他不想起床,很想就這么一直想下去,灶間里的黃麂在一聲長一聲短的叫,叫得他心煩起來,猛然記起門外還有一擔草晾在屋檐下,昨天晚上回來沒有做飯也沒有去灶間,竟忘了給黃麂添加飼料,難怪它們要叫。殷世清連忙起床去開門。
殷世清打開門,馮雨花竟然撐著把補過的雨傘站在門前焦躁地看著他。馮雨花不滿地說:“你是裝睡還是怎么?我喉嚨都要喊啞了。快去幫幫我們,我家后墻讓雨水浸倒了,水正往房里灌呢。看樣子前邊的墻也要倒的,快點啊。”
沒等殷世清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馮雨花轉身匆匆跑回去。殷世清急急忙忙地抱了把草扔進柵欄里,隨手撈過頂笠帽,連門也沒有關便向馮雨花家那邊跑去。
馮雨花家里已經一塌糊涂。很多人拚命地在加固差點倒塌的泥墻,水正從倒塌的墻外嘩嘩地涌進來,屋子里的水已經漫上腳背。殷世清擠進亂哄哄的人群里,不知道該做點什么。墻邊有人叫拿柴扦來,殷世清就滿處去找柴扦。馮雨花跑過來說:“你家里有沒有?還要很多呢。”
殷世清一下子清醒了,自己冬上備下了不少毛竹,準備年后師親妮回來把黃麂圈移出灶間,搭黃麂圈用的,師親妮沒有回來,他就一直沒有心思去動它。現在,殷世清心里很不想把那些毛竹拿出來用掉,萬一師親妮回來,再要去找那么些毛竹來又要待到秋后了。然而,畢竟是馮雨花需要,他掉頭和她回家去扛。
雨沒有要停的意思。殷世清的笠帽根本起不到作用,身上老早就濕透了。馮雨花從后面趕上來,給他打傘,倆人頂著雨向前走,二十多米路好像比往常長了許多倍。跑到殷世清家里時,馮雨花的全身也濕透了。殷世清一眼看見馮雨花雪白的的確良襯衣緊貼在身子上,勾勒出她豐滿的身段。他看見馮雨花被雨水弄得完全透明的外衣下渾圓的肩膀和被乳峰高高頂起的碎花小背心,心里愣了愣,拿下自己頭上的笠帽一下一下地甩著水珠。
馮雨花擰袖子上的水說:“喂,你看什么呀?給我找塊干毛巾來吧,全身都濕了,很難受的。”
殷世清答應一聲去找毛巾。馮雨花就到廂房里把外衣脫了,一邊用力地絞水,一邊等殷世清找來毛巾。她把鞋子里的水也弄掉了,還是沒見他回來,干脆把外面的褲子也脫下來,一下一下擰干。這時候,殷世清還在房里翻箱倒柜地尋找干毛巾。他不知道,其實家里已經根本沒有新的毛巾了,師親妮在時積下那幾條新新舊舊的毛巾早已用完。直到馮雨花喊他時,他還一個勁把箱子里最后那幾件師親妮沒有帶走的衣服拉出來,匆匆地應了一聲,望著空空的箱子發呆。
馮雨花鬧不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提起濕衣“咚咚咚”跑到殷世清這邊埋怨:“讓你找條毛巾,你是在繡花啊?不舍得是不是?”
殷世清一回頭,驀然看見馮雨花裸露的雙肩,心里一激,再想移開眼睛就怎么也移不動了。
外面的雨仍然嘩嘩嘩的下著,殷世清忘了馮雨花家里的那些人還在等著他們把毛竹扛去,看著她發癡。馮雨花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說:“看什么,沒有看見過呀?毛巾呢?”
殷世清嘿嘿嘿地干笑幾聲說:“沒有找到。我再找找吧。”
馮雨花看一眼也落湯雞一樣的殷世清,嬌嗔地說:“還是我來吧,你自己找件衣服先換上。”
殷世清這才感到身上濕漉漉的難受,順手拉過幾件衣服出房去換。馮雨花扔下自己的濕衣服,在堆滿了衣服的床上找干毛巾。
殷世清換好衣服,順便去看看灶間里的黃麂,給它們添一把干革,又弄了些青飼料進去。兩頭黃麂一下子安靜下來,埋頭吃飼料。殷世清才回房里去。
馮雨花已經把一床的衣服收拾掉,自作主張拿了一套師親妮沒有帶走的衣服換上,斜躺在床上等殷世清過來。房間里的光線有點暗,殷世清看見馮雨花時已經走到了床邊。他看清躺在床上的馮雨花,就再也禁不住那股壓了很久很久的心火,想把她一把抱起來又不敢。面前的馮雨花在他的眼里已經和師親妮沒有什么兩樣,甚至馮雨花那有點暗示的微笑也與師親妮的一模一樣。
他們這樣相望了一會兒,馮雨花坐起來拉住他的手說:“我穿這身衣服好看嗎?”
殷世清語無倫次地說:“好看好看好看……”
馮雨花猛然把頭埋進他懷里,喃喃地說:“我有點冷,你抱緊我抱緊我。”
殷世清坐到床上,把她抱在了懷里,一下子感覺到馮雨花豐潤柔軟的胸脯緊緊貼上來,好像要把單薄的衣服撐破一樣。殷世清的手本能地伸進她的衣服里,很野蠻地搓捏那堅挺的乳房。馮雨花用頭在殷世清懷里磨蹭
著,不斷發出細若游絲的呻吟,身體更軟更熱了。房間里好像稍許亮了一些,殷世清透過不怎么明亮的光線看到馮雨花慢慢敞開來的雪白的胸脯。他試探著把手朝下摸去,摸到馮雨花潮濕的陰毛,他再也抑制不了自己,粗魯地把她放倒,用力去扯她那條寬大的內褲。馮雨花毫無力氣的手無意識地把內褲提了提,當殷世清搬開她的手再次去扯時,她就再也不動。一會兒,一絲不掛的馮雨花仰天躺在寬大的床上把自己的全部都展現開了。馮雨花越來越重的呼吸和越來越清晰的呻吟像一盆火在殷世清心里燃燒,他急急地撲上床去,剛一觸到馮雨花火熱的身子,她就一下把他緊緊地抱住。
這時候那兩頭黃麂突然聲嘶力竭地叫起來“哞——”。殷世清驟然一驚,眼前一團緋紅色的光一閃而過,全身上下霎時冷下來。他無力地搬開馮雨花蛇般的手從她身上爬起來站到地上,那兩頭黃麂又一長一短的叫了兩聲,殷世清腦子清醒了許多,回憶起剛才那會兒馮雨花穿的原是一件被師親妮叫作睡衣的東西。他莫名其妙地打了個寒噤,理好衣服快步向黃麂圈那邊走,慌慌地感覺到黃麂那邊似乎有什么事。
黃麂那邊什么事也沒有。它們安閑地吃著草,見殷世清走過去,習慣地抬起頭來,重又低頭吃草。殷世清長長嘆口氣,剛才發生的事恍若夢中。
殷世清再不敢去房間里,怕馮雨花還沒有完全理好自己。這時的殷世清腦子完全冷靜下來,聽著外面的雨聲,又記起那擔被他忘在屋檐下的草。
剛想出門,殷上樹領著幾個人向這邊奔來。殷世清心虛地喊了聲馮雨花,連忙爬上樓去放架在樓上的毛竹。殷上樹匆匆進門時,殷世清還是按不住滿心里的慌亂,手上的毛竹沒拿牢,一下子落到地上。毛竹落地時的撞擊聲讓剛進門的殷上樹嚇了一跳,殷世清自己也嚇了一跳。
“慢慢來慢慢來,不要慌呵。”馮雨花不知什么時候已經換掉了那身睡衣站在房門邊不遠的地方,抬頭望著站在樓沿的殷世清說。
殷上樹定了定神,看清是殷世清在樓上放毛竹,也跟著說:“殷世清,你慢慢來,小心一點。”
隨來的幾個人將一頭已經落地的毛竹扛起來,小跑著出門。一個響雷就在這時炸開在寬敞的門前,那瞬間的亮光把殷世清站立的地方照得雪亮,馮雨花細心地看到他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木然地搬動那長長的毛竹。
毛竹被他們一根根小心地放到地上。進進出出的人全身都濕漉漉的,屋子里的泥地上沒多久便鋪上了層雨水,有點滑。殷上樹沒有隨大家一起搬毛竹,一直站在門邊看著殷世清一根根往下放毛竹,好幾次很不經意地看了看馮雨花,又回頭看看門外那無休無止的大雨,一臉茫然。
毛竹放完以后,殷上樹隨最后一批搬毛竹的人沖進雨中。殷世清從樓上下來,清楚地看到殷上樹投過來最后的一瞥,心里面不由得又一緊,頓時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馮雨花走過來拍拍殷世清身上的灰塵,又把頭埋進他懷里。殷世清木頭一樣站在那里,心里沒有一點點感覺,滿腦子里都是嘩嘩嘩的雨聲。
片刻,馮雨花見殷世清沒有一點反應,抬起頭望著他說:“你怎么了?”
殷世清就勢推開她說:“沒什么。我還沒有吃過早飯,餓了。”
馮雨花說:“那好呀,我來給你做。”
殷世清沒響,任馮雨花去忙,自己坐在門邊看著屋檐下那擔被雨水澆濕的草,想起師親妮和他的孩子。
那雨還不斷的下著,已經一天一夜了,山澗里的水像一頭被囚了很久的困獸奔騰而出。村前溪水不斷往上漲,低處的幾戶人家都已經進水,屋子年數久一些的開始倒塌,到處是大呼小叫和嘩嘩嘩的雨聲,只有殷世清家這邊靜悄悄的。當初幸虧把屋子建在村子最外邊的山坡上,要不然現在真不知道怎么好。
灶間那邊飄過來飯香,殷世清坐不住了,站起來把吊在窗前鐵鉤上_的一大塊咸肉弄下來,這塊肉還是年前從殷老二家里賒來的,答應說等黃麂今年不再生時就把它賣給殷老二,到時肉錢從那里面除。殷世清的家里除了這塊肉再也沒有其他的菜了。這塊肉之所以沒有吃掉,完全是他沒有心思去弄,燒這東西太麻煩。
殷世清拎著肉到灶間里,馮雨花已經把飯盛進鋼精鍋。她看見殷世清拎著一大塊肉進來,一邊把鋼精鍋坐到灶前剛扒出的灰燼里,一邊說:“你家的肉還沒有吃完呀!去地里拔幾棵青菜來,炒起來好吃。”
“這么大的雨,算了,煮熟能吃就好。”殷世清不想去。
馮雨花道:“你這個男人真夠懶的,那我去吧。”
殷世清忙攔住她說:“好好好我去。”
馮雨花笑了,殷世清不明白這有什么好笑的,找出了師親妮前些年從城里帶回的雨衣,出去拔菜。
殷世清回來時,馮雨花已經把肉切好。放下青菜他就去燒火。馮雨花說:“你現在這么乖,誰教的?”
殷世清沒響,只顧燒火。馮雨花又說:“喂,我說這兩頭黃麂也不會再生了,倒不如把它弄到城里去賣了。一個人不行,我和你一起去怎么樣?到時你也可以去看看師親妮和兒子,不是很好嗎?”
殷世清被馮雨花這么一點撥,心里動了動,很快又恢復了平靜。現在殷世清漸漸地感到自己和這兩頭黃麂有天然的緣份。黃麂已和他的生活緊緊地聯在了一起,他甚至感到這兩頭黃麂身上有一種天然的靈性,要不然剛才正要深入馮雨花身體時,它們為什么要聲嘶力竭的高叫呢?要不是它們叫起來,殷上樹一定撞到了他們正在床上,天曉得要鬧出怎樣的事情。想到這一點他有些害怕,不由瞅瞅馮雨花,他不明白她怎么也會盯上這兩頭黃麂。
雨仍然下著,只是小了一些。馮雨花炒好了菜,殷世清還一個勁地向灶頭里塞柴草。馮雨花叫:“菜燒好了,吃飯吧。”
殷世清回過神來,把灶頭里的柴草退出來塞到灰燼里滅掉,拍拍手站起來說:“一起吃吧。反正你們家一時也不會再做飯了。”
馮雨花笑說:“還用你說,要不給我吃,我才不來燒呢。”
倆人說笑著端了飯菜去堂前吃飯。村子里的喊叫聲還遠遠的傳過來,窗外面的雨已漸漸的小去。殷世清沒注意馮雨花的表情,顧自吃飯。他有些日子沒有吃過這么香噴噴的飯菜了,不禁又想起要把師親妮母子倆接回來。這樣想著就抬頭看了一眼馮雨花,說:“你說那兩頭黃麂能賣多少錢?”
馮雨花沒弄明白他問這話的意思,隨意地說:“我也不知道,要不我們一起到城里去問問吧。”
殷世清感到很失望,重又埋頭吃飯。他原以為她知道黃麂的價值,誰知她也不知道。這一問一答的,殷世清心里又猶豫了,把黃麂賣成錢,又有什么用呢?
雨終于停了下來。殷世清和馮雨花走出屋子。外面的一切都很新鮮,空氣被洗得能夠蕩胸滌肺,山上的森林像是剛出浴的少男少女們,青春勃發。他倆在門前站了一會,馮雨花回頭把換下的濕衣服攏在一起拿回家去洗,殷世清感到一種久違的溫暖正一點點逼近。這都是那頭母麂帶來的,這是頭多么好運的黃麂呵。
天睛以后,村子里的人都忙著重建家園,
只有殷世清很清閑地在家里喂那兩頭黃麂,偶而也到地里去看看已經爬滿畦面的番薯藤。
鄉里派了個民政助理來村里了解受災情況,村支書殷木桶帶他到受災的各家看了看,順便也夸大地上報了村子里總的損失。民政助理應承著說:“我這里好辦,反正也不是鄉里出錢,就是城里那邊不好辦。上次來要過黃麂,我們沒給弄到手,唉,難啊。”
殷木桶干笑著不接茬,跟在民政助理后面走。民政助理說:“哎,那頭黃麂不是還在嗎?動員一下,遲早總是宰了吃的,救濟款下來弄點給他補補損失就是。木桶呵木桶,現在辦事要活絡點,好多鄉村也都盯著這筆救濟款呢。”
殷木桶頭腦里一轉,很快就沒了指望。如果黃麂不給民政助理,這救濟款準不會再有,而殷世清卻是絕不會把黃麂拿出來換救濟款的。除非現在找回師親妮。殷木桶知道師親妮是絕不會再出現在這個村子里了,她和城里面的一個大老板好上,做了大老板的二房,日子過得好著呢,做什么還要回到這窮山溝里來?殷木桶只好說:“讓我試試看吧,大助理你可要多幫忙,我們這里損失最大哩。黃麂的事我一定盡力。聽殷老二說,前些日子差一點獵到一頭黃麂呢。”
民政助理笑笑說:“我是一定會盡力的。其實黃麂也不是我要,是城里管救濟的那個人要,我是替人做嫁衣哪。要不,我和你一起去找那養黃麂的,看看能不能商量商量,最好這次能帶走。那筆款總數不多喲,免得夜長夢多。”
倆人說著走到殷世清的門前。殷木桶老遠就打招呼:“世清老弟,鄉政府派干部來看你啦。”
殷世清放下手里的活,看著不緊不慢走來的兩個人,心里嘀咕:我又沒有受災,有什么好看的?這么多年也沒聽說有人來看一下我。心里這么想,嘴上卻說:“到屋里坐,到屋里坐吧。老遠的路不好走哩,嘿嘿。”
殷木桶和民政助理走進去,東看看西瞧瞧,沒有落座。殷世清跟在他們后面,不知道該怎么樣好。他從來也沒有在家接待過像民政助理這樣高級別的干部。殷木桶踱兩步說:“你那黃麂現在怎么樣啊?”
殷世清連忙說:“還好,沒受災害的影響,長得蠻快的。”
殷木桶就說:“帶我們去看看吧,那東西已經幾年沒看見過了。”
殷世清瞟了一眼殷木桶和民政助理,敏感地想這兩人大概又是為那黃麂而來吧,反正說破了天我也不賣給你們。他領著他們去灶間,順便抱了一捆草去。
兩頭黃麂見有生人進來,站起來豎著耳朵直楞楞地盯著殷木桶和民政助理,表現出一種天生的警惕。殷世清心里感到好笑,連這畜牲也提防著你們呢,你們還看個屁!
三個人一起擠到圈邊,殷世清把青草扔進圈里。黃麂沒吃,還那樣不安地看著兩個陌生人。民政助理見黃麂已經變成兩頭,一下子來了信心,說:“不錯不錯,已經有兩頭了嘛,我說殷木桶,看看看,這是你們村里人的福氣來了。”
殷木桶澀澀地說:“是啊,殷世清,你可要發財了。”
殷世清不想和他們糾纏,說:“我吃穿不愁,發財沒想過,師親妮也用不著我的錢,日子過得去就是了。”
民政助理說:“那是那是。殷木桶,你看這事……”
殷木桶看看民政助理,干脆把事情點明了說:“殷世清,是這樣的,我們村今年損失大,你知道村里人大多窮得很,等著鄉里的救濟款過日子。嗯,城里管救濟款的人一直想要幾斤黃麂肉,殷老二弄了一冬也沒碰到黃麂的腥味,這個……反正你現在也有兩頭黃麂了,你看能不能幫助一下村子里,拿出一頭來?當是村里向你借的吧。救濟款下來后村里按市場上最高的價格加倍給你錢。要不,以后村子里要能弄到活的黃麂,賠還給你也行。”
殷世清看著殷木桶說:“這兩頭黃麂我要留到師親妮回來,只要她還沒有回來,我就一直養下去,哪怕只是讓它們陪著我。錢對我沒用的,師親妮回來會有錢,你們給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賣。”
民政助理看看沒戲,招呼殷木桶走了。
殷世清沒送他們。站在圈子邊看黃麂悠閑的吃草。師親妮什么時候回來呢?他想,真應該和馮雨花去一趟城里,師親妮這回出去的時間也夠長了,頭幾次頂多半來年就要回來一趟。這次已經三年了,孩子也該念書了吧?想著轉身回到房里躺到床上,驀然看見那件被馮雨花穿過的衣服還擱在床檔上,他奇怪地想,馮雨花那天怎么就選了這件睡衣呢?她和師親妮真有些地方十分相同。又清晰的回憶起那個雨天和馮雨花在這張床上……
隱隱約約中,門外有人喊他的名字。喊聲再一次響起時,殷世清極不情愿地起身去開門。
來人見殷世清沒精打采的出來,問:“殷世清是不是住這里?”
殷世清打量了一下來人,那付城里人的派頭讓他頓生戒意。殷世清猜測這幾個人又是沖黃麂來的,想著怎么打發他們,嘴上于是不客氣地說:“這是殷世清的家,什么事?”
剛才在門口探頭的人笑嘻嘻地從袋里掏出一只小鐵盒,抽出一張紙片遞給殷世清說:“這是我的名片。師親妮你認識吧?”
殷世清不明白這人給他這印花的小紙片有什么用,心想大概是什么票吧,就收起來,說:“她是我老婆!”
那人說:“這就對了,你就是殷世清。這地方真難找。”
同來的另一個人把一個小孩領過來,教小孩說:“殷為然,這是你爸爸,快叫啊。”
被叫作殷為然的小孩有點怯,躲回那人的后面,那人便笑著說:“這孩子還認生呢。”
殷世清懵里懵懂的,自己的兒子明明叫殷雨壽,怎么會變成殷為然的?仔細看看那孩子的臉,看出了一些名堂,只一下便認出確實是自己的孩子。他下意識地拉住孩子的手,眼里突然流下淚來。那兩個陌生人說:“我們是和師親妮一起的,師親妮忙,也想著你一個人在家里沒個伴,所以讓我們把孩子給你送回來。好了,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殷為然,你好好聽爸爸的話,叔叔該回去了,過段日子再來看你們。”
那倆人把幾只小旅行包搬進屋子里,其中一個胖些的從袋里掏出一沓錢來說:“殷世清,這是師親妮讓我們捎給你的。孩子就交給你了,這錢請你當面點清。”
殷世清不知道說些什么好,望著面前的孩子和手里那一沓從來沒有見過的百元大鈔,一腦門子糊涂帳,最后任由那兩人向村外走去,直到他們消失在山坳的那邊,才恍然想起應該問一問師親妮的地址,應該告訴師親妮家里平白無故跑來一頭帶崽的黃麂,要是她在城里用得著,過些日子給送去。
這些想法很快便因為面前活生生的兒子而煙消云散。殷世清滿足地看著面前已經比桌子還高出一個頭的殷為然,傻笑著說:“小家伙,累壞了吧?”
殷為然搖搖頭。
殷世清說:“媽媽怎么沒回來?”
殷為然又搖搖頭。
殷世清就不再問,笑嘻嘻說:“走,伯帶你去看一樣東西。”
殷為然怯怯地跟在殷世清的后面向灶間里走去。門檻差一點把殷為然絆倒。他生疏地扶著門檻,委屈得想哭。殷世清沒注意這些,快活地把殷為然領到黃麂圈邊,哄他說:
“你看,這是黃麂哩。沒見過吧,去給它們喂點草,好玩哩。”
殷為然真是沒見過黃麂,在城里他見多了狗啊貓啊什么的,來時還吵著要把家里的那條哈巴狗帶來,領他來的人沒讓,把狗給藏了起來。現在,殷為然看見這比哈巴狗還新奇的東西,拿了一把草就去喂它。殷世清叮囑他在這里玩一會,自己去收拾那幾包東西。
兒子回來了,殷世清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在他看來,兒子回到自己的身邊,師親妮總該也快回來了。不知道她現在是什么樣子了。
殷世清沒想到兒子回來以后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煩惱,不得不央求馮雨花來幫忙料理兒子的生活。殷世清那個被人改了名字的兒子,已經習慣了城里的生活,當天晚上就嚷著要看電視。殷世清一點也弄不明白這個小人兒為什么要看電視,電視有什么好看的?殷木桶前些年從鄉里借回來一臺讓大家看,殷世清也去瞧稀罕了,那小小的屏幕上無非是密密麻麻一片雪花點,還帶一些難聽死的嗞嗞聲,有什么看頭?
殷為然先是哭,后來哭時間長了,嚷著要媽媽。殷世清什么辦法都用盡了,就是沒法哄好兒子,突然就想到讓馮雨花來幫一下忙,便對兒子說:“別哭別哭,伯替你去買買看,你等著啊。”
殷世清就出門去請馮雨花。她聽殷世清說起不經看的電視,笑了,就到了殷世清的家里。
馮雨花看看面前的孩子,說:“你這么大了還哭,真不好意思。我們這里電視接收不到信號,沒法看見。過些天阿姨領你回城里去吧。來,阿姨給你講故事聽好不好。”
殷為然還哭。馮雨花不管他,讓殷世清換了床干凈的被子抱著殷為然上床講故事:
從前這里的山上住著一個漂亮的公主,公主養了很多很多的黃麂,種了很多很多的鮮花,還搭了一座非常非常漂亮的紅房。美麗的公主把房子里面涂得五彩繽紛,又在房子南面開了一只圓圓的小窗,找來一枚猩紅的楓葉做那小窗簾。每天太陽一出山,公主就從小房子里出來,給鮮花澆上一遍水,再趕著她那群心愛的黃麂出去放牧。
有一天,美麗的公主趕著黃麂走得很遠很遠,來到一個從來也沒有來過的地方。這地方真美呀,滿野是青青的草,草叢間開著各色各樣的鮮花,鮮花四周色彩斑斕的蝴蝶翩翩起舞。原野的邊緣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小樹林,從小樹林里面飛出來又飛回去很多很多鳥兒。公主被這美麗的景色迷住了,站下來高興得唱起歌來。
公主的歌兒很好聽,順風飄得很遠很遠。那些黃麂也忘了吃肥嫩的青草,仰起頭來聽公主的歌聲。有一頭黃麂聽著聽著就走過來躺倒在公主的身邊,目不轉睛地看著公主。
突然,從草叢里跳出來一頭大灰狼,直朝山坡上一頭小黃麂沖去,一口咬住小黃麂就跑。公主一聲驚呼,急得流下淚來,這頭小黃麂是公主最喜歡的。怎么辦呢?正焦急時,躺在身邊的那頭黃麂忽然開口說話了,它說:“美麗的公主呵,你不要流淚,我去替你追回來吧。”
公主很奇怪,是誰在和她說話呢?那頭黃麂繼續說:“美麗的公主呵,你把你的淚水抹在我的鼻子上吧,你的淚水可以增加我百倍的體力,我會追上那頭狼,把它抓回來見你。”
公主終于聽清是黃麂在跟她說話。她來不及多想,把自己的淚水抹在黃麂的鼻子上。那頭黃麂一下子站起來像利箭一樣向狼逃跑的方向沖去。公主擔心地暗暗為那頭黃麂祈禱。
過了好一會兒,公主終于看見遠處的小樹林邊,那頭黃麂和被狼叼走的小黃麂押著餓狼回來了。公主高興極了,從此對那頭黃麂格外寵愛。
日子過得很快。這天那頭黃麂又開口說話了:“美麗的公主呵,我想變得像你一樣,讓我們永遠在一起。”
公主說:“我們怎樣才能在一起呢?你是黃麂,我是人啊。”
黃麂說:“你每天用你的眼淚抹我的鼻子一次,抹到七七四十九天,我就會變成人了。”
公主說:“那好吧,從今天開始我就給你抹。”
黃麂說:“可千萬要記住,七七四十九天,一天也不能斷啊,要不然我會變成石頭的。”
公主說:“你就放心吧,我手里有一個魔匣呢,它會提醒我的。”
于是,公主開始每天在黃麂的鼻子上抹眼淚。有時候沒有眼淚,公主就用剛采來的辣椒水刺激眼睛,讓眼淚流出來。七七四十九天馬上就要到了,公主看著一點也沒有什么變化的黃麂想,它怎么會變成人呢?最后一天,公主眼睛很疼,躺在床上整整休息了一天。翌日早晨,公主想起黃麂說的話,到黃麂圈里一看,一個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里面朝她微笑呢。公主驚喜地說:“你真變成人啦!”
那小伙子傷感地說:“公主,看來我們是有緣無份了。我馬上會變在石頭的,昨天你為什么不給我抹眼淚了呢?”
公主后悔莫及,淚像雨水一樣落下來。她傷心地說:“還有什么辦法能夠補救嗎?”
小伙子說:“沒有了,我們只有永別了。”
說著,小伙子的腳慢慢并攏,從下到上開始變成石頭。公主跑過去緊緊地抱住他,一會兒便覺得抱在懷里的身體越來越冷。小伙子已經成了一塊人形的石頭。公主放聲痛哭了三天三夜,后來,公主發誓一定要找到一種讓石頭復活的神藥,就趕著她的黃麂群在山里面到處流浪,到現在還在尋找那種神藥呢。
殷為然眨眨眼睛問:“那后來呢?”
馮雨花認真地說:“我也不知道,過幾天待你伯有空了,我們一起去找找那間紅房子,只要能掀開小窗子的紅楓葉,我們就可以看見那個公主,就可以知道公主有沒有找到神藥,有沒有救活那小伙子了。”
殷為然抬起頭問:“阿姨,真的嗎?我們一起去啊。”
馮雨花笑著說:“好吧,不過,現在我們睡覺好嗎?”
殷為然說:“我要阿姨陪我一起睡。”
馮雨花點了點頭幫他脫掉衣服,和他一起躺下。一會兒,殷為然就甜甜地進入了夢鄉。
殷為然的到來,給殷世清的生活平添了許多情趣。殷世清不再那么想念師親妮了,偶爾想起也不再那么強烈。只是他的兒子殷為然不怎么喜歡和他在一起,整天守在黃麂圈旁,一到晚上就念叨著他的馮雨花阿姨,要她來講故事。馮雨花每天都來陪殷為然,給他講故事聽。馮雨花在做著這一切的時候,殷世清只會坐在一邊望著他倆傻笑。夜里,馮雨花哄殷為然入睡回家后,殷世清躺到馮雨花睡過的那塊地方,嗅著她留下來的氣息,時常會生出許多遐想。
日子在機械的日升日落里過去,夏天悄悄地到來。殷世清不再為黃麂的飼料發愁了,開始準備一年一度的夏收,心里打算在夏收后弄點現錢來,給兒子添幾件衣服。
殷為然和那兩頭黃麂很快親近起來。他給它們分別取名為貝塔、皮皮魯,殷為然一走過去,那兩頭黃麂就興奮得站起來,深情地朝他看著,像老朋友一般。殷為然沉浸在童話世界里,也不再提那個遙遠的電視了。
一天,殷世清到地里去弄飼料,殷為然一個人在家。他奔進黃麂圈邊弄開圈門鉆進去。兩頭黃麂已經和他很熟,根本不害怕,都依偎過來。殷為然抱起那頭小的說:“皮皮魯,我放
你出去找美麗的公主好嗎?你一定要找到她呵。”
黃麂不知道小主人想干什么,伸出舌頭溫柔地舔著殷為然的小手,抬起頭來望他。殷為然把黃麂推到圈門邊,朝它說:“皮皮魯,快去吧,找到公主再來叫我啊。”
那頭小黃麂怯生生地走出圈門,圍著圈慢慢地轉著。殷為然急了,跑過去把它趕了出去。小黃麂在門外猶豫了一下,終于向遠處的山林跑去,一會兒便消失在茫茫的山林里面。殷為然快樂地笑了。
殷世清回到家里,發現黃麂不見了,問殷為然:“你看見黃麂往哪里跑的?誰來過了?”
殷為然搖搖頭,怯怯地看了殷世清好長時間才說:“皮皮魯去找公主了。”
殷世清不由發火,問:“是你放走的?看我打死你。”
殷為然害怕地說:“我讓它去找公主了,它會回來的。”
殷世清很懊惱,自己怎么會生了這么一個傻兒子,真想一巴掌打過去,可又不舍得動手,回到圈邊把圈門弄死了。
晚上殷世清跟馮雨花說,別再給殷為然講那黃麂的故事了,說點別的吧。馮雨花笑笑,在殷為然的一再糾纏下,還是說起了公主的故事。最后,她告訴殷為然說,公主為了找藥,已經離開了這片森林,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再也不會回來。
殷為然一下子從床上跳起來說:“壞了壞了,皮皮魯找不到公主了,我也再找不到媽媽了。”
殷世清一驚,這孩子的小心眼兒可真是深,面子上沒露出一點想媽媽的神情,肚子里卻原來每時每刻都想著他媽呢。記得馮雨花對殷為然講過,公主有一塊魔鏡,在那里面可以看到自己要想見的任何人。他這才明白,殷為然放走黃麂是為了到公主那里去找魔鏡,這孩子沒有忘記他媽呵。這樣想著,殷世清也忽然懷念起師親妮來,一團緋紅色的光芒經久不息地在他眼前晃動。殷世清怎么也回憶不起師親妮的臉,只剩下這團緋紅色的光芒還深深烙在他記憶深處,讓他的心隱隱作痛。
這天晚上,殷世清待殷為然睡熟后留住馮雨花說:“這孩子想媽呢,我想夏收后把黃麂抬到城里去賣了,領孩子找她媽去。”
馮雨花說:“怎么,又想老婆了?”
殷世清說:“雨花,我不識字,想找你一起去。”
馮雨花說:“我可不去。你不怕殷上樹吃了你,我怕呢。除非……”
殷世清急急地追問:“除非什么?”
馮雨花定定地看著殷世清說:“除非你帶我走,永遠不要再回來。”
殷世清一下子覺得她的話有點古怪,自己怎么好帶她走呢?她畢竟是本家親戚殷上樹花錢弄來的老婆啊。他訥訥地說:“這怕不行吧,你是我本家哩。”
說這些話時,殷世清心里涌過一陣莫名其妙的感覺,不由抬頭看了看馮雨花微微發紅的臉頰,又重新低下頭去。他感覺到了馮雨花近在咫尺的胸脯正在急速起伏。
馮雨花猛地撲到殷世清的懷里,沒等他回過神來,她就把自己的身子和他緊緊貼在一起,手忙腳亂地去拉他的衣衫。殷世清只覺得自己的身子一下子飄起來,馬上想要干點什么,眼前一片緋紅。
殷世清正在興奮中,馮雨花突然說:“我們到床上去吧。”
殷世清又仿佛感覺到一股火熱的東西霎時離去,冥冥中似聽到灶間里那頭母麂輕聲的在呼喚什么,門外也隱隱地傳來低聲的呼喚。他掙脫開馮雨花的雙手,向門外走去,打開門的一剎那,一樣東西箭一樣向他沖來。殷世清本能地一閃,那東西徑直朝灶間里奔去。殷世清心里一喜,是那頭跑走的黃麂回來了。
灶間里傳來一陣親昵的聲音。殷世清走回房間,沉浸在黃麂回來的喜悅中,興奮地向馮雨花說著黃麂的事。她耐心地聽著,最后說:“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殷世清呆了呆,嘆口氣說:“你是殷上樹的老婆,人家是花了錢的。我殷世清再怎么,也不能做傷害本家人的事啊。”
馮雨花有點惱,說:“我怎么是殷上樹的老婆了?我身上哪地方印著是他老婆了?殷世清,你真是沒出息。你知不知道師親妮在城里做什么事?告訴你,我現在并不是誰的老婆,和殷上樹沒有登記,我還不能真正算是他老婆!我愿意給你,你為什么不要?”
殷世清看著她,無言以對。
馮雨花哭了,說:“告訴你,自從我被賣到這里以后,沒有哪一天不想離開這里,離開這個閉塞的地方。可是我過不去那條大河,我想只有你能幫我,不論你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跟著你,做你的老婆,只要你帶我去外面的大世界。”哭著哭著又偎到殷世清的懷里,越哭越兇。殷世清不敢再看滿面淚痕的馮雨花,心里卻想,師親妮在城里到底是做什么呢?
不知過了多久,馮雨花不哭了,她看見殷為然啥時候已經醒來,眼巴巴地望著他們兩人發呆。馮雨花就收拾好自己的衣服,匆匆跑出廂房。殷為然什么也沒有問,又一聲不吭地睡下。殷世清想,這孩子長大了哩。
夏收以后,村里人很少看到殷世清從家里走出來。馮雨花也不再天天到他家去,最后一次,她半真半假地嚇唬殷世清,如果他不帶她走,就把殷世清要和她做那事的事告訴殷上樹。那次以后,殷世清就心事重重,悶悶不樂,有時候整天坐在自家的門檻上望著遠處的山巒出神。
殷為然已經熟悉了村子的環境,和村里的孩子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用不著再讓馮雨花編故事來哄他了,殷世清重又感到非常的寂寞,時常又想起師親妮。師親妮在城里到底做的什么事呢?他沒日沒夜的想,怎么也想不明白。
過了一段日子,馮雨花再次去殷世清家討答復時忽然發現殷世清已經消失了多時,屋子里到處是蛛網還有老鼠走動的聲音,灶間那兩頭黃麂也沒有了。馮雨花無助地感到自己心里陡然空了,很是絕望。她十分后悔地想著以前的事,悔不該那么逼他。她想象著殷世清能到什么地方去,想得心口疼痛起來。灰心地回到家里,一病不起。
村子里似乎沒人特別注意殷世清和他的孩子,時隔一段人們才聽說殷世清失蹤了。人們多半說這傢伙大概是去城里找他老婆師親妮去了,沒人把他和馮雨花的病聯系在一起。
馮雨花的病到了當年的冬天才好。那天,她頭一次從床上起來,摸著板壁和椅子一步一步挪到門前,驀然看見天上紛紛揚揚的大雪,自言自語地說:“殷世清還欠我的番薯藤呢。”
家里人不明白她念叨這干嘛,都勸她說:“那點番薯藤算什么?等他回來再說吧。”
馮雨花把眼瞪得大大的,說:“你們懂個屁。”
村里人頭一次聽馮雨花罵人,感到挺開心。久病初愈的馮雨花骨瘦嶙峋,弱不禁風。大伙兒讓著她,不跟她爭。風雪中的馮雨花像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婦女,變得十分難看,連殷上樹也有些懶得理她了。
外面的雪一陣緊似一陣,馮雨花望著大雪發呆,想著不知在何方的殷世清。在她的眼里,殷世清才是能給她希望的男子。現在,她多么渴望有那么一頭黃麂向她跑來,她堅信這黃麂是好運的,可以領她走出這個幾年來仍然還是感覺陌生的小山村,回到她熟悉的地方去。
這以后,馮雨花陸陸續續的聽說殷世清
找到師親妮了;也有人說在山里面看見他,正在找他丟失的黃麂,還領著他的兒子殷為然;也有的說他把那兩頭黃麂賣給了一個老板,老板留下他在那里幫忙,不回來了。馮雨花不愿輕信人們的種種猜測,想象著殷世清現時的情景,人變得愈加憔悴。
又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天氣,殷上樹一早起來,發現馮雨花赤腳立在雪地里,癡癡地望著遠山。殷上樹上前拉她時才發現,馮雨花瘋了。瘋了的馮雨花不斷說著一些亂七八糟的話,一拉她就要打人。后來,馮雨花動不動就拿了把柴刀到處砍人,有次竟然把自家的房子也點燃起來,要不是發現得早房子差點燒掉了。殷木桶見馮雨花已經瘋了,便想把她送回老家去。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也不知道馮雨花的老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夫妻了幾年怎么會這樣,現在怎么好呢?
快要過年了,大家忙著辦年貨。一天早上,殷老二發現對面山上有黃麂一閃,立即回家背了槍來。經過殷上樹家門口時,瘋子馮雨花兩眼放光地望著山那邊,順著她的視線,殷老二看見了兩頭黃麂,這時馮雨花已經狂笑著向黃麂出現的方向跑去。獵手殷老二也急忙攆去,可怎么也追不上她,他眼睜睜地看著馮雨花消失在茫茫大雪里,和那黃麂一起不見了。
當天晚上,馮雨花沒有回來。殷老二始終也沒有追上那兩頭黃麂,他回到村子里逢人就說,那黃麂真是怪了真是怪了,馮雨花這女子跑得也太快,要不然那黃麂說不定不會跑走的,這個瘋女子!第二天馮雨花還是沒有回來,已經一夜了,她會到那里去呢?
吃過早飯,殷木桶動員全村老少去山里尋找他婆娘,終于在山那邊的雪地里找到了被凍僵的馮雨花。她身上已經薄薄地覆上一層潔白的雪,像是一層暖和的被子,把她蓋在寬廣博大的山地里。村子里的人都沒有說什么,這個瘋女人也真是活受罪,好好的做殷上樹的老婆有什么不好?女人在哪里不是生孩子燒飯?幾個年輕的小伙子在殷上樹的招呼下,把她抬到一塊門板上,用家里拿來的一床破被蓋了,按照習俗沒敢抬回村里去。過了幾天,殷木桶把馮雨花埋進自家的墳地里,從此不再向別人提起這個女人。一切都是命定的。殷木桶這樣想。
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議論起殷世清和他們家的人,殷世清空蕩蕩的家門前,漸漸就長出許多不知名的雜草來。村子里的人經過他的門前,也草草地看幾眼他家的大門,都想著殷世清這回是發大財了,以后有倒霉的時候,最終還是要回到這個小山村里來的。逢年過節閑下來的時候,也有人想起那頭雪天里跑來的黃麂,都說它能賣好多的錢,都在想著自己有殷世清這樣的運氣該多好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這塊地方,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再看見過黃麂,這東西好像永遠在這里消失了,不再回來。不知怎么的,每當大雪紛飛還是有人會莫名其妙地說起那頭帶崽的黃麂以及有關黃麂的種種傳說。
責任編輯舟揚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