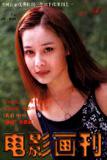在烏克蘭煉“鋼鐵”
文/韓剛
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在中國廣為流傳,前蘇聯拍攝的電影也曾在中國放映,產生過很大影響,此次重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我來說既新鮮又富挑戰性。也許正是因為前蘇聯曾拍過三版,此次我們的中國版才更有意義。
我是伴隨著前蘇聯文學、詩歌、繪畫和電影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四十歲以上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樣,不僅熟悉前蘇聯的藝術作品,甚至今天仍能背誦,不少蘇聯歌曲張口就唱。畢竟中國與蘇聯曾同在一個陣營,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是“同志加兄弟”的關系。我正是懷著對前蘇聯藝術大師們的崇敬與對烏克蘭人民的情誼踏上了這片土地。
“你們為什么要重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初到烏克蘭便遇到無數記者的相同提問。他們對中國人來拍自己民族的故事感到新鮮,這在情理之中,但他們幾乎相同的疑惑表情也著實有些令人納悶兒。后來當我看到博雅爾卡那已塵封多年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才清晰地感受到獨立后的烏克蘭意識形態已與從前大相經庭。自由以及“多元化”的社會已經使他們的年輕人對保爾·柯察金越來越陌生……當然,這并不妨礙許多熱心人對我們的支持,尤其是杜甫仁科電影制片廠的大力協作。
烏克蘭的冬季非常寒冷。為了趕上季節,我們首先搶拍保爾修鐵路的戲,由于人物眾多,場面宏大,組織拍攝相當艱難。但幾天之后我便發現最為艱難的還不是拍攝,而是技術問題。雖然杜甫仁科電影制片廠歷史悠久,工作人員都很專業,但他們沒拍過電視劇,甚至自烏克蘭獨立之后,由于經濟衰退,連電影也很少拍。拍攝中烏克蘭攝影師對攝相機的性能及操作難于掌握,接二連三地出現技術故障。拍了一段時間之后,我有一種體會:實際上我是在帶領烏克蘭電影廠的第一支電視劇攝制組拍戲,一切有如回到了中國電視劇剛剛起步的八十年代初。百般無奈之下只好撤換攝影,從國內急調攝影和照明重新來過,否則質量實在難于保障。
與攝影的技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演員個個非常出色。這當然與烏克蘭深厚的戲劇傳統有關,至今他們的許多劇院幾乎每天都有演出,話劇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種藝術形式。演員每天都在與觀眾直接交流,這種歷練是很難得的。因此,烏克蘭演員的心態和狀態都極好。無論老演員還是青年演員都非常敬業。
此次中國人重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烏克蘭也算一件大事,自然吸引了眾多烏克蘭最好的演員前來參演。許多與影視久違了的演員們穿上服裝就不舍得脫下,甚至拍完戲不愿走,一直看攝制組拍戲至半夜才回家。許多烏克蘭的人民演員、功勛演員、著名的老藝術家只在劇中扮演一個小小的角色,這也許是我們的整體表演水平保持高水準的根本原因。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最關鍵的演員無疑是飾演保爾·柯察金的人選。正當我們憂心忡忡的時候,一名烏克蘭“左岸”劇院的青年演員安德烈·薩米寧正在默默地期待著我們的挑選。他形象消瘦,棱角分明,有些局部很象58年版的保爾,但又比那個保爾柔和一些,也可愛一些。經過試妝,我們認為,僅從形象上看保爾非他莫屬,但是否能勝任表演,我著實替他捏著一把汗。在以后的拍攝過程中,他的表現一再驗證了我們當初決定的無比正確。第一,安德烈·薩米寧演戲非常地投入。也許因為這是他初登屏幕,心里壓力很大,故格外重視。他用心體會人物的每一細微心理,尋找到塑造人物的真實、合理、恰當的方法。我時常見他蹲在角落里沉浸于戲中,激動處以至于渾身顫抖。第二,安德烈·薩米寧經常會提出自己的見解。我一向認為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見解,是作為優秀演員的前提,見解必定是他從再創作的思考中提煉出來的,其用心與執著難能可貴。拍攝現場,他經常要求反復試戲、反復琢磨,而且都象實拍一樣,即使是“打戲”也要遍遍真摔,決不偷懶。第三,在安德烈·薩米寧身上體現出一個職業演員為藝術獻身的精神。由于劇中人物保爾·柯察金的特殊經歷,演員在塑造人物時必然是相當艱苦的,他要經歷挨凍、挨餓、挨打,以及殘酷“戰爭”的種種磨煉與考驗,安德烈經常傷痕累累。一天拍謝寥沙犧牲前推保爾跳崖逃生一場戲,其實這個鏡頭完全可以用替身,但為了使這個戰爭場面真實連慣,他要求自己來演。從十幾米高的河岸上躍下,跳進河中,這確實很危險,如果是在國內拍戲,這樣的場面對任何演員來說都不敢調以輕心。
總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的扮演者安德烈·薩米寧,從形象、氣質到表演都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當然其他如飾演冬妮婭、朱赫萊的演員也都很棒……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拍攝到后期完成經歷了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預計將于年底完成,屆時我相信將奉獻給觀眾一部既新鮮又好看,而且雅俗共賞的電視劇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