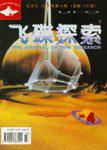能往火星之路(四)
鐘建業

合作還是單干?
前不久,美國航空航天局向白宮提交了一份文件,內容包括對下世紀初人類開發宇宙空間的前景介紹。根據起草者的計劃,第一個人類的空間居住區將會于2017年前在月球上建立。10年之后,還會將其建至火星。其發展步驟如下所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在近地軌道上建立大型軌道空間站,用以逐步積累迄今為止美國宇航員還很缺乏的遠距離飛行的經驗。此外,從根本上改變未來宇宙飛船的開發途徑,其明顯的特征是從火星或是它的衛星上取材,加工成推進系統的燃料。在載人飛行之前,首先要把自動化加工場發送到那些擁有原料的天體之上,爾后再從中開發燃料。另外,還計劃著手研究一種類似于溫室的所謂“自給自足生物圈”。
從總體上說,這個計劃內容廣泛且頗具吸引力。但如果美國政府有意施行這一計劃,我們也早該在對火星的探測中目睹這些大型研究項目的實施了。美國科學家始終在抱怨政府對航天飛機的熱情已經燃盡了所有的預留資金,其中不僅有用于火星研究的,還有其他很多研究項目的經費。最近剛剛得到美國主管部門批準的空間軌道站的資金,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還是被削減掉了,其實這個項目的實施日期就一拖再拖。任何人都很清楚,如果政府集中所有的力量在星球大戰計劃之上,那么對月球與火星的探測就只能是海市蜃樓。目前五角大樓對軌道空間站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正在努力扶持這一計劃以達到一系列的軍事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誰還認為探測火星的項目中有多少余地的話,那他真是太天真了。
登月計劃耗費美國政府250億美元。載人火星飛行計劃的開銷將是這個款項的10倍,那將是2500億美元。這筆花費究竟算多還是算少?這就取決于當局者的觀點了。此款項的總數可比五角大樓的年度預算要少得多。可話又說回來,有一次美國航空航天局甚至湊不出區區10萬美元以支持“旅行者”號的探索計劃,最終他們還是求助于私人贊助商才使項目得以實施。美國著名科學家卡爾·薩根曾不無諷刺地寫道,研究哈雷彗星的經費等于開發一枚戰略導彈的資金。但事實則完全不是這樣,這不過是因為某些實權人物總是認為,如果沒有導彈的話,美國安全將會受到嚴重威脅。
當然,像載人火星飛行這樣的計劃,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如果能夠將其建立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則只需適當地減少軍費開支,那這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許多美國科學家都支持在空間開發上美國和前蘇聯之間進行更廣泛合作的觀點。特別是卡爾·薩根,他熱誠倡導多國合作開發載人火星飛行計劃,其中包括前蘇聯和美國。
他認為近地軌道上對載人火星飛船的組裝將會始于1992年,其時正值前蘇聯10月革命75周年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周年紀念。
在這種趨勢中,另一個新舉措就是美國將加入福博斯的合作計劃。
漫談火星蘋果樹
要是沒有陽光的話,地球上的有機物就會生長得很差。那些曾由南方飛往北方的旅行者都能深深體會到這種植被的變化。例如,高大的樺樹逐漸變小,以至于在與凍土地帶接壤的地方,最終只剩下了地苔。
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曾有一首歌曲這樣唱道:“宇航員和科學家們總是告訴我們火星上快長出蘋果樹啦。”在幾十年前,人們就這樣夢想過,可直到現在,我們才認識到火星上的生命只可能生活在人造氣候的環境中。目前的問題是蘋果樹能否在玻璃容器中生長以及它們長大后會是什么樣。
火星上自然沒有蘋果樹所需要的充足的陽光,但可以用某種設施,比如鏡子使光線發生聚集,然后照射在蘋果樹上。火星上有與地球上相同的季節變化,只不過每個季節的持續時間都是地球的兩倍。至于蘋果樹在這么長的季節里會做出何等反應,這還很難說 。
火星的引力比地球弱,那里蘋果樹應該有地球上的兩倍高。有可能它的樹干沒有地球上的那么粗壯,但還有可能它會像地球北部的蔓生植物一樣生長。
至于火星上的工作人員,顯然,他們必須采取特殊的措施,如同那些空間軌道站上的宇航員一樣,確保身體不會過于習慣于火星上較弱的引力效應,否則他們將很難再適應地球的生活。也許他們必須進行高強度的體育鍛煉,也許需要在食物中增加鹽分,或者用其他什么手段——總之目前還無法下定論。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經過多次實驗,前蘇聯專家們終于將生命維持系統構建到宇宙飛船和軌道空間站中。如果要在火星上發展人類居住區,也類似地要把這個系統先移植到火星上。而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什克就構建了此類系統。它被稱為“Bios”,其實就是一個溫室,室內植物的生長完全依靠封閉的物質循環。經過測試,這個系統也有一些改進。早在1964年,就有第一批植物被送進“Bios1”號中。溫室雖然只有12立方米,但是科學家們還是通過綠藻成功地獲得了全部的再生水和空氣。而后續的實驗對象將主要是谷物和蔬菜。
現在的“太空蔬菜園”共有3個人工氣候室。在這些暗箱里,植物完全生長在人工控制的環境中。種植面積達60平方米的植物足夠為5個人的生活提供氧氣。其中一種植物就是小麥,但它并非普通的種類。氣候室中的植物生長環境是很理想的,普通的谷類在那里都能長到1.5米高。但我們并不需要那樣,因為在如此高的植物內,有相當部分的營養物質都會用于莖的生長。在西伯利亞工作的科學家為“太空田”研究出一種矮小但產量奇高的麥種,1萬平方米的產量可達13噸,而且一年中能有6次收割期。另外還有多達15種的新型蔬菜,其產量比地球上的普通品種高出5倍~8倍。
目前,生長在人工氣候室中的植物的“地球模擬飛行”有時持續6個月之久。氣候室能滿足人3/4的食品需求,可是其中不包括肉類和動物脂肪。但用人工氣候室中的蔬菜做湯、沙拉和裝飾菜都是可以的。因此,在火星上建造一個封閉的生物系統是可行的。然而,并非所有的產物都可以再生;這也是為什么說自給自足生物圈還是一個遙遠的夢想的原因。人工氣候室不只用來滿足宇航員的需求,其生產和各種種植方法同樣可以滿足地球上的需求。特別是位于克拉斯諾·亞爾什克的“太空”溫室,除了達到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它也用于為頗具經濟效益的新種谷物進行培植和分區。在火星探測和谷類劃分之間,不只是它們之間的地理距離,好像無論從哪方面看,都相差著十萬八千里。但是目光長遠的人們認為,這說明行星探測一定會對人類大有裨益,遲早它會為地球帶來很高的技術回報。早在20世紀初,現代空間科學的奠基人康斯坦丁·喬爾科夫斯基就曾經預言過人類的太空飛行和行星探索。
人類向火星的飛行將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探索太陽系的最重要的一步。對其技術上的可行性,我們沒有任何懷疑。但是,我們還要把目光放得更遠些,并且更多地考慮一下怎樣改造火星的自然面貌。
不難想像出一個巨型光鏡系統,它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火星表面吸收的太陽能。那樣恒久的冰冷將由溫暖的氣候取而代之。作為“第二個地球”的火星,勢必將迎來一個燦爛輝煌的新時代。
董兆惠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