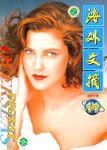爵士,吹出一生的故事
劉 軒
這個(gè)地方很神秘,全紐約沒(méi)有幾個(gè)人知道,即使你到了格林威治村東區(qū),走到“它”的門口,只怕都認(rèn)不出來(lái)。
這是一家外表很不顯眼的咖啡廳,進(jìn)去直走,經(jīng)過(guò)酒吧,繞幾道墻,經(jīng)過(guò)廁所和賣香煙的機(jī)器,后面廚房旁邊有個(gè)小樓梯,下去之后右轉(zhuǎn),再過(guò)一條窄窄的走廊便到了……一個(gè)黑暗、擁擠的小房間,裝滿了紐約最酷的人和最酷的音樂(lè)。
臺(tái)子上擠了4個(gè)人、4種樂(lè)器:鋼琴、貝斯、鼓、喇叭。這首曲子節(jié)奏很快,打鼓的棍子劈里啪啦地飛,喇叭手更是在盡情地發(fā)揮。
“好!”有人叫。
吹出一生的故事
我很少看過(guò)有人吹喇叭這么賣力的:他緊閉著眼睛,滿面通紅,臉頰鼓成兩個(gè)汽球,汗珠在他額頭上抖動(dòng),一根青筋在脖子上扭曲……更驚人的是那喇叭聲,每個(gè)音符都好像滲進(jìn)了他的血。
我旁邊的人搖了搖頭:“這家伙可正在告訴我們他一生的故事啊。”
其實(shí)每次講到紐約,我就會(huì)想到爵士。
雖然林肯中心有古典音樂(lè)、街頭有打擊樂(lè)、夜總會(huì)里有搖滾,但當(dāng)我晚上站在對(duì)岸,看到整個(gè)燈火輝煌的曼哈頓展現(xiàn)在眼前時(shí),我心里聽(tīng)到的卻是那喇叭手吹出的曲子。我想這是因?yàn)榫羰亢图~約一樣,復(fù)雜、直爽、世故,難怪當(dāng)它在1914年從新奧爾良來(lái)到這大城之后,就一直沒(méi)走。
爵士樂(lè)的首創(chuàng)者是非洲黑奴,以前他們冒著生命危險(xiǎn),深夜時(shí)在森林里聚集,拿著白人的喇叭和吉他,吹彈出自己的心聲。旋律中,可以感覺(jué)他們身上的鞭痕、失去的家、被賣掉的兄弟。身為奴隸,把心里的傷痛轉(zhuǎn)為藝術(shù),是他們唯一的訴苦方式。
最早的爵士樂(lè)手常說(shuō):“你沒(méi)過(guò)這樣的日子,就甭想彈出這樣的音樂(lè)!”
他們也從來(lái)不解釋自己的曲子。有人曾問(wèn)一位有名的喇叭手,為什么他的旋律是這樣那樣,得到的答案是:
“你干嘛問(wèn)為什么?你自己的耳朵不會(huì)告訴你嗎?你少用分析,多去感覺(jué),說(shuō)不定能聽(tīng)到我的故事。我是在跟你說(shuō)故事啊!”
所以,爵士常是不用譜子的。同一首曲子給3個(gè)人彈,會(huì)有3種不同的旋律,因?yàn)樗麄冇?個(gè)不同的故事。
曲子完了,大家不停地叫好,有人大聲吹口哨。
彈琴的站了起來(lái),拿過(guò)麥克風(fēng):“各位知道爵士這個(gè)詞的由來(lái)嗎?”
很多人搖頭。
“它以前是臟話,”他停了一下,“現(xiàn)在我就要把它原本的意思,彈出來(lái)給大家聽(tīng)聽(tīng)!”
大家都笑了,熱烈的鼓掌,有人跳起來(lái)歡呼。
下層社會(huì)的文化暗流
我心想,中文的翻譯,真差遠(yuǎn)了!
最早的時(shí)候,爵士是一種文化暗流,爵士樂(lè)手曾被認(rèn)為是社會(huì)的下三濫之一。想聽(tīng)爵士,得去城里最陰險(xiǎn)的地方,曲子聽(tīng)到一半響起槍聲也不奇怪。它早期的擁護(hù)者多半是不良分子,20年代,更是黑手黨最喜歡的音樂(lè)。
后來(lái),越來(lái)越多的白人學(xué)會(huì)了爵士,把它發(fā)揚(yáng)光大,進(jìn)了舞廳。臺(tái)上,15、20人的大樂(lè)團(tuán)用爵士的方式奏起響亮的舞曲。臺(tái)下,瘋狂的聽(tīng)眾從傍晚跳到天亮。爵士居然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
有人說(shuō),藝術(shù)一旦跟錢搞在一起,就沒(méi)有藝術(shù)了。可惜,爵士也不例外。許多唱片公司為了搶爵士熱,只關(guān)心大眾是否喜歡、賣錢是否容易,卻忘了音樂(lè)家的要求。我聽(tīng)過(guò)一個(gè)故事,一位唱片制作人告訴正在錄音的薩克斯風(fēng)手,他吹的旋律太復(fù)雜,平常人無(wú)法接受。那位音樂(lè)家一氣之下,便故意把曲子吹得像兒歌一樣。沒(méi)想到制作人跳起來(lái),猛跟他握手:
“謝謝!謝謝!這就對(duì)了!”
哈佛有位教授,是個(gè)著名爵士樂(lè)團(tuán)的團(tuán)長(zhǎng),還開(kāi)了個(gè)純爵士樂(lè)的唱片公司。有一次和他聊天,他嘆著氣說(shuō):
“自從弗蘭克·西納特拉在臺(tái)上跟大樂(lè)隊(duì)紅起來(lái)之后,主流的爵士就不是爵士了。你聽(tīng)聽(tīng)現(xiàn)在他們吹出來(lái)的旋律,簡(jiǎn)直是糖精!哪里有故事?問(wèn)題是,他可以賣六、七百萬(wàn)張唱片,而我最欣賞的爵士樂(lè)團(tuán)。能賣個(gè)十萬(wàn)張就笑得合不攏嘴了。”
商業(yè)化令人心痛
不久前,哈佛那位教授作了一首曲子,被提名格萊美獎(jiǎng)。他告訴我,去參加頒獎(jiǎng)典禮,看到音樂(lè)事業(yè)是多么的商業(yè)化,實(shí)在令人心痛。
“我想,爵士樂(lè)家,總要面對(duì)一個(gè)問(wèn)題……他是彈自己的爵士呢,還是彈人家的爵士?”他說(shuō)。
“你是怎么決定的?”我問(wèn)。
他苦笑了一下:“我現(xiàn)在不正教書(shū)嗎?”
我想,并不是沒(méi)有人想聽(tīng)暗流的爵士樂(lè),問(wèn)題是他們有沒(méi)有辦法聽(tīng)到,還有,聽(tīng)到之后會(huì)不會(huì)喜愛(ài)?
我永遠(yuǎn)記得。那天在小小黑黑的地下室,一群人無(wú)拘無(wú)束,用音樂(lè)分享他們心境的那種感覺(jué)。
每一段音符都說(shuō)出一段喜怒哀樂(lè)的故事,說(shuō)到很久很久以前,也說(shuō)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沒(méi)聽(tīng)懂,卻也懂了!
[摘自馬來(lái)西亞《南洋商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