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天生的勇士
齊魯青
“這孩子天生膽大。”
“這孩子天生膽小。”
這是我們常常聽到的話。但是,其中只有一句是對的:“這孩子天生膽大。”
孩子的膽量是怎樣形成的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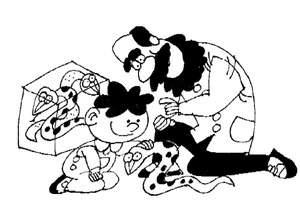
國外兒童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實驗。科學家將兒童分為1歲組、4歲組和7歲組,讓他們分別接近一只小白兔和一條無毒小花蛇,觀察兒童的反應。1歲組的兒童對兔子和蛇的反應是驚奇。在確信沒有什么危險后,便試圖用手觸摸。當兒童想觸摸兔子時,科學家就裝作害怕地大叫一聲,兒童立即縮回了手。如此反復一次之后,即使家長率先撫摩兔子并慫恿兒童觸摸,兒童也不敢再觸摸了,而是小手拍拍胸脯表示害怕。此時科學家撫摩小花蛇,并且作出非常親近的樣子,兒童便也伸手去觸摸蛇,毫無懼色。用同樣的方法試驗4歲組的兒童。由于這個年齡組的兒童已經從美麗的童話中“認知”了小白兔和蛇,所以看見兔子就驚喜地想伸手觸摸,看見蛇卻連連后退。如果科學家如上所述地“表演”對兔子和蛇的態度,幾次之后,兒童便會改變原先的反應去觸摸蛇,卻對兔子表現了疑懼。7歲組的兒童,無論科學家如何努力,家長作何配合,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對兔子和蛇的印象,最多是干脆連兔子也不碰,也不愿去觸摸蛇。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兒童對事物的認知和態度來源于成人,一旦形成,往往持續很長時間甚至終身。
記得兒子4歲時,我正在廚房做飯,他跑過來指著鼻子說:“出血了!”我一看,他的鼻血滴落在衣襟上,還一路滴在地板上。當時我知道,如果我稍微表示出一絲驚恐狀,他必定會嚇得哭。于是我極力控制自己,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他抱到床上躺下,說:“哦,大概你的鼻子太干了,就出血了。我給你塞一個棉花球就好了。你別起來,要不滴在床上,媽媽還要洗被單呢!”我故意將出鼻血看得很輕,似乎出鼻血的壞處就是要多洗幾件衣服床單而已。兒子很快平靜了,問:“為什么鼻子會干?”我說:“你要多吃水果多喝水,鼻子就不干了。”我扯到了吃蔬菜水果上。不一會兒他爸爸回來,他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出鼻血了。”就像說“流鼻涕了”一樣。可是下午外婆見他鼻孔和衣襟上殘留的血跡大驚小怪地說:“呀!出過鼻血啦?!”早已止住鼻血的兒子這會兒卻嚇得大哭起來,而且從此以后,哪怕只是手指上蹭破一點點皮,只要看見血,他就害怕,怎么也改變不了。
兒子5歲時,有一次我和他在沙發上做游戲,正玩著,他忽然猛地將我推開,手起掌落,一只小爬蟲被他拍死在墻上,看得我目瞪口呆。我強按驚恐告訴他蟲子臟,以后不要用手去拍。以后他就用穿著鞋的腳去踩正在爬的毛毛蟲或蟑螂。就是這個大膽的兒子,到念大學時卻還會因為一只撲燈蛾而丟掉手里的書落荒而逃。道理也很簡單,我曾親眼看見他的幼兒園的小老師,因為一只蝴蝶飛進教室而尖叫著抱頭鼠竄!
世界對于兒童來說是陌生和充滿新奇的。兒童認識世界從無知到有知,這一過程來源于成人的教育(間接經驗)和自身體驗(直接經驗)。其中,間接經驗占主導地位。間接經驗除了來自語言,很重要的一條途徑是來自成人的表情和態度。在對語言的理解力還未健全時,兒童通過對成人的表情和態度來判斷事物的好壞、是非、安危以及榮辱等等。所以對于學齡前兒童來說,父母對各種事物的表情或態度無異于一本教科書。
我從來不給兒子講鬼怪的故事,也從來不以關黑屋子作為懲罰的手段。相反,我鼓勵兒子敢于獨處黑暗。在他3歲時,有一次我故意關掉里屋的燈,并告訴兒子燈壞了。兒子就在外間玩,我則在廚房做飯。一會兒,我說:“僧僧(兒子的乳名),媽媽要到里屋去搬一只椅子,可是看不清,你領媽媽進去,不讓媽媽摔跤好嗎?”(這里我又用了聲東擊西法,著重于“不摔跤”而不是“壯膽”)。兒子自然高高興興地充當向導,只是在我的身后推著我進去。出來后我就表揚他沒讓媽媽摔跤(而不是夸他“膽子大”),接著又找理由要他領路。這次他走在了前面,出來后我仍表揚他沒讓媽媽摔跤。還說“僧僧的眼睛真好!”接著我說:“哎呀,忘記拿僧僧的杯子了!媽媽都走不動了。”兒子立刻自告奮勇地說:“我去我去!”我忙關照他:“杯子要拿拿緊噢!”(而不是夸獎他“真勇敢”)。他很快樂地從黑屋子里找來了他的水杯,完全忘記了“黑”與“害怕”之間的關系。因為我始終沒有提到有關的詞。直到現在,兒子從來不信鬼神,不怕黑暗和孤獨,卻會因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飛蟲而大驚失色。
因此可以這樣說:孩子是天生的勇士。成人的若無其事是增強兒童膽量和自信的最有用的表情;在孩子的面前,成人的鎮定自若是任何事情發生時最合適的態度。俗話說“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可沒有權利讓一個勇士在成長的過程中變成了懦夫啊。
圖/毛小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