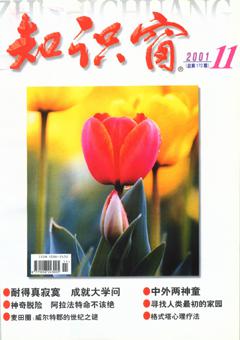樂平狗肉
余釋冰
柔情與俠骨,古戲臺與狗肉,兩種讓我印象至深卻又不相關連的感受與事物,如此奇異地交織在一起,使江西樂平這個贛東北小城變得不再平庸,如同剁碎的紅辣椒、拍碎的蒜瓣,色彩分明,有滋有味。
依附于悠久文化的古戲臺終于敵不過歷史的風雨,油彩剝落,蛛網遍結,而向來上不了臺面的狗肉,卻留香百年,身份倍漲,或許只有吃過了樂平狗肉,才能找出其中的答案。
最初的狗肉攤子擺在小城的西市橋邊,一只篾簍,上置一塊沒亮的案板,刀、狗肉、佐料碗,擠得滿滿當當,攤主悠閑地坐定,身后是一輛老式的加重自行車,一大塑料壺谷酒。不一會,便會有人在攤前坐下,估算著口袋里的錢,眼睛迅速在案板上掃一下,大塊的肉通體黃亮,頭、爪、肝、肚、腸則堆在一旁。酒一倒上,那刀便飛快的舞動起來。不一會,便又會有幾個并不相識的人圍過來,悶著頭,吃著、喝著,熱氣一涌,便“箍”到了一起,盛著碎椒、蔥末、姜蒜、醬油、麻油的碗里盡是筷子。樂平狗肉講究現吃現切,否則會走了香氣。上好的部位是狗爪,先在中產是剖開,用勁一掰,小腿骨便抽了出來,再用尖刀剔除爪尖上的幾塊碎骨,即可切片碼成一堆。筋肉相間的斷面裹著一圈黃亮、透明的皮,狀若花朵,咬勁十足。要有此等口福,早來自不必說,還得搭上一塊分量不輕的狗肝。同樣是下水,狗肚腸則能唱主角,“牛肝馬肺狗肚腸”是一說,而樂平的狗肚腸更是一絕,腸洗凈后,裹成一團,塞進刮凈了的肝里,熟透后切出的片如同腦花一般;黑乎乎的狗頭看相不雅,但皮厚、肉緊、嚼頭好;剔了排骨,肋條也是一層皮,一層肉,脆爛異常,倒是狗腿,肉厚,皮少,常常飽了偶爾路過的外鄉人。這些都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狗肉不過塊把錢一斤,即使身上只有幾分錢,也能吸一個狗腦。
現在,狗肉攤子都搬進了農貿市場,水泥板的臺面,坐看現吃的人也少了,常常是賓館酒家一袋袋的拎走。冬天要賣二十塊一斤,但那撲鼻的香味還是以前的那種,畢竟,只有接渡鄒家村的十幾個師傅能蒸出地道的樂平狗肉。與貴州的花江狗肉、永新的砂鍋狗肉相比,樂平狗肉清蒸、白切,十足的原汁原味。師傅們練得一手絕技,聞香就知狗肉是否熟爛。聽他們說,這套秘訣是祖傳的,傳內不傳外,十幾個攤主均是一個家族里的人,姓鄒,用的刀,也是李紅村的萬鐵匠一個人打的。
我不是樂平人,所以無法揣度遠離故鄉的樂平人在思鄉時的心情,哼唱幾句戲文是能勾出幾行老淚的,要想吃上幾口狗肉,那就只有回鄉了。雖然,我也曾吃過真空裝的“樂平狗肉”,那味道豈止是天上與地下,恐怕要把“樂平狗肉”塊牌子給賣了。
汽笛聲響了,一踏上回鄉的火車,就開始回味樂平以及剛剛吃過的狗肉,好在這是一趟慢車,停停開開,有足夠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