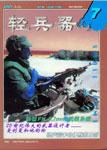非致武器在軍事行動中的戰略應用
非致命武器在戰爭以外的其他軍事行動中的戰術運用早已被人們所認識,如在沖突中驅散集結人群時,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彈就是最典型例子。冷戰結束后,非致命武器的發展受到了各國軍警部門的重視,開發了許多產品,并開始廣泛裝備特種作戰部隊、維和部隊、武警部隊和警備人員。隨著新一代非致命武器技術的出現,非致命武器在軍事行動中的應用將逐漸從戰術層次上升到戰略層次,并將在暴力沖突中得到充分應用。
作為防御體系中相對獨立的一個特殊領域,非致命武器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所采用的技術是形形色色的,由于一直沒有得到政府機構的支持,非致命武器的早期發展一直處于分散的無組織狀態。盡管美國的一些高級官員早在1991年就已對這類武器表示了極大興趣,但是這種支持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有人強烈支持,同時也有人在極力反對。
索馬里危機促成非致命武器的發展
1995年援救索馬里危機為非致命武器的有組織發展帶來了轉機。美國戰區司令官查爾斯·希爾發現,海軍陸戰隊的隊員們在戰斗準備時,必須考慮如何對付可能具有殺傷能力的暴徒。查爾斯曾作為一名行政司法部的官員,親眼目睹了洛杉磯暴亂的整個過程,反思過平息暴亂的經驗和教訓,因此,他建議海軍陸戰隊配備非致命武器前往索馬里,這是該類武器首次正式納入美國軍事行動計劃。
從戰術角度看,這種武器彌補了傳統殺傷性武器在制止沖突事件中的局限性,而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一位從索馬里回來的海軍陸戰隊隊員說:“暴徒們知道我們不允許開槍射擊,他們就試圖逃跑或是竊取士兵攜帶的武器裝備。”在對付具有殺傷能力的暴徒時,非致命武器為執行任務的士兵提供了新的選擇,用它可以阻截、制止并驅散暴徒,同時又最大限度地降低傷亡人數,這就意味著在很多危險情況下,執行任務的士兵可以擺脫殺傷性武器的局限性,在行動上獲得更大的自由度。
非致命武器在索馬里暴亂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受到的歡迎,成為非致命武器發展進程的催化劑,對其他部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引起了美國國會的注意。1996年《國防部授權法案》指定國防部長具體負責非致命武器的發展,1997年海軍司令被任命為執行代理人。此后不久,便成立了非致命武器司令部,目的是在美國軍隊與特別軍事行動之間做好協調工作。此外,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顧問小組,研究非致命武器對人類的影響。
早在1973年人們就已認識到,發展非致命技術需要共同計劃,依賴于多學科的研究。國著名的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擁有在非致命技術多學科研究方面的專長,許多技術都是在他們的應用研究室中誕生的。1997年,該大學專門建立了非致命技術研究院,以配合多學科研究項目的開展。這極大地支持了非致命武器顧問小組的工作,該小組將為非致命武器聯合領導機構服務,發表包括定量分析在內的非致命與傷殘結論報告。
近幾年來,非致命武器得到了較大發展,對非致命武器的概念也已形成共識。相關的訓練在美國各軍種中已經展開,對其使用上的有關規則也正在進一步完善。如今,對非致命武器的需求正在大幅度增加,它的列裝已是勢在必行。前往波斯尼亞執行任務的美軍已經裝備和使用了這類武器,美國海軍遠征先頭部隊也開始裝備這類武器。
使用非致命武器的優勢
當今,整個國際環境使得非致命武器的出現和使用成為必然,正如一名學者指出的那樣:具有超級殺傷能力的強武力對抗已被各種文化之間,或者說是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沖突所取代,危機的存在就意味著危險的存在,當與產生危機的地區有著相同歷史文化的周邊國家或種族加入的時候,地區性沖突將轉變為更大范圍的沖突,其結果必然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與秩序。因此,常規武裝部隊的使用必須非常慎重,絕不能單純從戰術角度考慮,而必須從更深層次的戰略高度看到部隊使用的復雜性。比如說,在巴爾干地區,俄羅斯人支持塞爾維亞人,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國則堅定地站在穆斯林一邊,如果武裝力量使用不當,就可能燃起民族文化間的仇恨之火,而部隊的使用僅僅從戰術角度考慮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單純依靠殺傷性武器,有時是非常不利的,有可能強化地區沖突。同樣,單純依靠殺傷性武力,也會對多國聯盟產生危害。例如在海灣戰爭中,“沙漠風暴”行動之后,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輿論,繼續對伊拉克實施打擊,致使整個阿拉伯世界,包括許多先前支持多國部隊的國家都開始譴責美國。
非致命武器在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中的作用已經變得日益重要,它不僅填補了戰術上的空白,而且還填補了戰略上的空白,它為不足以使用殺傷性武器,而外交力量又不夠的情況提供了新的選擇。它比單純動用武力有更小的挑釁性,所造成的傷害也小得多,而且,它對維護道義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事態就會發展成為一種深陷沖突、混亂不堪的局面。
城市作戰大顯身手
今后,非致命武器在沖突事件中的應用將更加廣泛,尤其是當戰場轉移到市區的時候。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城市中軍事行動的日益增長,將對未來社會的安全環境造成一種獨特的挑戰。”
軍事行動向城市中轉移的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世界越來越趨于城市化。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將是1990年的3倍,達到40億,也就是說,城市人口將占世界總人口的61%。而軍事行動的進一步展開,需要部隊在城市中的港口或機場之間運動,要繞過不斷擴大的百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處于弱勢的一方會引誘力量較強的對手進入市區作戰,迫使對手在作戰效能最低的地方進行戰斗,以試圖借此削弱對方的戰斗力。1993年的索馬里沖突就是這樣的,索馬里叛亂分子誘使美軍展開了只能用步槍對步槍的城市巷戰。
城市作戰產生了分辨參戰與非參戰人員,減少附帶災難等一系列獨特的問題。開展城市戰的對手常常與非戰斗人員混雜在一起,而且還可能利用市民做人體盾牌來抵御進攻,直到萬不得已,他們才會利用城市軍事防御設施來掩護、隱蔽和運動。因此,非致命武器在城市作戰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它們可以用來疏散非戰斗人員;能夠在最小傷亡的情況下,區分參戰與非參戰人員;還可以清除人為路障;而且,它們的使用可以減少對城市設施的破壞并最終減少戰爭消耗,這就使受保護的城鎮遭到破壞的可能性減少到了最低限度。
非致命武器的戰略應用
相比而言,目前非致命武器的應用大多數仍在戰術意義上,其產生的結果往往是肉眼可見的,如聲波武器、激光致眩武器、粘性泡沫和噴射辣椒油脂等武器。而新一代的非致命武器將更加強調軍事戰略上的應用,因此,人們寄予下一代非致命武器更多的希望。
“沙漠風暴”行動展示了新一代非致命武器的發展前景。有資料表明,攜帶有計算機病毒的芯片裝入打印機,通過約旦走私至伊拉克,然后被送往一個防空地下掩體。這種計算機病毒能使負責在各防空炮兵連之間進行協調與通訊的網絡癱瘓,當技術人員打開顯示器檢查空中防御系統的時候,它便吞噬計算機的Windows操作系統。
另一個例子是,在海灣戰爭中,美國使用“戰斧”導彈在伊拉克電廠上空釋放了碳纖維炸彈,成千上萬的碳纖維破壞了電力設備中的電路,最終導致伊拉克電力供應中斷,類似這樣的武器說明,在今天對軍事和民用防御設施進行攻擊時,避免傳統殺傷性武器造成的突發災難已成為可能。
今天,新一代的非致命武器正在不斷涌現,包括聲波、電磁脈沖、激光束以及其他定向能武器。將來,微波武器可能用來切斷敵人與后方之間的聯絡;激光武器將降低敵方重要探測系統的性能;攜帶電磁脈沖系統或碳纖維的巡航導彈幾乎能夠破壞任何電子設備,從而切斷軍事和民用防御設施與外界的聯系。此外,這類技術還可用來實現多種戰略目的。它能夠支持經濟制裁;可以在戰略上使敵人暫時麻痹,從而為發揮外交作用創造時機等等,這都是殺傷性武器所不及的。
總之,非致命武器使用的基本原則是使那些具有致命戰斗力的敵人變得脆弱,甚至失去戰斗力。這項技術如果能夠合理公正地使用,不僅能夠削弱敵人斗志,打擊敵人,而且能夠取得道義上的支持。
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
非致命武器不僅肩負著艱巨的使命,而且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它們需要被法律、社會、宗教等所接受,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正如其發展歷程一樣,其合法地位的取得,主要依賴于怎樣準確評估它們對人體所造成的傷害,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區分殺傷性武器與非致命武器,然而,確定區分標準并不像想象的那樣簡單。
在1997年美國技術專題研討會上,專家們明確指出,確定一種武器對人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首先,試驗造成的潛在傷害甚至死亡,嚴重地制約著試驗的開展;其次,動物試驗也同樣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結果也不完全可靠;第三,非致命技術已涉及到了非常廣泛的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和廣度已經超出了生物技術的發展速度。
目前,國際上已經制定了一些限制武器對人身造成傷害的公約。比如: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的激光武器就違反了1995年《禁止致盲性激光武器禁約》;使用能造成神經系統紊亂的定向能武器則違反了1980年頒布的《常規傳統武器公約》;使用超出非致命目的,引起“超常”傷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則違反了《1977年日內瓦公約草案1》。
使用非致命武器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它們引起的環境改變如果有害人類健康,就將違反《禁止軍事或敵對的使用破壞環境性技術公約》。因此,要建立國際標準,就必須科學地掌握這類武器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最終影響。
1996年,在瑞士舉行的“醫藥與武器對人類影響”研討會上,一些人認為,多數非致命武器違反了國際法,建議醫學界和法律界聯合起來,用醫學數據來制止非致命武器的研制,隨后,在一份提交給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報告中提議:必須以十分嚴肅的態度檢驗包括“非致命武器”在內的所有新型武器,新型武器的研制必須符合人道主義。
非致命武器使用后的許多效果還沒有得到明確驗證,使用效能有待于未知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以及技術的發展。但是無論是軍方還是其他組織機構都必須明確:對于非致命武器的使用,在正確與錯誤之間有著明顯區別。非致命武器的正確使用是一種必然趨勢。◆
馬紅麗倪志成編譯
(編輯/樵夫)
返回主列表(Returnt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