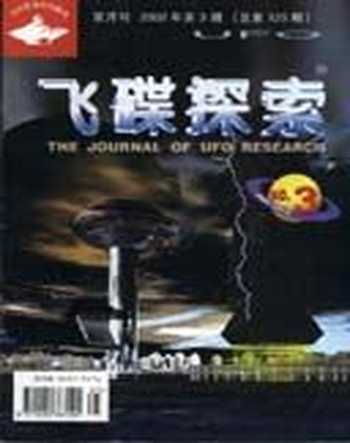零重態:飛行的超越
楊 進
早先,科學家把自然力分成四種,即引力、電磁力、強核力和弱核力。但當代科學家卻煞費苦心地想要找到一個統一理論,把這四種力解釋為是統一力的不同方面,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取得成功。
引力至今還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讓人無法識其廬山真面目。量子力學認為引力是由引力子(據稱是一種虛粒子,檢測不到,但人們可以知道它的存在)攜帶的,太陽和地球之間的引力是這兩個天體的粒子之間交換引力子的結果,于是地球就繞太陽公轉起來!經典物理學家則認為引力是一種實際存在,是一種叫引力波的東西構成的,但直到現在它還沒有被觀測到過。無論怎樣,人們只是憑著經典力學的知識才認識到引力子確實存在,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東西,是虛粒子還是引力波,人們都無法觀測到。因而,人們對引力是怎樣產生的,又是怎樣控制它的大小,能不能讓它消失又復而把它激發出來都幾乎一無所知。
其他三種力,情況就大不同了。首先,人們對于軟磁材料的電磁力的產生與消失、大小的控制早就駕輕就熟了。其次,人類在50年前就能夠用小得多的能量把強核力激發出來,制成了原子彈;之后,原子能發電就是一種利用可控強核力產生的熱量來發電的方法。再者,1867年史蒂芬·溫伯格(哈佛)和阿伯達斯·薩拉姆(倫敦帝國學院)弱核力和電磁力的統一理論認為:除了光子,還存在其他三個攜帶弱核力的有大質量的粒子,統稱為重矢量玻色子。這種理論在之后的十幾年中,在低能量下被實驗證實。溫伯格-薩拉姆弱電統一理論可與100年前麥克斯韋統一了電學和磁學并駕齊驅。1983年,卡拉·魯比亞(歐洲核子研究中心)領導了幾百名同事發現了光子中也存在被弱電統一理論很早預言的三個帶質量的粒子,人們稱它為中微子。弱電統一理論促使許多人試圖將弱核力、電磁力這兩種力與強核力合并到大統一理論中去(請注意,并不包括引力)。但是,建立大統一理論要建造足以將粒子加速到所需的能量——可能是1千萬億吉(1吉為10億電子伏特)的設備,它像太陽系那么大,這不可能。我們可以像弱電統一理論那樣,以在低能量條件下檢測的結果建立推論。
由上述可知,在四種自然力中有三種已經搞得成就非凡,只有引力似乎還處在牛頓(公元1642年~1727年)時代——蘋果從樹上落到地上而不飛上天,只認識到此力的一種外表特征。因此,引力是一塊尚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但它卻是一把打開航天大門的“金鑰匙”。因為UFO正是一種帶有反引力裝置的“零重態”航天器。
牛頓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作用于質點的力(F),等于質點的質量(m)與加速度(a)的乘積,即F=ma,加速度的方向與力的方向相同。在地球表面,任何質量為(m)的物體都受到重力(P)的作用,在重力(即物體與地球之間的引力)作用下得到的加速度稱為重力加速度(g),則可得到P=mg或m=P/g。由此F=ma也可寫成F=(P/g)a。在地球表面g=981m/s 2,在月球表面g月=g地/6。航天器運行在不同的引力場中(根據愛氏的廣義相對論也可稱為伽利略系),g航就有不同的值。由于星際距離非常大,所以在航天過程中絕大部分時間航天器都處于極低的引力作用下,g航接近于零,也就是說航天器在近“零重態”飛行。它要維持近光速飛行,加在航天器上的推力就只需很小,只要能克服它外界的阻力(比如說暗物質給它的阻力)就行了。問題是航天器在某星球上起飛時與到達某星球著陸前它的重力非常大——有人認為航天器在脫離起飛星球之后直到進入著陸星球之前的飛行所需能量還不到起落之間總能量的1/1000。所以在伽利略系的飛行過程中,航天器所需的飛行推力在沿途是容易得到的,而且航天器上的能量轉化和儲能設備也不會很大。給航天器上裝上反引力裝置,使它在起飛或著陸時的引力場內都能達到“零重態”,也就是F=(P/g)a中的P=0。因此,從理論上講,我們可以用很小的推力(F),達到無限大的加速度(a),當然加速度不會無限增大,因為當航天器的速度增大時,加在它上面的外界(空氣、 暗物質……)阻力就隨之增大,當航天器的推力與外界阻力平衡時就會做勻速運行——亞光速、光速、超光速都是可能的。但必須注意到航天器的設計推力不能隨意增大,因為推力愈大,航天器所承受的外界阻力也愈大,而外界阻力越大則意味著航天器達到的速度也越高,而航天器所能承受的力則至少受到它材料性能的制約。
當航天器上的反引力裝置可以調節時,航天器便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在“零重態”狀態下運行,只要動動調節旋鈕或開啟自動系統,正在以超光速運行的航天器瞬間就可以由“零重態”增到“微重態”,反過來任意減重也可以。當超光速運行的“零重態”航天器突然增加重量,并且航天器的推力保持不變時,那么它就會瞬間減速飛行或停止飛行;反過來它又會從停飛或慢飛狀態瞬間轉為任意方向的超光速飛行,很快消失在人們的視野里。當航天器的重量等于下降時空氣(或其他介質)給它的阻力時,它就會慢慢飄落下來。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重力——萬有引力使航天器和人套上了枷鎖,使人類絞盡腦汁、耗盡資源也未必能把航天器連同人一起送到離地球很遠的別的恒星系去!這就像一只小鳥身上綁了一塊大石頭一樣,根本飛不動,反之如果我們除去這塊大石頭,小鳥瞬間就會向任意方向飛去。反電子的發現激勵著人們去發現反引力,裝上可調反引力裝置的航天器就可以像UFO那樣驟停驟飛、驟隱驟現、驟快驟慢,還能直角轉彎,還會飄飄忽忽像樹葉一樣飄搖而下。UFO的輝光是反引力裝置作用的結果,不同的作用強度作用于不同的材料就會產生不同的顏色。UFO來自不同的星球,不僅采用不同的材料,而且還會有不同的外形設計。
航天器的“零重態”飛行是必要的,它可以避免被吸入“黑洞”;可以避免中途被行星俘獲;可以輕而易舉地躲開彗星、小行星或宇宙塵埃的撞擊,因而特別有利于航天路線的選擇,而且“零重態”航天器以超光速飛行的任何一條路線都可以成為“瞬達隧道”。
以上假設植根于牛頓經典力學,但與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也不相悖,因為愛氏認為的無法達到光速的物體是有重量的而不是“零重態”。而且如前所述,光子中三個攜帶弱核力的粒子還具有大的質量,而沒有重量的物體運動速度就可以超過光速。新世紀將是人類開發反引力的世紀。
離我們最近的一顆恒星是天狼A,它與太陽系的距離約為87光年。1977年美國發射的“旅行者”號宇宙飛船的飛行速度是172米/秒(約為第二宇宙速度的一倍半),現已飛出太陽系,大約需要152萬年的時間才能飛到天狼A。光速航天器如果不計愛氏的長度收縮和時間膨脹效應飛到那里也要87年,然而愛氏兩效應是必須考慮的。計算表明,當航天器的速度達到接近光速時,飛到那里就只需054秒的時間,真可謂彈指一揮間!但是我們的銀河系有10億光年的跨度,我們人類現在所能觀察到的宇宙也已是300億光年直徑的球體。我們以每秒飛行1光年計算,那么飛越10億~300億光年所需的時間約為30年~950年。當航天器在“零重態”下超光速飛行時,我們已不能用愛氏的方法計算了。“零重態”超光速飛行的計算有待開發,但肯定只需要更短的時間。
至于在亞光速、光速或超光速航天器中處于失重狀態生活的地球人,會不會延長壽命,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愛氏兩效應帶來的有利因素外,眾所周知,當代航天的實踐證明,人在太空逗留5~7個月會得骨質疏松癥,逗留1年骨骼失鈣將達全身鈣質總重的20%左右并不可逆轉。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有機智能生物,決定其生命長短的應該是總體生存環境和個體生活質量而不是單因素的運動速度。人類要做超遠程宇航至少還有生理上的失重需要解決,同時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孤獨感也要消除。
由于地球是一個長期穩定的生態進化環境,人類才得以產生并生存至今。但是這種長期穩定的環境終將會變化破壞直到消亡:例如太陽的熄滅(或氦化)、地球被小行星碰撞或據稱到6000萬年以后地球會進入銀河系的災變環境區等等。所以超遠程宇航終將成為人類的實際需要,以便實現星際遷移,否則人類會失去生機。